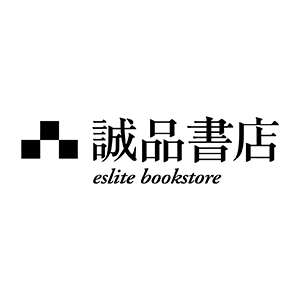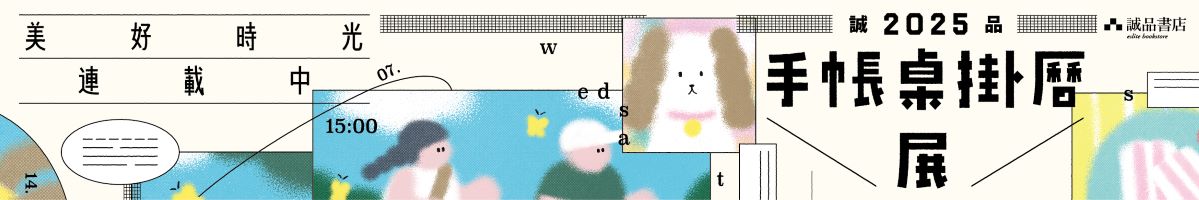Perfect Days with Music and Literature——《新活日常》中的「互文性」
撰文 香港誠品書店60/70s卡式帶回魂:城市邊緣的遊蕩者
在《新活日常》出現過十首樂曲,歌曲類型由Soul、Folk、Rock至Punk等無所不包,但都有同一個特質——歌曲均發行於6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從歌曲的擁有者:The Animals、 The Velvet Underground、Lou Reed、Rolling Stones、Patti Smith等熟悉又閃耀的名字,組成了主角平山那一代的文化基因,同時亦是導演音樂品味的一次私心展現(在他的雜文《溫德斯談電影:情感創作與&形象邏輯》中有專文談及過電影出現的樂團或樂手,如奇想樂團、滾石樂團、范.莫里森等)。
電影以搖滾樂團The Velvet Underground 的成員Lou Reed 同名solo歌曲〈Perfect Days〉命名,片中多次出現他的卡式帶,Patti Smith 又與Lou Reed 淵源匪淺,這種音樂連結以塊狀的方式為電影定調。60年代後期搖滾樂從Bob Dylan的體制反抗、Beatles的愛與和平中出走,來到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毒品、社會異化、虐戀、扮裝皇后,從大寫的理想主義去到個人化暗黑經驗的考掘,如音樂評論人張鐵志而言,The Velvet Underground創造出「黑色搖滾」(a rock noir)「讓人們正視不敢凝視的殘酷大街,並開始理解城市邊緣的遊蕩者」,《新活日常》中的平山固然不是癮君子或Drag Queen,但重點在於上述提及的,這些歌曲代表個體經驗對主流價值的挑戰,及底層邊緣人的關注。電影起首的The Animals〈House Of The Rising Sun〉(1964)就已是新奧爾良貧民窟青年的自述(電影中後段居酒屋老闆娘吟唱的日語版將貧民窟改成「妓院」);《新》正正遍佈都市邊緣人:廁所清潔工平山(替迷路兒童尋覓家人會被厭棄手骯髒)、貴司(高舉「沒錢不能戀愛」,典型的「月光族」)、天天在公園擺動特殊肢體的拾荒老伯、愛摸人耳朵的青年寺等。
而細心點可以發現,電影配樂的主角,不論是〈Pale Blue Eyes〉(1969)失去前度呢喃「Linger on, your pale blue eyes」;〈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1968)中橫跨二千公里追夢最後「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wasting time」;還是〈(Walkin’ Thru The) Sleepy City〉中夜遊都市感嘆「I'm tired of walking on my own」,都是孤獨而重疊的深色身影,代表著城市一個個寂寞的靈魂,伴隨著平山的駕駛征途。
電影對每個角色的背景都大量留白,編者大膽從電影配樂嘗試填補。在電影大概30:40出現,由美國歌手Otis Redding唱的〈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1968):
I left my home in Georgia Headed for the 'Frisco bay 'Cause I've had nothing to live for And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ome my way
Look like nothing's gonna change Everything still remains the same I can't do what ten people tell me to do So I guess I'll remain the same, yes
歌曲講述一個離鄉別井、無法符合他人預期的浪子長途跋涉追尋自己心中理想,最後落寞地在海灣碼頭度日。電影沒有交代平山的過去,但從他與妹妹的對話可以推斷他應該出身富裕家庭,因為不知名原因和父親鬧翻,離家來到這簡陋的居室,從事外界無法理解的清潔工作,和歌詞裡漠視世俗聲音、甘願維持現狀的「我」互為寫照。在另一個場景,在酒吧工作的綾在平山車中愛上〈Redondo Beach〉(1975),此歌據悉是Patti Smith與姊姊Linda爭執後有感而發下創作,內容描述一個女孩在海攤尋人,期間有人被發現自殺,自殺者正是自己尋覓的對象——「you'll never return into my arms cause you were gone gone」,是一個關於痛失所愛的故事。綾在平山車上第二次聽樂曲時流淚,觀眾並不知道原因,因為電影的語言,我們清楚綾對平山的同事貴司並無興趣,綾對樂曲的觸動是否能暗示她正為他人受情傷?(此歌更曾被解讀歌詞影射女同性戀)。
除了可以作為背景推測以外,電影中的樂曲有時後會用來配合故事情節的轉變,例如在平山和貴司到訪下北澤卡式帶店後,平山獨自駕車回家,途中因汽油耗盡停泊路邊,響起了滾石樂隊的〈Walking Thru the Sleeping City〉(1964),講述在街上遊蕩的主角進入了一間Café,痛惜內裡的人不曾發現城市夜景的美:
Just a lookin' at the sleepy city In the night it looks so pretty No one sees the city lights They just care about the warmth inside
緊接著他遇見一個女孩,並期望能與她共享美景,不再孤身一人:
I'm tired of walkin on my own It looks better when you're not alone
《新》中平山對卡式帶的珍視表現了他對音樂的熱愛,但貴司和卡式帶店老闆都只關注卡式帶復古熱潮帶來的收益,並非真正欣賞70-80年代的音樂,他在路邊拿著Lou Reed卡式帶沈思的寂寥和歌詞主角可謂互通。能夠和平山分享同樣品味的,是在他車上自然流露出對Patti Smith音樂感到興趣的綾,所以他才會對綾展露出遇見知音的神情。聽完〈Walking Thru the Sleeping City〉,平山還要一個人回家吃杯麵;盡顯落寞;但緊接著綾向他歸還卡式帶並無預警地親吻了他,電影播放的是Lou Reed的〈Perfect Day〉(1972),歌曲講述主角與對方在公園喝雞尾酒、彈吉他、餵動物,共度了美好的一天:
Just a summer's day Problems all left alone Weekends on our own It's such fun
Oh, it's just a perfect day I'm glad that I spent it with you I thought I was someone else Someone good, yeah
雖然主角知道這種美好只是短暫的,但亦因為如此,主角可以忘卻煩憂和自己的處境,可以「hanging on」下去,和《新》中平山被吻後開心了一整天,歡快地踏單車,吃飯時還甜笑地摸自己被吻的左臉互相呼應,可見這些歌曲並非導演單純音樂性的考量,而是為情節過渡而精心挑選。
文學地圖:被隱藏的電影語言
《新活日常》中的平山熱愛閱讀,休息日會到書店購買一百円的文庫新書,電影出現過的書籍共有三本,分別是美國作家福克納的《野棕櫚》、派翠西亞.海史密斯的《短篇小說:11》及日本作家幸田文的《木》。《野棕櫚》由〈野棕櫚〉與〈老人〉兩篇小說構成,其中〈野棕櫚〉講述了女藝術家夏洛特為了自由和愛與醫生出軌私奔,最後悲劇收場的故事;〈老人〉則講述兩名囚犯被派去拯救被圍困的水災災民,最後拯救成功,卻被控越獄而加判十年的荒誕故事。前者關於「選擇與代價」的主題,和平山關於生活模式的思量,遙遙相合;後者關於「付出與回報不對等」的描繪,在平山的日常生活經常發生,平山敬業樂業,清潔每一個廁所都絕不馬虎,除了自製清潔工具,還仔細地用鏡子檢查每個打掃後的廁所有否遺漏的污垢,卻經常遭到質疑(同事貴司:「這種工作為甚麼要如此努力?」妹妹:「哥,你……真的在打掃廁所嗎?」)或被厭棄(替迷路兒童尋覓家人會被嫌棄手骯髒)。
至於《短篇小說:11》,平山的姪女Nico表示自己能夠理解其中一篇“The Terrapin”故事主角維多的處境,“The Terrapin” 講述了男孩維多長期承受母親的精神虐待,包括要他讀不喜歡的學校;為了令他看上去感覺更“French”逼他穿“short shorts and stockings that came to just below his knees, and dopey shirts with round collars”等。或許可以引述一段文字來讓大家更深刻感受維多的壓力:
Mom: “Today is Saturday.”
Victor: “I know.”
Mom: “ Can you say the days of the week?”
Victor: “Of course.”
Mom: “Say them.”
維多最後因為寵物水龜母親烹煮而弒母,由此可以推斷《新》中Nico同樣承受來自母親的管控。電影雖然沒有交代Nico為何突然來找平山並要借住他家,但從她母親接獲平山電話後旋即趕來可知Nico應該是和母親鬧翻後離家出走,鬧翻的原因,導演沒拍,從Nico母親乘搭的轎車、送給平山昂貴的巧克力以及指出平山和自己家是「兩個世界的人」的說話,可知她是以富人的標準在培養女兒,偏偏Nico的性情,卻是和叔叔一樣偏重精神世界大於物質享受,可以想像Nico平日的壓抑以及成長的陣痛。
編者最想討論的,是第三本書籍,幸田文的《木》。此書是由十五篇有關樹木的散文組成,是幸田文從北海道至屋久島和不同樹木互動後結集的,有關生命本質的感悟,在首篇講述蝦夷松樹自體更新的〈えぞ松の更新〉,有相當有意思的討論,以下引述此文的起首:
「あの木もこの木も、「木」という言葉ひとつに括って「ひとつ」と数えることは、人間の身勝手であるのだが、そうすることでようやく人間たり得てもいる。「木」とは関係のないこちら側の事情。しかしそういう事情とは全く異なる次元で、木は「ひとつ」であ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るようなのだ。」
為方便討論筆者簡單試譯:「如果人類把這棵樹和那棵樹都簡單歸類為『樹』這『一』個詞語,這樣未免太自私了。但透過歸納事物,人類才得以發展成為人類。然而,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下,樹木又似乎努力地成為『一』。」簡單而言,幸田文是想表達每棵樹之間都有不同的特質,不能夠被簡單概括為同一事物,鼓勵我們發掘事物的特性,對生活提升覺察力,而「樹木又似乎努力地成為『一』」是指她在林間看見在倒臥的蝦夷松樹幹中,長出新的幼苗,幼苗透過寄生在樹幹中吸取養分長成新樹,完成林木更替,就如同人的生死循環一樣。筆者認為這和電影的主題很有關聯,平山正正是個會對日常事物仔細觀察和感知的人,他會每天利用公園午餐的空檔用膠卷相機拍下樹木的變化,對於長在城市間隙的幼苗,會愛惜地移植到別處,努力將每天都活成特別的一天,不簡單將自己簡化為「一」,同一時間,蝦夷松的新舊交替,又恰似平山與Nico之間的關係(平山在Nico住在他家時開始閱讀《木》),他贈Nico相機、文學小說,教會她欣賞生活細節的美,保護她靈性的部分,同時又將自己的生活哲學傳授給她(「下次是下次,現在是現在」),老去的平山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不知不覺間灌養了成長中的Nico,就如同蝦夷松以老幹餵養新苗一樣。
上文拉得相當遠,或許還有些過度詮釋的可能,但筆者都旨在提出,Wim Wenders在《新活日常》中大量引進其他文本(音樂、小說,甚至攝影),文本與電影之間互相延伸成為更廣闊的閱讀空間,是不能被單一閱讀或將之當成是電影製作的技術性考量,唯有將文本脈絡化,才可以讀懂他的苦心孤詣,或更了解導演的電影的美學養分。
延伸閲讀

《未來還沒被書寫:搖滾樂及其所創造的》
作者|張鐵志
出版|印刻文學生活雜誌

作者|文.溫德斯
出版|原點

《只是孩子》
作者|佩蒂.史密斯
出版|新經典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