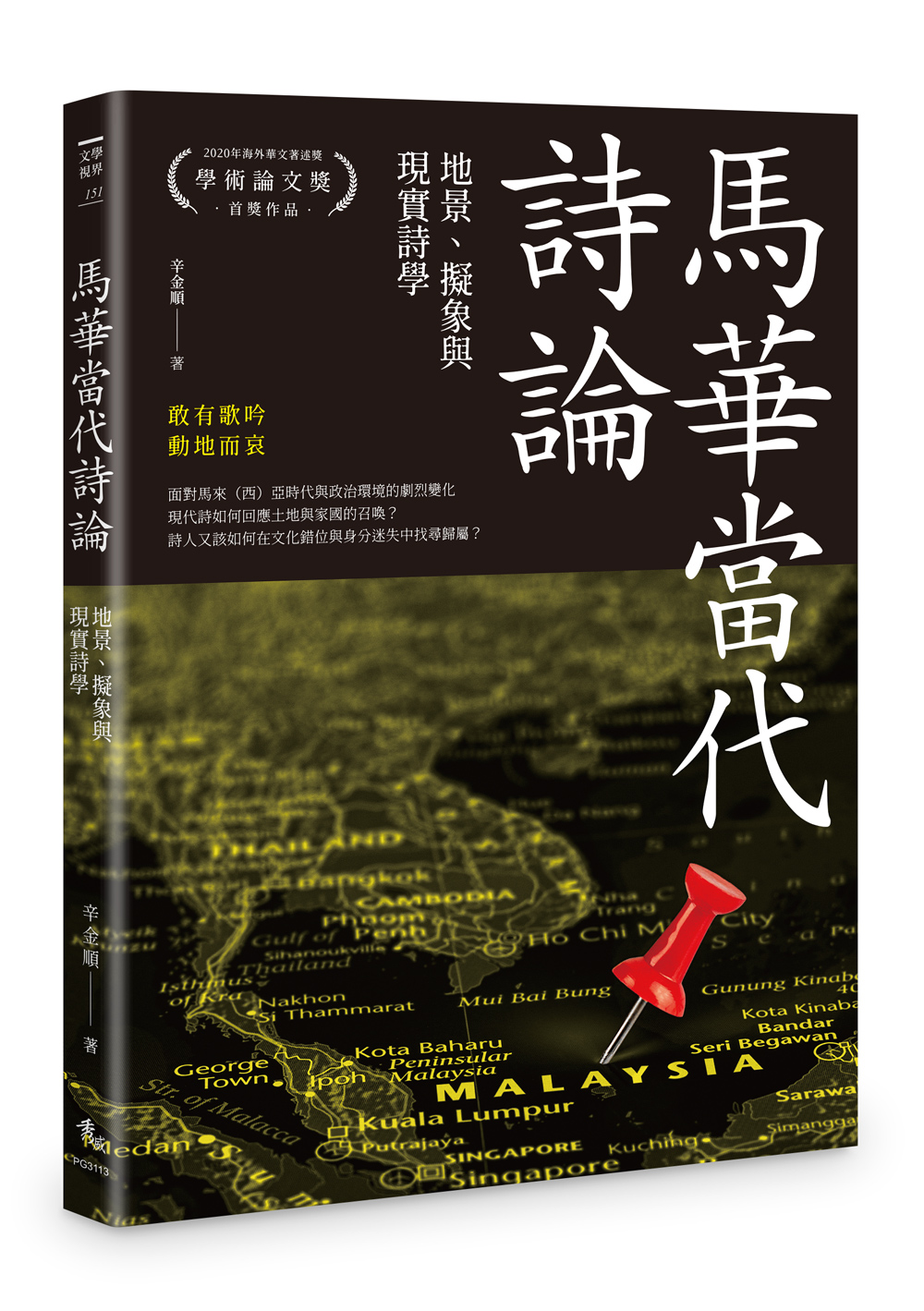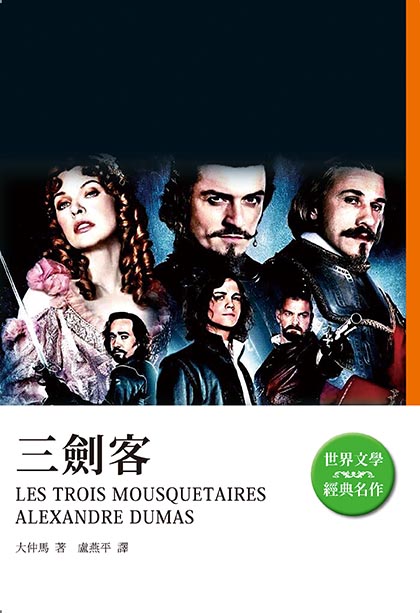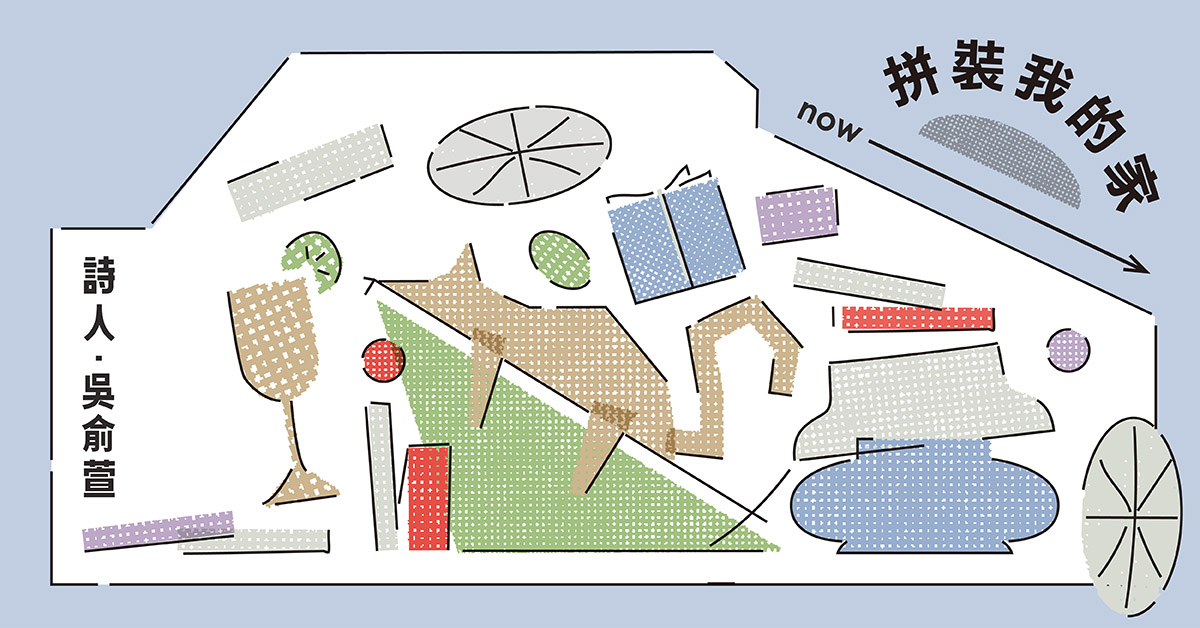漂鳥的身分與土地的救贖 |葡萄牙文學經典《畫鳥的人》 #經典共讀
撰文 張淑英(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家裡的餐桌一年一年地分裂開來,每塊碎片都去了世界的另一個角落。
.
.
.
葡萄牙文壇超重量級作家 莉迪亞.豪爾赫 最經典作品 ☞《畫鳥的人》首次中譯出版!

▌撰文者簡介|張淑英
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鄉愁書寫(Saudade):漂鳥的身分與土地的救贖
莉迪亞.豪爾赫 (Lídia Guerreiro Jorge, 1946-)和前輩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奧古絲汀娜.佩薩—路易斯(Agustina Bessa-Luís),以及同輩小說家羅伯.安頓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並列為當代葡萄牙文學最重要的健筆。前輩或同輩不是摘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就是葡萄牙最重要的賈梅士(Luís Vaz de Camões)文學獎得主,足能評斷莉迪亞.豪爾赫在葡語文學的分量。二○二○年底,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國際書展授予她的羅曼語系文學大獎更是跨國跨語言的重磅榮譽。
莉迪亞.豪爾赫的第七本小說《激情的峽谷》(O Vale da Paixão)一九九八年面世後,接連獲得四個文學獎項的加冕,如今以英文(和西文)譯本的名稱☞《畫鳥的人》(The Migrant Painter of Birds)在中文書市出版,有了更具體的象徵意涵及隱喻。

閱讀莉迪亞.豪爾赫的作品或☞《畫鳥的人》,有幾個破題的關鍵符碼:第一個是薩拉查 (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總理建立的「新國家政體」(Estado Novo)獨裁體制,長達四十二年到他逝後四年的康乃馨革命始告終結(1932-1974)。這當中包括殖民地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尋求獨立的革命戰亂期,恰巧也是作者在兩國執教鞭六年(1968-1974)的非洲經驗。
第二個是一九五○至八○年期間,葡萄牙高比例的鄉村人口(68%~58%遞減),而自一九六○年末起,每年約有十萬人移居國外。長期且獨斷的獨裁體制,艱苦貧困的農村勞力,不斷遷徙的人口外流,在在撩撥了詩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筆下所謂的「鄉愁啊(saudade)——刻骨銘心,唯有葡萄牙人懂的徹底」。在那個時代,離去的人和遭棄的土地,盡是悲劇的鄉愁!以莉迪亞的作品為博士論文且提出精闢解析的學者保羅.賽拉(Paulo Serra) 點出從☞《畫鳥的人》可以看到莉迪亞小說的兩大特點:憂鬱的美學(豐沛的情感筆觸刻畫人物的無奈與屈服)和殘酷的寫實(人類在歷史的洪流中淹沒,尊嚴赤裸受辱的不堪)。

☞《畫鳥的人》以莉迪亞的故鄉為背景,敘述葡萄牙南部法羅區(Faro)鄉村瓦馬雷斯(Valmares)大宅院的蛻變。故事環繞綿延將近半個世紀的狄亞斯家族的流變與停泊:一個大家長范西斯科、他的八個兒女、三媳一婿、四個孫子與一對工頭夫婦的家族史。
「Saudade」是葡語文學的傳統與經典議題,是一種因距離產生的既親密又憂鬱的情感,一種想要破除距離的渴望,又明知不可得的糾結;既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思,也是人與地景的思鄉。小說扣人心弦的Saudade必要條件(sine qua non)是華特和他的女兒這對父女的親情轇轕和身分認同。

☞《畫鳥的人》是華特,而真正的主角是說故事的女兒。華特是家族裡唯一不甘下田幹粗活的老么。他叛逆、風流、逃逸,年少輕狂和瑪莉亞·艾瑪生下女兒,卻遠走他鄉;身殘腳跛的長兄庫斯多喬(Custódio,意思即為監護人)娶了瑪莉亞·艾瑪,父女關係變成了叔姪。從此彼此的聯繫是華特浪跡天涯寄回的家書,以及坐在他的軍毯上畫下的各地珍禽異鳥。小說裡,狄亞斯家族每個人都有名字,唯獨女主角沒有名字。「華特的女兒」是她的代稱,她是「缺席的全知」:她記憶、她書寫,她觀看聆聽,一度也曾像年輕時的母親一樣佻達失了身,她都一一記錄串連,想要對永遠不會知道這些詳情的「華特叔叔」細訴。書寫是她的話語,沉默是她的聲音,但不能碰觸與言談「女兒」的身分;而華特,卻永遠是「在場的缺席」,鄉愁療癒的方式是再次離家,就好像法國詩人高第耶(Théophile Gautier)所描述的「易地/異地鄉愁」(nostalgia inversa),易地流浪異地方知故鄉情。女兒的日常生活永遠有華特和來自四面八方的鳥的影像相隨。華特也是遠離家鄉眾兄嫂書信控訴的藉口,推諉責任的箭靶。狄亞斯家族的互動猶如板塊運動造成的地震,范西斯科和華特的衝突對峙是震源,華特和女兒的會面所牽連的攪擾則是震央。

鳥圖和毯子這些「物件」成為華特的「假體」(prosthesis),讓華特的女兒有了繼承的屬性。「鳥」的特性也成為華特的譬喻。他像鳥類一樣遷徙移動,從北美頂端到南美盡頭,試圖擇良木而棲;毯子成為他畫圖的一部分(畫鳥與風流「鳥=屌」的憑藉),是女兒的追憶、懷舊、思念、發現真相與身分的救贖。

遷徙是 ☞《畫鳥的人》另一個重要的主題。
狄亞斯家族的兄弟們,除了獨裁獨斷的家長范西斯科和不良於行的長子庫斯多喬守著宅院,守著土地,其他的手足都遠離家園,另謀出路,也紛紛致富。一開始,在墨守成規又專制的父親的統御下,狄亞斯家族成員沒有人可以逃脫范西斯科的寡頭鐵律,但是也沒有人要就此屈從他們被限定的命運。這段鄉間人口外移和莊園逐漸蕭條的景象,和魯佛(Juan Rulfo)的☞《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或胡利歐.亞馬薩雷斯(Julio Llamazares)的☞《黃雨》(La lluvia amarilla, 1988)有類似的蒼涼和無情。前者是可馬拉(Comala),後者是艾涅爾村(Ainielle),最後都只剩耄耋老翁苦守的孤寂。


莉迪亞想藉著《伊里亞德》詩性的鋪陳和史詩的悲泣來襯托☞《畫鳥的人》的抒情與呢喃。《伊里亞德》建構的主題,烘托了狄亞斯家族鄉愁的縮影。一是還鄉:范西斯科殷殷期盼召喚不回兒媳們返鄉的念頭,父權的消失是他的鄉愁;二是榮譽:兒媳先後棄宅院而去,與莊園切割、離開鄉里為揚眉吐氣。
對范西斯科而言,「之前與之後,遠方與屋內,他都毫無興趣。他唯一在意的只有自己土地的範圍,以及他以堅定意志侍奉的熟悉神祇。榮譽、愛與生命,唯有轉化成田畝才有意義。」三是命運:造化弄人,親情、愛情都沒有對位。華特依然如漂鳥消逝,瑪莉亞·艾瑪永遠等不到伊人回首;庫斯多喬忍受「烏龜」的侮辱,華特的女兒形同「孤女」,兩個身/心缺陷的人是狄亞斯家族最後守護宅院的傳人。

薩拉馬戈稱許莉迪亞的創作感性與理性兼備,善於梳理時間的節奏。
我們讀到的☞《畫鳥的人》裡,華特的女兒是時間的裁縫師,是織拆壽衣的潘尼洛碧,然她的記憶拼圖也難免錯亂,跳了針,穿錯了線,但都無妨,時間在這本小說裡只有當下有意義,但以靜謐封存,近似虛無。生活在他方或擁抱鄉土的人依然在佛朗西斯科.馬努埃.梅洛(Francisco Manuel de Melo, 1608-1666)詮釋的矛盾修辭——「磨時樂,享時苦」(Saudade)——的情感裡等待救贖。
▌作者自序——莉迪亞.豪爾赫
◎莉迪亞.豪爾赫
2005年獲頒法國藝術與文學勳章,2006年成為首位信天翁文學獎(Albatross Prize)得主,2011年獲得拉丁聯盟國際獎(Latin Union International Prize),2013年獲著名法國雜誌《Littéraire》評為「十大文學之聲」,2014年獲西班牙-葡萄牙藝術與文化獎(Spanish-Portuguese Art and Culture Prize), 2015年獲葡萄牙文壇Vergílio Ferreira獎,並於2020年獲FIL羅曼語系文學大獎的重磅榮譽。
製圖學(CARTOGRAFIA)
這本書起稿於某個雨夜。那天,家門前的小徑上覆著泥土,剛剛結束長途旅行的我正準備返家。接近家門時,我注意到門前放置了一條毯子,讓我們可以在進門前清潔鞋子。我就是這麼做的,在那條毯子上蹭掉鞋底的泥濘,然而在午夜時分,心中卻浮現了一股懊悔之意。一名士兵的形象清晰地浮現在我面前,他對我說:「把我的毯子從泥裡拿起來,為何讓它這樣消失,在腳底下消失?」

我起身把大門的毯子拿起,擰一擰、甩一甩然後放在壁爐晾乾。接下來的幾天都持續下著雨,我拿起筆記本,在上面寫出第一行字——在士兵的毯子前。那是個四○年代的角色,有能力、聰明睿智且充滿夢想的葡萄牙年輕人,然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即便腦中充滿點子,卻受到了限制,因此只留給家人一條毯子留念。這條毯子激盪出我想隨雨聲寫作的故事,當時我文思泉湧,因而確立了這個故事的開始。
但是三天過後,那個我認為只是短篇故事——由一條毯子憶起前主人的簡短故事,最後的敘事看來卻是不完整的。雨天結束了,我眼前這些複雜的情節與資料足以獨立寫成一本書。這是一個以概述形式且結合人物分析構成的故事,這個故事將成為一本關於士兵毯子的虛構小說,毯子上刻畫著一名人物在世界各地旅行的痕跡,更以敘述網的形式擴展,超越了單一角色的個人故事,甚至以象徵的形式濃縮呈現。最後,這個男人的角色以及他轉變成地圖集的毯子,代表著其他數百萬個葡萄牙人,他們承載著事業心和對藝術的野心,其唯一出路就是在遙遠的領土上追求更好的生活。在頒給本書的獎項中,評審團成員之一——一名羅馬尼亞的演員曾經說:☞《畫鳥的人》此書象徵著歐洲人被滿足內心的必要性,進而驅動到遠處旅行,幫助他們在大海的另一邊建立新的世界。這些話精準地描述了當我將毯子從地面拿起時,那條毯子給我的靈感之一。

這種毯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種由羊毛編織而成、重量相對較輕的灰色長方形毯子。葡萄牙沒有直接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可怕的衝突,但依然遭受劇烈影響。在這場戰爭中,葡萄牙表面上與同盟國同一陣線,私底下卻幫助了軸心國。絕對的獨裁者薩拉查向葡萄牙人民表示——我使我們免於戰爭,但非免於飢餓。是的,這裡曾經有嚴重的饑荒及文化知識的缺乏。葡萄牙當時是個缺乏學校的地方,對於文化資產的取得及行為的解放可以說是相當地缺乏,甚至根本沒有。華特.狄亞斯的故事即是存在於這樣的背景中——一個沒有赴戰的士兵,加入了外圍歐洲世界的行列。當時的葡萄牙選擇中立,因沒有參與這場造成歐洲悲劇的行動而獲得利益,然而這卻導致了兩個惡果:獨裁政權延長了三十年,且延緩了歐洲民主政體的發展。直至一九七四年,因為康乃馨革命,才得以進入到言論自由的國家行列,放棄了在非洲和亞洲的帝國主義形式殖民地,漸漸轉變成獨立和自由的國家。

書中角色——華特的女兒,後來憶起父親時,便是在這個時期、成為歐盟成員之一的年代,並經歷了深度的結構轉變。當時葡萄牙一邊適應布魯塞爾的共同指示,並為自己選擇一個最好的計畫以增強國家競爭力,外圍局勢促使它對其他洲的國家敞開國門,優越的地理位置更使其一躍成為迎接世界各地遊客的大廳。
在該國南部的法羅,即 ☞《畫鳥的人》的故事場景所在地,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徵兆的。對於書中的老父親而言,這是戲劇性的。他在家族中的獨裁統治,就如同里斯本獨裁者的權威形象。但對於那些離家不歸的兒女們,這些轉變卻是自由的。那名孫女,即華特的女兒,她就是留下來支持地方轉型的人,並扮演著時代橋樑的角色。她回顧了歷史同時也預測了未來。時間長河裡的古老鄉村,是可以被看見並等待人發掘的,就如同一間活的博物館,參觀者可以觀察到這裡過去的生活,新科技世界中的孩子們,能以適當的距離窺探玻璃櫥窗後面的務農器具。而未來又將有所不同。

但是一本書的寫作從不會誤導作者。就算時間流轉,優秀的讀者們依然能感受到歷史和社會時空營造出的故事氛圍,將戲劇衝突聚焦於士兵的毯子上。在持續下雨的三天裡,壁爐石頭上晾著的毯子烤乾了,毛料上的泥漬乾涸成地圖集,也因此決定了這個故事及敘述的型態。即使我已經不在毯子前寫作,士兵的身影仍會出現在我欲寫作的頁面前。最終,這些頁面是虛構的,包括了士兵回憶的連續片段,虛構的士兵過虛構的生活,而虛構的女兒則想抹去父親不良的聲譽。我原本要遠離雨水而寫,但雨好像持續且永久地飄落紙上,而我沿著這些頁面,將這個虛構又不完美的愛情故事塑形,就像人類的大愛,它是不完美卻偉大的。

文學小說的巨大貢獻在於將原本被認為是創造的故事轉化為經驗豐富的敘事,每一次的閱讀都像一種不孤寂的內在創造,彷彿與其他生命牽連在一起,又像是自家姊妹一般。並不是所有故事都擁有這種力量。為何有些作品能達到這種人性相互連結的祕密精粹,有些卻不能,這始終是個謎。寫下這些內容的人希望 ☞《畫鳥的人》》屬於前者,但這無非是個美好的夢想,如同華特.狄亞斯的野心。
▌畫鳥的人 (誠品限量作者燙金簽名版)
☞ 對於人際相處與家族故事有興趣的人,請盡情享受閱讀...

▌閱讀更多經典文學書單
☞《佩德羅.巴拉莫》是一本傳奇的小說,最後讓它的作者也變成傳奇
✦
▌延伸閱讀
☞原來外國人也在讀我們的書!已經被翻譯成外文的華語創作,你怎麼能不讀
☞災難還是會再來,春天也是|《那年春天,在車諾比》,靜謐而非殘敗的森林
☞ 這是因為我們還能夠假設──張亦絢談《九歌109年小說選》
☞河水記得自己的軌跡:與布莉.貝內特談《消失的另一半》 #誠品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