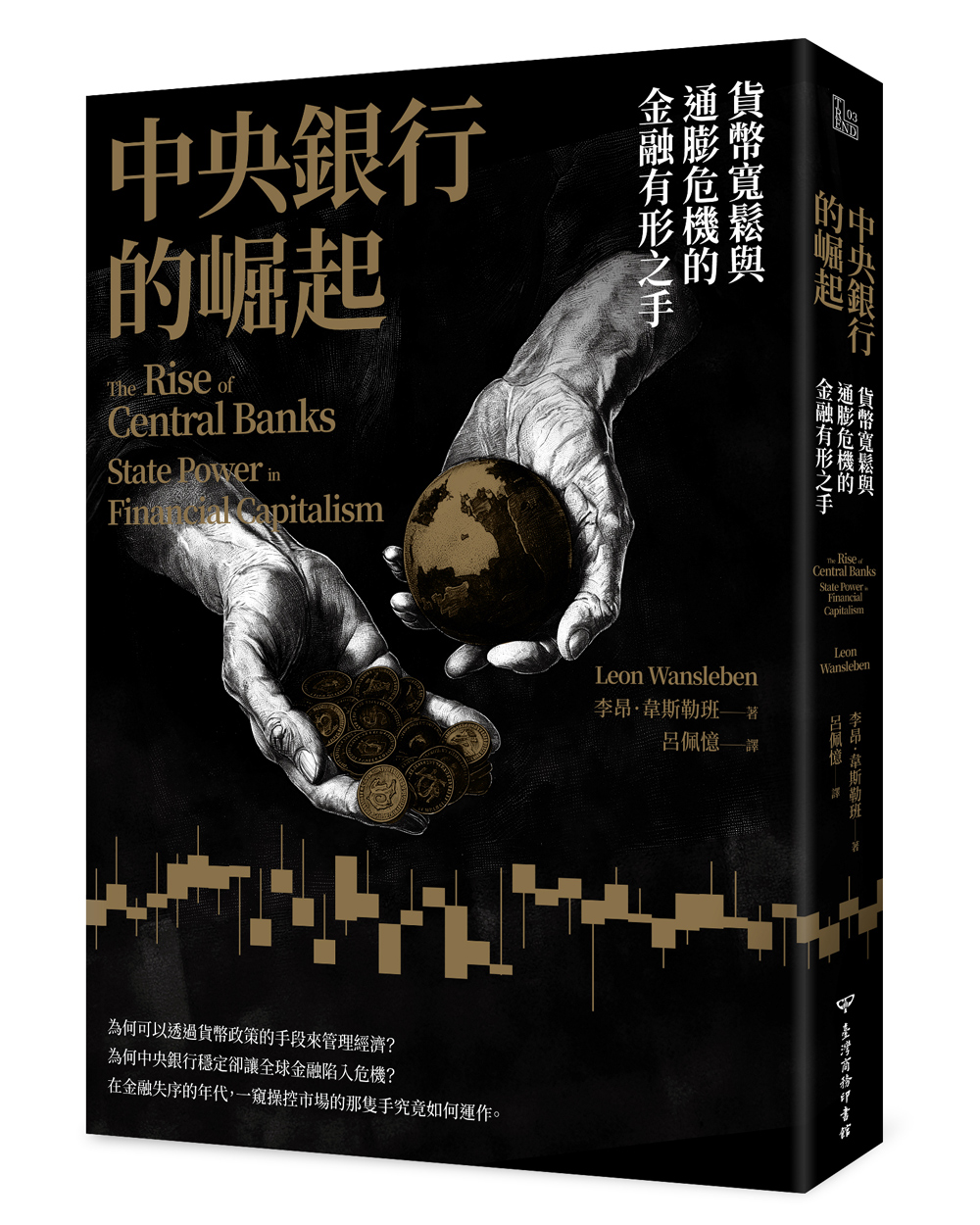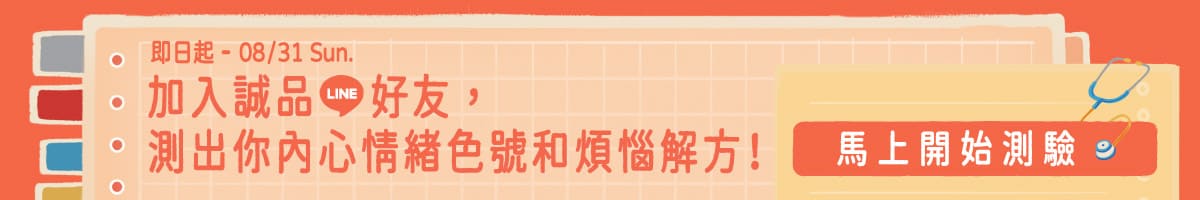專訪《末日》作者弗格森:應對極端災難,我們該建立的是韌性社會
撰文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時代》雜誌百大人物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書《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Doom)是他對威脅人類的各種極端災難——從地質災難、生物災難、科技災難到地緣政治災難——的一次總體檢。當我問他目前市面上已經出現數百本與疫情相關的書籍,《末日》與其他的書籍有何不同時,弗格森立刻表示,《末日》所關心者不僅是疫情,還包括各種極端災難,他的目的在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視角,以便對於未來仍可能出現的各種極端災難,能夠有所預期。

但是所謂從歷史回顧極端災難以便獲得啟示,並非如此直覺。向歷史學習從來並非易事,任何兩個事件在歷史上通常是獨一無二的,以史為鑒必然需要經過材料的取捨與詮釋,以便找出不同類型的異同;不同史觀與採用不同方法的歷史學家,有時會從同樣的歷史對比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不過弗格森在本書中強調的不僅於此,他更進一步說明,極端災難之所以「極端」,正是因為極其罕見。這時不僅歷史的類比需謹慎,而且人類必須更懷謙卑之心,因為人類的大腦天生就不適合對這種事情加以估計。
自從賽門(Herbert Simon)提出理性的有限性以來,學者便花費大量心力尋找人類真正的決策模式與經濟學的理性模式有何差異。《雜訊》作者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找到了大量的例子,說明人類思考與決策的真正過程其實充滿了偏誤。我們經常以為教育與經驗能夠幫助我們克服這些偏誤,以此說明學校與實作的重要性,可惜很多時候並非如此。

例如兩人在1979年發現「計畫謬誤」(planning fallacy)十分常見。所謂的計畫謬誤是指人們在對完成某項任務所需要的各種因素加以預測,以便對所需的時間、金錢及人力等加以規畫,結果發現人們經常低估完成任務所需要的時間與金錢,這在男性中更為常見。不僅學生低估完成作業所需要的時間,即使是經驗老到的工程師也經常低估完成標案的時間與金錢。
對於極端災難也是如此。弗格森認為我們經常搞錯事件的本質,錯將「灰犀牛」(gray rhino)誤認為「黑天鵝」(black swans)。前者是「顯而易見,人們卻視而不見的威脅」,而後者是「在我們有限的經驗看來,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都有人多次警告這種事遲早會發生,但是一旦發生,人們又宣稱「極其罕見,聞所未聞」。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的大腦被演化與教育搞出很多心理偏誤,很容易以為大多數現象就像人類的身高一樣呈常態分布,但這種預測很多時候會失準。我舉一個例子就好:森林大火的發生機率通常不是常態分布,而是冪次分布。世上沒有『典型』的森林大火,森林大火的統計分布圖不是我們熟悉的那種大多數火災集中在平均值附近的鐘形曲線,而是對數曲線。如果你把火災規模取對數,它跟發生頻率就會呈一條直線」。
在這種情形下,弗格森認為我們需要一個一般性的框架來理解這種極端災難,這種框架無法由單一學科推導而來,而必須結合政治、經濟、歷史、心理、技術與組織等各方面知識,才能從災難的歷史中習得真正有用的訊息,而《末日》的目的正在提供這樣一種框架。
❐ 所有的天災,也都是人禍
具體來說,弗格森認為有極端災難的歷史告訴我們以下五件事情:
第一,大多數的災難無法預測。從地震到戰爭再到金融危機,歷史上各種重大動盪的特徵,就是呈現隨機或冪次分布,這並非風險,而是不確定性。
第二,災難的形式千變萬化,不可能依賴尋常手段來加以控制。承認這點有助於我們更靈活地應對災難。台灣、南韓與疫情初期的以色列會成為2020年應對疫情最優秀的國家,並不是巧合,因為它們都是長期面對鄰國壓力等多重威脅的國家。
第三,理解網絡十分重要。並非所有的災難都會擴及全球,但是當人類社會的網絡連結愈發緊密,災害就就愈容易蔓延。當社會有了連結緊密的網絡,就需要設計良好的斷路器,才能在危機發生時迅速減少網絡的連結度,又不致於徹底粉碎或癱瘓整個社會。
第四,這場疫情暴露的問題不僅侷限於公衛官僚的失能,而是「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普遍都有的問題。理解與設計官僚組織對於應對極端災難十分重要。
第五,歷史經驗顯示,只要社會碰到龐大的壓力,宗教或近乎宗教的意識形態就很容易興起,妨礙理性的應對措施。

弗格森在此強調的是,所謂天災與人禍的分野具有誤導性質,所有的天災也都是人禍,即使是完全源自大自然的衝擊,對人類的影響程度也和人類的行為有關,更不用說,許多的金融災難或是地緣政治災難,主要是出自人類社會或政治體系,因此我們需要理解官僚組織或是社會網絡如何影響極端災難。
提到政治體系,很容易令人想起領導者與高高在上的政客所造成的災難,例如很多人批評美國前總統川普在疫情發生之初,在美國的聯邦體制下造成的領導危機,擴大了疫情初期的危害。政治領袖固然重要,但是弗格森在《末日》中更加強調的是容易為人所忽略的官僚失能。他在書中以「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的例子說明官僚體系在極端災難中的地位。

▶︎1983年,執行任務的挑戰者號太空梭(圖片來源:NASA)
挑戰者號太空梭於1986年1月28日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上空爆炸,從發射到太空梭解體只花了七十三秒多一點,雖然只有七人死亡,卻成了美國史上最有名的空難之一。

▶︎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墜毀(圖片來源:Kennedy Space Center)
挑戰者號為什麼會爆炸?事發之後,有人猜測是當白宮施壓航太總署,硬是要在雷根總統發表國情咨文之前發射,或是佛羅里達出現的異常低溫,還有人說是負責團隊陷入「群體迷思」(groupthink)。但事後發現,這些均非主因。
後來是由費曼(Richard Feynman)在羅傑斯委員會的首次聽證會中,以簡單的實驗表明,失事的原因是O形環在低溫下失去彈性以致無法保持密封。很多人都在《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中讀過這個故事。

事實上航太總署內部早就警告過要注意這種危機。
根據費曼的描述,他在羅傑斯委員會裡面的調查簡直就是學者版的《華府風雲》(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費曼認為事故的發生,是航太總署那些把工程師當耳邊風的中階官僚造成的,因為在太空總署工程師眼中有百分之一發生率的災難性故障,被中階官僚堅持認定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發生率。
弗格森認為費曼所找到造成太空梭事故的中階官僚失靈並不罕見,在很多其他的極端災難中,都可以見到類似的情形,由政治所造成的極端災難經常是由領導危機與中階官僚危機所共同組成的。
弗格森舉的例子耳熟能詳,也十分有趣,不過令我想起另一篇馬洛尼(Michael Maloney)和穆勒林(Harold Mulherin)於2003年在《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發表的有趣論文。
挑戰者號太空梭於1986年1月28日爆炸,2月11日,費曼就在聽證會上說明了失事原因,前後僅花了區區兩個星期。
費曼的天才毋庸置疑,但是馬洛尼和穆勒林卻驚訝地發現,股市在挑戰者號爆炸後一小時內就找到了這場悲劇的「凶手」。挑戰者在股票市場上有四大供應商:洛克希德(Lockheed)、馬丁.瑪麗埃塔(Martin Marietta)、洛克威爾(Rockwell)和莫頓.賽奧科爾(Morton Thiokol),其中賽奧科爾是O型環的供應商。在爆炸後8分鐘,道瓊通訊社發布快報。21分鐘時,洛克希德的股價下跌了5.05%,馬丁.瑪麗埃塔下跌2.83%,洛克威爾下跌6.12%。
但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O型環供應商賽奧科爾的股價出現大量拋售,股市因此暫停交易,當股市於12:36恢復交易時,賽奧科爾的股價已下跌6%且跌勢未止,其他三家公司的股價則從最初的下跌中開始反彈。
當天交易結束時,股市已經確定太空梭爆炸的主要責任屬於賽奧科爾,該公司當天的報酬率為-11.86%,比太空梭爆炸前三個月的平均報酬率差了6個標準差以上。相較之下,其他三間公司的報酬率雖然也是負的,但是與爆炸前三個月的平均報酬率相差不到2個標準差。更驚人的是,事後估算賽奧科爾因股價下跌所損失的市值,幾乎等於其因為失去太空總署訂單所影響的市值,股市在此展現驚人的效率與準確性!
❐ 市場機制在極端災難中的角色
所謂的市場,不僅如經濟學家寇斯(Ronald Coase)所建議的,市場與層級組織代表兩種可以彼此替代的資源分配方式,同時也是適應環境變化的兩種替代的制度安排。例如海耶克(Fredrich Hayek)即表示「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最主要的是,在特定的時空中如何快速適應」,而巴納德(Chester Barnard)則提出,組織內的有意識的合作是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關鍵。也就是無論是海耶克或是巴納德,都認為環境變化如此不可測,絕非個人所能預測,因此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只是兩人強調的制度正好相反,一者是市場,另一為組織。

更具體來說,人類的制度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一端是組織,另一端是市場,官僚組織是組織形式的一種,股市則是市場制度的一種。在組織與市場之間,還有各種的中間形式,例如社會網絡等等。綜觀弗格森在《末日》中探討各種與極端災難有關的制度,主要是強調組織與網絡,例如官僚組織、政治組織、企業組織,或是社會網絡、科學社群、貿易網絡與社區網絡等等,但是卻鮮少提及市場。不免令人懷疑,究竟弗格森如何看待市場在極端災難中的角色?
弗格森回答道,他在《末日》中提到過市場,例如他曾引用《正義的理念》作者阿馬蒂亞.庫馬爾.沈恩(Amartya Sen)對於饑荒的著名研究,認為以「市場失靈」的角度來看待饑荒是錯誤的,因為許多饑荒發生在缺乏自由市場制度的國家。至於《末日》並未大量提及市場,乃是因為他在另一本著作《貨幣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中探討了金融保險的歷史。該書已經將市場視為應對特定災難的解方,因此《末日》中不再重述。

既然弗格森提到沈恩了,我於是繼續追問:「沈恩認為大饑荒與缺乏民主相關,但是您不同意。您認為民主也許可以處理許多災難,但是對於極端事件無能為力。由於大饑荒屬於極端災難,所以即使民主也無法應對。那麼,應對災難的最佳政體是什麼?我忍不住想起中國與台灣在防疫上的對比。西方國家有不少人為了證明民主國家也有能力應對Covid-19,因此用民主台灣的案例來對比威權中國,您同意這樣的對比嗎?」

弗格森立刻表示:「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個人更喜歡去年台灣應對疫情的方式!我只是希望台灣今年能夠在疫苗政策有更積極的作為。我對民主的看法與邱吉爾相同,那就是『民主是除其他制度之外的最差制度』。令人費解的是,民主國家應對疫情的成效遠不如其應對饑荒。當然,民主制度也可能導致軍事大災難。我並非主張威權政體具有任何優勢(這是錯誤的!),而是民主國家需要當心自由社會之中出現的危險:從官僚主義僵化,到惡意與錯誤訊息導致的網絡資訊疫情。」
❐ 疫情與紓困方案對經濟的影響
其實《末日》中雖然並未過多強調市場,不過弗格森並未忽略疫情對於經濟的影響,他花了一整章的篇幅來討論疫情將如何影響各國經濟。弗格森認為Covid-19或許比較不像多數人拿來類比的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反而更像1957~58年的亞洲流感。鑑於疫情對於經濟的重大影響,以及世界各國政府推出龐大的補助與經濟振興方案,不免令人猜想,也許疫情不僅影響各國的經濟,同樣會影響各國的經濟思潮。例如《貿易的取捨》作者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認為,自19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或稱為華盛頓共識、市場教義派)已經宣告死亡,因為「新自由主義導致高度金融化、不平等和不穩定的經濟體系,而今這些經濟體系缺乏能力應對當今最重大的挑戰」。那麼對弗格森來說,目前哪些最流行的想法會因疫情而改變?這種變化是短期的或是長期的現象?

弗格森解釋他的確認為疫情已經對我們的經濟思維產生影響,就像他在《末日》第十章寫道:「(紓困法案的財政與貨幣擴張)政策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大得不可思議。在短短幾個月內,現代貨幣理論(MMT)和全民基本收入(UBI)這兩個最極端的經濟觀點,似乎都變成了主流。」
至於這些影響會持續多久,取決於我們面對的通貨膨脹問題有多嚴重。如果中央銀行的專家是正確的,也就是通膨只會是暫時性的,那麼現代貨幣理論與全民基本收入的影響就可能會持續。但如果這些近期的政策最後像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所警告的,將導致經濟過熱並讓通膨失控,那我們就會又回到貨幣政策與債務管控的古典原則。另一項經濟轉變(而且很可能早在2020年前就已經發生),就是「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的回歸。也就是政府更公開地干預市場,引導投資與資金向「綠色新政」或更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這些政策都會導致價格扭曲與低效率,但影響在最初還不會那麼顯著。簡而言之,我們有可能正在重蹈1960年代與1970年代的覆轍,卻在心裡期待這回會有不同的結果。
❐ 以早期預警系統,應對官僚失能造成的極端災難
接下來我將焦點轉到官僚組織——這是《末日》的核心概念之一。對弗格森來說,中階官僚失能,不僅本身可能造成災難(如挑戰者號的爆炸),也是擴大災難範圍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某些西方國家對抗疫情)。因此弗格森認為,要應對不可預知的不確定性,需要普遍準備各種災難,而不是單純地依靠專業化的官僚組織。除此之外,社會還需要具有韌性,能夠抵抗災害並且能夠從損害中回復。
然而,建立具有普遍性以及韌性的組織或是網絡,意謂著組織、網絡以及社會具有剩餘資源(slackness),這些平時看似無用的資源,能夠在環境劇烈變動時提供彈性與韌性,可是這對許多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來說是相當昂貴的。弗格森認為對早期預警的快速反應是達成韌性的關鍵,但這也不容易。因此問題在於如何在彈性和成本之間找到平衡,是否有辦法以具有效率的方式建構具有韌性的系統?如果將之放大到國際,那麼這種系統與國際組織和國際合作體系的關係又是如何?
弗格森的回答應該會令台灣人驚喜。很顯然的,弗格森並不想落入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科學主義與日本式管理孰優孰劣的爭辯;與其討論何謂最佳系統,不如不斷努力尋求改進之道。他說:「這個嘛,目前大量的資源浪費在某些人精美模型所做的錯誤未來災難預測,以及由此衍生的精心防災之上。因此,我所提到的『對早期預警的快速反應』方法實際上可以節省資源。台灣防疫的經驗證明,我們能夠使用科技與網路平台來增加政府的課責性,在我看來,用這種方法處理公共政策的問題,並不十分昂貴。基本上,二十世紀的國家已經發展到了極度缺乏效率、而且官僚組織笨重且肥大的地步,在新科技面前已經顯得落伍。我們愈快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公共服務的模式,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愈低,效果也愈好。」
❐ 台灣經驗的可貴
弗格森所指的台灣運用科技與網路平台的可貴經驗究竟是什麼?為何他認為這是二十一世紀建立韌性社會應對極端災難的典範?除了原書正文之外,在弗格森特別為台灣版所寫的長序中,有更清楚的敘述。
他在批評美國的防疫措施之後,話鋒一轉,說:
「相比之下,台灣政府的活力實在令人驚豔。雖然他們的防線終於在五月被新一波病毒給攻破,但接下來情勢的發展又繼續展現了新型智慧政府的效能。在唐鳳等人的努力下,台灣已經備妥了一系列接觸者追蹤程式,包含官方的『臺灣社交距離』APP。名為g0v零時政府的開源網絡也快速架起一個網站,匯聚來自醫院等單位的資源,以追蹤縱疫情蹤跡。人民也自發性地利用Google地圖製作了『風險地圖』,協助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唐鳳前述作法中最吸引人之處,是她著重於利用軟體和智慧型手機,強化一般民眾而非政府的防疫能力,這種精神源自於2014年三一八學運,別名『太陽花運動』。(⋯)唐鳳認為,這和中國大陸利用人工智慧打造的監控帝國正好相反:『從民主和人權的角度來看,他們發展得愈遠,就退步得愈多。我們的感想是:「呃,千萬不要追隨他們。」』唐鳳的防疫方針不只讓人民獲得更完善的資訊,也讓政府更能掌握實際狀況。而在面對假訊息和錯誤訊息上,她則是以諷刺取代審查。她曾在去年表示:『我們不是用外出限制來擊退傳染病,也不是用言論限制來擊退資訊疫病。』她的辦法是採用『妙語對抗謠言』,也就是用好玩的迷因對抗假新聞。如果西方政治家想了解民主的未來,他們真的該常去台北走走。」

儘管美國被弗格森視為與台灣相對的防疫失敗案例,但是美國畢竟代表世界資訊科技最前沿,擁有最先進的資訊技術,以及最多最有價值的IT公司。在另一方面,中國的資訊科技也一日千里,但中國政府卻建立了一個數位極權的國家。我因此好奇弗格森會如何評價這三個國家在利用資訊科技防疫的三種不同作法。
弗格森並未將美國、中國與台灣三種模式對立起來,而是認為真正的選擇只有兩種:中國模式或台灣模式,而不將美國視為一種獨立的理想型模式。他說,所有已開發國家都必須決定如何利用技術達成治理,必須在兩種模式間做出選擇:一方是集權、利用人工智慧的監控型國家,也就是中國模式;另一方是分權、部分基於區塊鏈系統,而對公民賦權的國家,也就是台灣模式。美國自然會選擇台灣模式,那種想要以二十世紀的官僚體系來運作二十一世紀經濟體的想法,注定是徒勞無功的。

我試圖在弗格森的回答中拓展空間,在「台灣模式」中進行更細緻的區分。我問弗格森,說他提到台灣和南韓能夠結合快速的大規模篩檢、接觸者追蹤和隔離潛在患者,成功在初期就控制住病毒擴散,一年多來都不必實施有礙經濟活動的外出限制。不過就在《末日》英文版出版之後,台灣和南韓都受到所謂第四波Covid-19疫情的攻擊。不過不同的是,台灣很快成功地拉平了曲線,而南韓仍掙扎於難以控制疫情。此外,雖然越南並非民主國家,但是在疫情初期的表現和台灣與南韓一樣傑出,但是至今越南的疫情同樣出現破口,染疫人數甚至超過南韓。為何台灣、南韓與越南在防疫初期的表現並無二致,如今卻產生重大分歧?
弗格森並未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而是表示如同他在《末日》中所說,Covid-19疫情暴露出不同體系的優缺點。台灣與南韓在控制病毒擴散上的表現十分傑出,但是在疫苗注射上則落後於不少國家。相對的,英國與美國在控制病毒擴散上表現極差,但是在疫苗注射上則是身處全球最佳國家之列。這大致上反映出歐美與東亞之間的差異。

最後我將問題拉回到《末日》書中最後章節所討論的地緣政治問題,請他評論一下自己的觀點。我提到弗格森批評某些西方人士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傳統看法過於幼稚,而他們所提倡的「競合」方式也大有問題。多年來,台灣身處中國軍事威脅的第一線,又時時面對中國對台灣的認知戰與外交孤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行事風格有第一手的觀察,因此不難找到弗格森意見的支持者。
但是不可諱言的,弗格森的意見並非主流,至少對美國政府來說是如此。畢竟當國務卿布林肯對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箎說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將會是「在應該競爭的領域競爭,在可以合作的領域合作,在必須對抗的領域對抗」時,誰會不同意他的觀點呢?
這種認同不僅是意識形態上的,也是方法上的。至少對學習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者而言,「競合」是一個政策上十分自然的結果。經濟學家相信經濟活動乃是基於自願交易的互惠活動,在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譬喻上,建構其理論基礎。今天,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經常利用同樣的工具(賽局理論)來建構模型、理解世界,進而推出政策涵意。在這種情形下,相信「競合」無疑是十分自然的結果,因為「競合」的概念原本就植基於學者所用的理論與工具中。
因此要說服他們相信中共打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他們所使用的邏輯,或是他們的作法很多時候並無效果,實非易事。在這種情形下,要如何說服其相信弗格森的論點?說服需要的是策略還是全新的理論?就目前兩黨難得在中國政策上達成共識的局面下,弗格森認為他的意見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成為主流觀點嗎?
弗格森對此充滿信心,他樂觀的程度令我微微地感到意外:他認為「競合」路線可行的幻覺,不久後就會因為接觸到中國政府的行為而破滅,擁抱熊貓派將很快認清現實。事實上,在弗格森寫作《末日》的那年裡,現實反覆地證實他對第二次冷戰的看法,這點只要看看北京以及中國媒體對喀布爾陷落的反應就一清二楚。他說曾經和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使用「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來形容那些經濟熊貓派,這些人將很快每週都被現實打臉!
✦
▌點圖收聽|迷誠品Podcast 〈Truth or Bias〉特別企畫
☞人際網絡解密:朋友多不等於人脈廣!

你是否感覺朋友的人緣總是比你好?一篇錯誤的醫學論文竟然造成一個世代的兒童傳染病蔓延?人與人之間傳遞的,不只是各種連結,還有疾病、風險⋯⋯本集將透過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系教授馬修.傑克森 (MATTHEW O. JACKSON) 的著作《人際網絡解密》,從電腦科技、數學、社群、人類行為學等面向,解析人際網絡在政治、金融商業、社會平等、疫苗接種等各種層面的決策考量及影響。
來賓|馮勃翰(台大經濟系副教授)
主持|Amber(誠品職人)
☞對抗世界的隱患——記者談假新聞與真相製造

「在假新聞讓一切真假難辨的時候,我們正需要一本堅實的報導之作,在訊息的流沙中不致暈眩。」
網路世代蓬勃發展後,假新聞已不是「新聞」,人們仍不自覺地被聳動標題吸引,而這些片面之詞卻是引發社會分裂的導火線!本集將從政治、商業到社會心理層次,探討「真相產業」如何在全球演變,成為亟需理解的新課題。
來賓|劉致昕(國際新聞記者)
主持|李惠貞(獨角獸計畫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