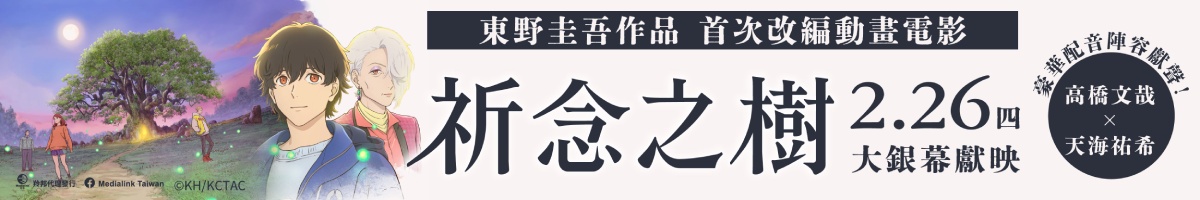专访《末日》作者弗格森:应对极端灾难,我们该建立的是韧性社会
撰文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时代》杂志百大人物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书《末日:致命瘟疫、核灾、战争与经济崩盘,灾难对人类社会的启示》(Doom)是他对威胁人类的各种极端灾难——从地质灾难、生物灾难、科技灾难到地缘政治灾难——的一次总体检。当我问他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数百本与疫情相关的书籍,《末日》与其他的书籍有何不同时,弗格森立刻表示,《末日》所关心者不仅是疫情,还包括各种极端灾难,他的目的在提供一个完整的历史视角,以便对於未来仍可能出现的各种极端灾难,能够有所预期。

但是所谓从历史回顾极端灾难以便获得启示,并非如此直觉。向历史学习从来并非易事,任何两个事件在历史上通常是独一无二的,以史为鉴必然需要经过材料的取舍与诠释,以便找出不同类型的异同;不同史观与采用不同方法的历史学家,有时会从同样的历史对比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不过弗格森在本书中强调的不仅於此,他更进一步说明,极端灾难之所以「极端」,正是因为极其罕见。这时不仅历史的类比需谨慎,而且人类必须更怀谦卑之心,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适合对这种事情加以估计。
自从赛门(Herbert Simon)提出理性的有限性以来,学者便花费大量心力寻找人类真正的决策模式与经济学的理性模式有何差异。《杂讯》作者康纳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找到了大量的例子,说明人类思考与决策的真正过程其实充满了偏误。我们经常以为教育与经验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偏误,以此说明学校与实作的重要性,可惜很多时候并非如此。

例如两人在1979年发现「计画谬误」(planning fallacy)十分常见。所谓的计画谬误是指人们在对完成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各种因素加以预测,以便对所需的时间、金钱及人力等加以规画,结果发现人们经常低估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与金钱,这在男性中更为常见。不仅学生低估完成作业所需要的时间,即使是经验老到的工程师也经常低估完成标案的时间与金钱。
对於极端灾难也是如此。弗格森认为我们经常搞错事件的本质,错将「灰犀牛」(gray rhino)误认为「黑天鹅」(black swans)。前者是「显而易见,人们却视而不见的威胁」,而後者是「在我们有限的经验看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都有人多次警告这种事迟早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人们又宣称「极其罕见,闻所未闻」。主要的原因在於「我们的大脑被演化与教育搞出很多心理偏误,很容易以为大多数现象就像人类的身高一样呈常态分布,但这种预测很多时候会失准。我举一个例子就好:森林大火的发生机率通常不是常态分布,而是幂次分布。世上没有『典型』的森林大火,森林大火的统计分布图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大多数火灾集中在平均值附近的钟形曲线,而是对数曲线。如果你把火灾规模取对数,它跟发生频率就会呈一条直线」。
在这种情形下,弗格森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一般性的框架来理解这种极端灾难,这种框架无法由单一学科推导而来,而必须结合政治、经济、历史、心理、技术与组织等各方面知识,才能从灾难的历史中习得真正有用的讯息,而《末日》的目的正在提供这样一种框架。
所有的天灾,也都是人祸
具体来说,弗格森认为有极端灾难的历史告诉我们以下五件事情:
第一,大多数的灾难无法预测。从地震到战争再到金融危机,历史上各种重大动荡的特徵,就是呈现随机或幂次分布,这并非风险,而是不确定性。
第二,灾难的形式千变万化,不可能依赖寻常手段来加以控制。承认这点有助於我们更灵活地应对灾难。台湾、南韩与疫情初期的以色列会成为2020年应对疫情最优秀的国家,并不是巧合,因为它们都是长期面对邻国压力等多重威胁的国家。
第三,理解网络十分重要。并非所有的灾难都会扩及全球,但是当人类社会的网络连结愈发紧密,灾害就就愈容易蔓延。当社会有了连结紧密的网络,就需要设计良好的断路器,才能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减少网络的连结度,又不致於彻底粉碎或瘫痪整个社会。
第四,这场疫情暴露的问题不仅局限於公卫官僚的失能,而是「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普遍都有的问题。理解与设计官僚组织对於应对极端灾难十分重要。
第五,历史经验显示,只要社会碰到庞大的压力,宗教或近乎宗教的意识形态就很容易兴起,妨碍理性的应对措施。

弗格森在此强调的是,所谓天灾与人祸的分野具有误导性质,所有的天灾也都是人祸,即使是完全源自大自然的冲击,对人类的影响程度也和人类的行为有关,更不用说,许多的金融灾难或是地缘政治灾难,主要是出自人类社会或政治体系,因此我们需要理解官僚组织或是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极端灾难。
提到政治体系,很容易令人想起领导者与高高在上的政客所造成的灾难,例如很多人批评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疫情发生之初,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下造成的领导危机,扩大了疫情初期的危害。政治领袖固然重要,但是弗格森在《末日》中更加强调的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官僚失能。他在书中以「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的例子说明官僚体系在极端灾难中的地位。

1983年,执行任务的挑战者号太空梭(图片来源:NASA)
挑战者号太空梭於1986年1月28日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上空爆炸,从发射到太空梭解体只花了七十三秒多一点,虽然只有七人死亡,却成了美国史上最有名的空难之一。

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坠毁(图片来源:Kennedy Space Center)
挑战者号为什麽会爆炸?事发之後,有人猜测是当白宫施压航太总署,硬是要在雷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前发射,或是佛罗里达出现的异常低温,还有人说是负责团队陷入「群体迷思」(groupthink)。但事後发现,这些均非主因。
後来是由费曼(Richard Feynman)在罗杰斯委员会的首次听证会中,以简单的实验表明,失事的原因是O形环在低温下失去弹性以致无法保持密封。很多人都在《别闹了,费曼先生:科学顽童的故事》中读过这个故事。

事实上航太总署内部早就警告过要注意这种危机。
根据费曼的描述,他在罗杰斯委员会里面的调查简直就是学者版的《华府风云》(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费曼认为事故的发生,是航太总署那些把工程师当耳边风的中阶官僚造成的,因为在太空总署工程师眼中有百分之一发生率的灾难性故障,被中阶官僚坚持认定只有十万分之一的发生率。
弗格森认为费曼所找到造成太空梭事故的中阶官僚失灵并不罕见,在很多其他的极端灾难中,都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形,由政治所造成的极端灾难经常是由领导危机与中阶官僚危机所共同组成的。
弗格森举的例子耳熟能详,也十分有趣,不过令我想起另一篇马洛尼(Michael Maloney)和穆勒林(Harold Mulherin)於2003年在《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发表的有趣论文。
挑战者号太空梭於1986年1月28日爆炸,2月11日,费曼就在听证会上说明了失事原因,前後仅花了区区两个星期。
费曼的天才毋庸置疑,但是马洛尼和穆勒林却惊讶地发现,股市在挑战者号爆炸後一小时内就找到了这场悲剧的「凶手」。挑战者在股票市场上有四大供应商:洛克希德(Lockheed)、马丁.玛丽埃塔(Martin Marietta)、洛克威尔(Rockwell)和莫顿.赛奥科尔(Morton Thiokol),其中赛奥科尔是O型环的供应商。在爆炸後8分钟,道琼通讯社发布快报。21分钟时,洛克希德的股价下跌了5.05%,马丁.玛丽埃塔下跌2.83%,洛克威尔下跌6.12%。
但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O型环供应商赛奥科尔的股价出现大量抛售,股市因此暂停交易,当股市於12:36恢复交易时,赛奥科尔的股价已下跌6%且跌势未止,其他三家公司的股价则从最初的下跌中开始反弹。
当天交易结束时,股市已经确定太空梭爆炸的主要责任属於赛奥科尔,该公司当天的报酬率为-11.86%,比太空梭爆炸前三个月的平均报酬率差了6个标准差以上。相较之下,其他三间公司的报酬率虽然也是负的,但是与爆炸前三个月的平均报酬率相差不到2个标准差。更惊人的是,事後估算赛奥科尔因股价下跌所损失的市值,几乎等於其因为失去太空总署订单所影响的市值,股市在此展现惊人的效率与准确性!
市场机制在极端灾难中的角色
所谓的市场,不仅如经济学家寇斯(Ronald Coase)所建议的,市场与层级组织代表两种可以彼此替代的资源分配方式,同时也是适应环境变化的两种替代的制度安排。例如海耶克(Fredrich Hayek)即表示「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如何快速适应」,而巴纳德(Chester Barnard)则提出,组织内的有意识的合作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关键。也就是无论是海耶克或是巴纳德,都认为环境变化如此不可测,绝非个人所能预测,因此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只是两人强调的制度正好相反,一者是市场,另一为组织。

更具体来说,人类的制度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端是组织,另一端是市场,官僚组织是组织形式的一种,股市则是市场制度的一种。在组织与市场之间,还有各种的中间形式,例如社会网络等等。综观弗格森在《末日》中探讨各种与极端灾难有关的制度,主要是强调组织与网络,例如官僚组织、政治组织、企业组织,或是社会网络、科学社群、贸易网络与社区网络等等,但是却鲜少提及市场。不免令人怀疑,究竟弗格森如何看待市场在极端灾难中的角色?
弗格森回答道,他在《末日》中提到过市场,例如他曾引用《正义的理念》作者阿马蒂亚.库马尔.沈恩(Amartya Sen)对於饥荒的着名研究,认为以「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看待饥荒是错误的,因为许多饥荒发生在缺乏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至於《末日》并未大量提及市场,乃是因为他在另一本着作《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中探讨了金融保险的历史。该书已经将市场视为应对特定灾难的解方,因此《末日》中不再重述。

既然弗格森提到沈恩了,我於是继续追问:「沈恩认为大饥荒与缺乏民主相关,但是您不同意。您认为民主也许可以处理许多灾难,但是对於极端事件无能为力。由於大饥荒属於极端灾难,所以即使民主也无法应对。那麽,应对灾难的最佳政体是什麽?我忍不住想起中国与台湾在防疫上的对比。西方国家有不少人为了证明民主国家也有能力应对Covid-19,因此用民主台湾的案例来对比威权中国,您同意这样的对比吗?」

弗格森立刻表示:「相较於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个人更喜欢去年台湾应对疫情的方式!我只是希望台湾今年能够在疫苗政策有更积极的作为。我对民主的看法与邱吉尔相同,那就是『民主是除其他制度之外的最差制度』。令人费解的是,民主国家应对疫情的成效远不如其应对饥荒。当然,民主制度也可能导致军事大灾难。我并非主张威权政体具有任何优势(这是错误的!),而是民主国家需要当心自由社会之中出现的危险:从官僚主义僵化,到恶意与错误讯息导致的网络资讯疫情。」
疫情与纾困方案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末日》中虽然并未过多强调市场,不过弗格森并未忽略疫情对於经济的影响,他花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讨论疫情将如何影响各国经济。弗格森认为Covid-19或许比较不像多数人拿来类比的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反而更像1957~58年的亚洲流感。监於疫情对於经济的重大影响,以及世界各国政府推出庞大的补助与经济振兴方案,不免令人猜想,也许疫情不仅影响各国的经济,同样会影响各国的经济思潮。例如《贸易的取舍》作者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自19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或称为华盛顿共识、市场教义派)已经宣告死亡,因为「新自由主义导致高度金融化、不平等和不稳定的经济体系,而今这些经济体系缺乏能力应对当今最重大的挑战」。那麽对弗格森来说,目前哪些最流行的想法会因疫情而改变?这种变化是短期的或是长期的现象?

弗格森解释他的确认为疫情已经对我们的经济思维产生影响,就像他在《末日》第十章写道:「(纾困法案的财政与货币扩张)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在短短几个月内,现代货币理论(MMT)和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两个最极端的经济观点,似乎都变成了主流。」
至於这些影响会持续多久,取决於我们面对的通货膨胀问题有多严重。如果中央银行的专家是正确的,也就是通膨只会是暂时性的,那麽现代货币理论与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响就可能会持续。但如果这些近期的政策最後像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所警告的,将导致经济过热并让通膨失控,那我们就会又回到货币政策与债务管控的古典原则。另一项经济转变(而且很可能早在2020年前就已经发生),就是「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的回归。也就是政府更公开地干预市场,引导投资与资金向「绿色新政」或更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这些政策都会导致价格扭曲与低效率,但影响在最初还不会那麽显着。简而言之,我们有可能正在重蹈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覆辙,却在心里期待这回会有不同的结果。
以早期预警系统,应对官僚失能造成的极端灾难
接下来我将焦点转到官僚组织——这是《末日》的核心概念之一。对弗格森来说,中阶官僚失能,不仅本身可能造成灾难(如挑战者号的爆炸),也是扩大灾难范围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某些西方国家对抗疫情)。因此弗格森认为,要应对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需要普遍准备各种灾难,而不是单纯地依靠专业化的官僚组织。除此之外,社会还需要具有韧性,能够抵抗灾害并且能够从损害中回复。
然而,建立具有普遍性以及韧性的组织或是网络,意谓着组织、网络以及社会具有剩余资源(slackness),这些平时看似无用的资源,能够在环境剧烈变动时提供弹性与韧性,可是这对许多开发中国家及未开发国家来说是相当昂贵的。弗格森认为对早期预警的快速反应是达成韧性的关键,但这也不容易。因此问题在於如何在弹性和成本之间找到平衡,是否有办法以具有效率的方式建构具有韧性的系统?如果将之放大到国际,那麽这种系统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体系的关系又是如何?
弗格森的回答应该会令台湾人惊喜。很显然的,弗格森并不想落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科学主义与日本式管理孰优孰劣的争辩;与其讨论何谓最佳系统,不如不断努力寻求改进之道。他说:「这个嘛,目前大量的资源浪费在某些人精美模型所做的错误未来灾难预测,以及由此衍生的精心防灾之上。因此,我所提到的『对早期预警的快速反应』方法实际上可以节省资源。台湾防疫的经验证明,我们能够使用科技与网路平台来增加政府的课责性,在我看来,用这种方法处理公共政策的问题,并不十分昂贵。基本上,二十世纪的国家已经发展到了极度缺乏效率、而且官僚组织笨重且肥大的地步,在新科技面前已经显得落伍。我们愈快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公共服务的模式,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愈低,效果也愈好。」
台湾经验的可贵
弗格森所指的台湾运用科技与网路平台的可贵经验究竟是什麽?为何他认为这是二十一世纪建立韧性社会应对极端灾难的典范?除了原书正文之外,在弗格森特别为台湾版所写的长序中,有更清楚的叙述。
他在批评美国的防疫措施之後,话锋一转,说:
「相比之下,台湾政府的活力实在令人惊艳。虽然他们的防线终於在五月被新一波病毒给攻破,但接下来情势的发展又继续展现了新型智慧政府的效能。在唐凤等人的努力下,台湾已经备妥了一系列接触者追踪程式,包含官方的『台湾社交距离』APP。名为g0v零时政府的开源网络也快速架起一个网站,汇聚来自医院等单位的资源,以追踪纵疫情踪迹。人民也自发性地利用Google地图制作了『风险地图』,协助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唐凤前述作法中最吸引人之处,是她着重於利用软体和智慧型手机,强化一般民众而非政府的防疫能力,这种精神源自於2014年三一八学运,别名『太阳花运动』。()唐凤认为,这和中国大陆利用人工智慧打造的监控帝国正好相反:『从民主和人权的角度来看,他们发展得愈远,就退步得愈多。我们的感想是:「呃,千万不要追随他们。」』唐凤的防疫方针不只让人民获得更完善的资讯,也让政府更能掌握实际状况。而在面对假讯息和错误讯息上,她则是以讽刺取代审查。她曾在去年表示:『我们不是用外出限制来击退传染病,也不是用言论限制来击退资讯疫病。』她的办法是采用『妙语对抗谣言』,也就是用好玩的迷因对抗假新闻。如果西方政治家想了解民主的未来,他们真的该常去台北走走。」

尽管美国被弗格森视为与台湾相对的防疫失败案例,但是美国毕竟代表世界资讯科技最前沿,拥有最先进的资讯技术,以及最多最有价值的IT公司。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资讯科技也一日千里,但中国政府却建立了一个数位极权的国家。我因此好奇弗格森会如何评价这三个国家在利用资讯科技防疫的三种不同作法。
弗格森并未将美国、中国与台湾三种模式对立起来,而是认为真正的选择只有两种:中国模式或台湾模式,而不将美国视为一种独立的理想型模式。他说,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必须决定如何利用技术达成治理,必须在两种模式间做出选择:一方是集权、利用人工智慧的监控型国家,也就是中国模式;另一方是分权、部分基於区块链系统,而对公民赋权的国家,也就是台湾模式。美国自然会选择台湾模式,那种想要以二十世纪的官僚体系来运作二十一世纪经济体的想法,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我试图在弗格森的回答中拓展空间,在「台湾模式」中进行更细致的区分。我问弗格森,说他提到台湾和南韩能够结合快速的大规模筛检、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潜在患者,成功在初期就控制住病毒扩散,一年多来都不必实施有碍经济活动的外出限制。不过就在《末日》英文版出版之後,台湾和南韩都受到所谓第四波Covid-19疫情的攻击。不过不同的是,台湾很快成功地拉平了曲线,而南韩仍挣扎於难以控制疫情。此外,虽然越南并非民主国家,但是在疫情初期的表现和台湾与南韩一样杰出,但是至今越南的疫情同样出现破口,染疫人数甚至超过南韩。为何台湾、南韩与越南在防疫初期的表现并无二致,如今却产生重大分歧?
弗格森并未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表示如同他在《末日》中所说,Covid-19疫情暴露出不同体系的优缺点。台湾与南韩在控制病毒扩散上的表现十分杰出,但是在疫苗注射上则落後於不少国家。相对的,英国与美国在控制病毒扩散上表现极差,但是在疫苗注射上则是身处全球最佳国家之列。这大致上反映出欧美与东亚之间的差异。

最後我将问题拉回到《末日》书中最後章节所讨论的地缘政治问题,请他评论一下自己的观点。我提到弗格森批评某些西方人士对於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看法过於幼稚,而他们所提倡的「竞合」方式也大有问题。多年来,台湾身处中国军事威胁的第一线,又时时面对中国对台湾的认知战与外交孤立,对於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风格有第一手的观察,因此不难找到弗格森意见的支持者。
但是不可讳言的,弗格森的意见并非主流,至少对美国政府来说是如此。毕竟当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箎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将会是「在应该竞争的领域竞争,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对抗的领域对抗」时,谁会不同意他的观点呢?
这种认同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也是方法上的。至少对学习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者而言,「竞合」是一个政策上十分自然的结果。经济学家相信经济活动乃是基於自愿交易的互惠活动,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譬喻上,建构其理论基础。今天,政治学者与经济学者经常利用同样的工具(赛局理论)来建构模型、理解世界,进而推出政策涵意。在这种情形下,相信「竞合」无疑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因为「竞合」的概念原本就植基於学者所用的理论与工具中。
因此要说服他们相信中共打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他们所使用的逻辑,或是他们的作法很多时候并无效果,实非易事。在这种情形下,要如何说服其相信弗格森的论点?说服需要的是策略还是全新的理论?就目前两党难得在中国政策上达成共识的局面下,弗格森认为他的意见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成为主流观点吗?
弗格森对此充满信心,他乐观的程度令我微微地感到意外:他认为「竞合」路线可行的幻觉,不久後就会因为接触到中国政府的行为而破灭,拥抱熊猫派将很快认清现实。事实上,在弗格森写作《末日》的那年里,现实反覆地证实他对第二次冷战的看法,这点只要看看北京以及中国媒体对喀布尔陷落的反应就一清二楚。他说曾经和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使用「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形容那些经济熊猫派,这些人将很快每周都被现实打脸!
▌点图收听|迷诚品Podcast 〈Truth or Bias〉特别企画
人际网络解密:朋友多不等於人脉广!

你是否感觉朋友的人缘总是比你好?一篇错误的医学论文竟然造成一个世代的儿童传染病蔓延?人与人之间传递的,不只是各种连结,还有疾病、风险本集将透过美国史丹福大学经济系教授马修.杰克森 (MATTHEW O. JACKSON) 的着作《人际网络解密》,从电脑科技、数学、社群、人类行为学等面向,解析人际网络在政治、金融商业、社会平等、疫苗接种等各种层面的决策考量及影响。
来宾|冯勃翰(台大经济系副教授)
主持|Amber(诚品职人)
对抗世界的隐患——记者谈假新闻与真相制造

「在假新闻让一切真假难辨的时候,我们正需要一本坚实的报导之作,在讯息的流沙中不致晕眩。」
网路世代蓬勃发展後,假新闻已不是「新闻」,人们仍不自觉地被耸动标题吸引,而这些片面之词却是引发社会分裂的导火线!本集将从政治、商业到社会心理层次,探讨「真相产业」如何在全球演变,成为亟需理解的新课题。
来宾|刘致昕(国际新闻记者)
主持|李惠贞(独角兽计画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