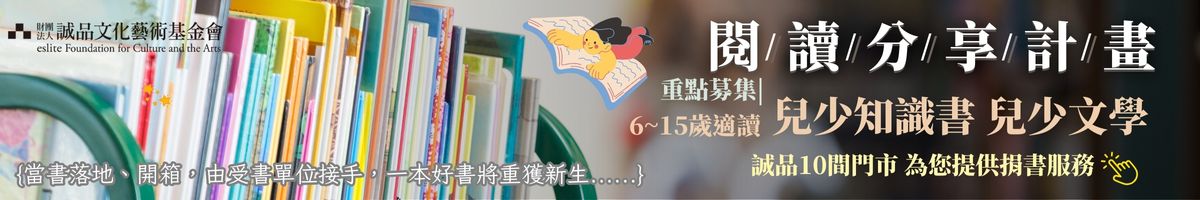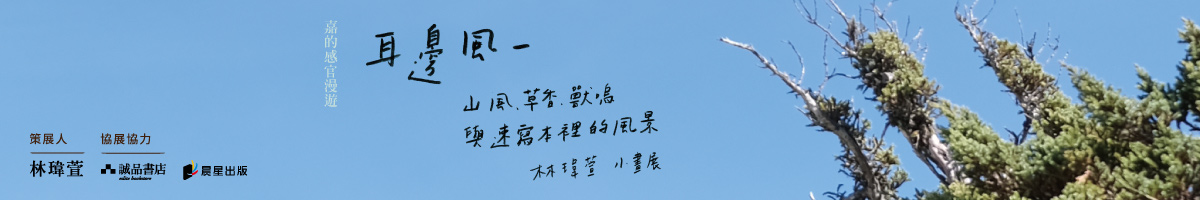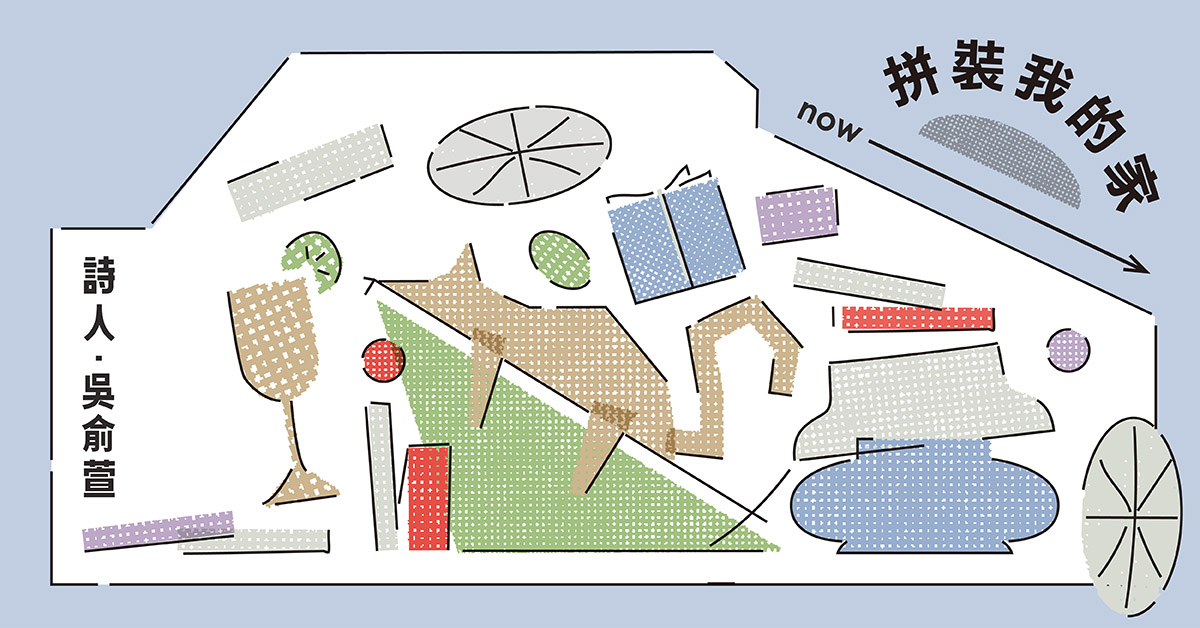「有時候在戰爭和衝突時期,善良也可能是一種特權」──專訪《寂靜風暴》作者陳惠珊 (Vanessa Chan)
撰文 皇冠文化作者|陳惠珊 (Vanessa Chan) 出版|皇冠文化
風暴的開始總是微小,
一張紙條,一杯熱茶,一次凝視,一份純真──
Q1. 您在開頭提到本書故事發想,起源於2019年底參與的書寫工作坊,想請問是什麼原因驅使您繼續完成這個故事?
陳惠珊:我當時正參加一個創意寫作碩士班的寫作研習營。我的指導老師是一名叫做瑪麗—海倫娜.博蒂諾(Marie-Helene Bertino)的小說家。她要全班同學寫一則有關一個人重複做某件事的故事,所以我就寫了篇關於一個日占時期的馬來西亞少女要通過一連串的檢查哨回家的短篇故事。我都不好意思說,我只把那故事當作個寫完就算的回家作業,上完課就扔到一旁了,但瑪麗給了我張字條,說她在我的故事裡看到更多潛力——覺得我像嘗試想拼湊出一部長篇小說。她鼓勵我繼續寫。我之前從沒打算要寫長篇小說,所以感覺還蠻衝擊的,但我接受了她的建議。疫情期間,我在紐約完成了《寂靜風暴》。那段日子裡,我無法回到馬來西亞的家人身邊。寫作過程中,我經歷了無比的喪親之痛,我母親和伯父都在那段期間過世了。現在,那份寫完就算的回家作業成了我小說中的第四章。是一位老師讓我動筆寫出這本小說,證明了老師和導師的影響有多重要。
Q2. 《寂靜風暴》中寫到許多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殖民馬來西亞的情況。想請問您在書寫這段歷史時,身邊是否有可以借鏡參考的事蹟?又或者您是如何收集資料,將史料撰寫成文學作品呢?
陳惠珊:在馬來西亞,我常說我們的祖父母是藉由「不說」來愛我們。被日本占領的那段經歷大多都被用「閉口不談」和「往前看」的方式掩蓋了起來。就連我從教科書上讀到的事實都很少,我知道日本人很巧妙地騎自行車自北方的泰國入侵,同時英國的大砲卻是對著南方的大海,也知道他們在入侵時會投下寫著「亞洲人的亞州」的紅色宣傳單,那既是警告,也是戰鬥的號召。
儘管如此,作爲我父親那邊的長孫,我跟祖父母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多年來,我從祖母那兒收集到各種有趣但常常也很可怕的軼事,而且她都是用一種就事論事的口氣說的。其中有件事是她十二歲的時候,在她騎腳踏車回家的路上,有枚空襲炸彈落在她後方,差個三十秒就會是掉在她腳踏車上。她用一種幾乎像是小朋友的開心口氣說她的兄弟姊妺沒發現她已經回家了,在瓦礫間挖了好幾個小時,要找她的殘骸,以為她死了。
當我終於開始在2020年初寫這本書時,沒有一間圖書館或檔案館有開放。所以我首先是靠我的記憶還有以前從家人那兒聽來的故事來寫,那些東西已內化成我一部分,但從未真正付諸紙筆。我在澳洲的叔叔寄了本馬來西亞的老照片給我。最後,當我終於能回家時,我有機會在祖母過世前和她核對許多事。我爸爸是個歷史愛好者,替我查證了許多細節,像是1930和40年代用的是什麼樣的餐具和鞋子。我想呢,一如既往地,我的小說變成了樁家族任務。
Q3. 本書分別從賽瑟莉、小棗、亞伯和茉莉四個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也讓我們看見不同角色的際遇與變化。請問您為何會決定以這種方式書寫,您想透過這四個角色讓讀者看見什麼樣的歷史樣貌?
陳惠珊:我來自一個吵吵鬧鬧、愛八卦又很戲劇化的家庭,所有人老是同時開口(我爸有39個堂兄弟姊妹!),因為這樣,我想我一直都很喜歡多視角的故事,開始常看似各不相干,最後卻兜到了一塊兒。《寂靜風暴》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有太多故事要說,單一視角感覺會限制故事的廣度,無法反映出我說這個故事所需的時間跨度,還有那些角色當時所處的多個地理位置。我也利用多重視角來反映出我筆下的人物是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遇見日本殖民者,還有這些不同的關係是如何改變我的角色。
Q4. 賽瑟莉是《寂靜風暴》中的靈魂人物,您在書中描寫許多關於這個角色的情感糾結,以及愛恨交織的複雜情緒。想請問您為何會特別從這個女性,又帶有豐富情欲的視角切入歷史,甚至影響馬來西亞被日本殖民的命運呢?
陳惠珊:原因其實很私人。我第一次開始寫這本小說時,它本是一個關於三個悲傷的馬來亞孩子度過二戰末期的故事。這本來也沒什麼,歷史本就充滿悲傷和戰爭,我們需要這樣的空間來寫下這些故事,無論它們有多悲慘。但在寫作期間,疫情肆虐,我母親因久病過世。我遭受巨大的傷痛,而且又被困著,無法回到馬來西亞。我必須給自己找些快樂,所以我為自己寫出了賽瑟莉,一位母親、一名間諜、一個女人,她必須四處奔走,做出決定(無論是好是壞!),擁有我並不覺得自己擁有的自主權與快樂與決策能力。此外,描寫女性的慾望和憤怒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我想要塑造一個全面的角色,她會愛、會恨、決定要採取行動,即便那些事是有瑕疵的。
Q5. 《寂靜風暴》中的小棗聰明冷靜,遇見高橋先生後,兩人在互動上也令表面上平靜如水的小棗,充滿許多內心活動。可否請您描述一下小棗對高橋先生的想法,以及您安排高橋先生的出現用意為何?
陳惠珊:當我和祖母討論二戰時,她總會小心翼翼地說人民和他們的政府是不同的。我祖母在二戰期間見證過殘酷的暴力,她總說那時日本士兵的暴行是很可怕的,但不是所有在馬來西亞的日本人都是殘暴的。她自己就和日本客戶與同事建立起親密的友誼,而這份友誼也一直持續到她生命終末。高橋先生是我將這細微的差異引入對日本的描述的一個方法,想反映出我們不能因其政府和歷史,就把一整個國家都視為壞蛋。有時候,人是矛盾的,善良的同時卻又同流合污;努力不去那麼做,卻又努力去那麼做。但有時候,在戰爭和衝突時期(以小棗為例),善良也可能是一種特權,令人憎恨,又令人混亂。
Q6. 亞伯的際遇令人心疼,他親身經歷了殘忍的對待,又憑藉著堅忍的意志回家。想請問您在撰寫亞伯的故事時,是以什麼樣的心境書寫?
陳惠珊:亞伯的故事是發生在建造死亡鐵路的勞改營中,它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研究,但同時也是最難寫的。不像其他故事,關於日占時期的勞改營生活,有許多的報導和描述,因為勞改營裡關了許多歐洲戰俘。不像書裡其他部分必須仰賴我祖母的記憶和口述歷史,因為歷史對亞洲事件的記載並不如歐洲那樣多。我能透過研究來填補亞伯的部分,但研究過程依舊令人心碎,而且殘暴。知道我的祖先、我的家人、我認識的人不得不以這種方式生活,遭受這種暴力,我覺得很害怕、很難過。
Q7. 雖然本書是以馬來西亞(被殖民者)的立場書寫,但在您筆下作為殖民者的日本將軍藤原茂同樣也有多重樣貌,並非只是冷血殘暴的惡人。他曾對賽瑟莉說:「日本將為你們國家帶來一個新未來,一個妳連想像都無法想像的未來!」請問您相信藤原勾勒的願景嗎?您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承諾?
陳惠珊:事後來看很簡單,我當然不相信啦!我現在知道(歷史也已告訴我們)日占時期是個充滿暴力、飢餓和酷刑的年代,是歷史的一大污點。但重要的是,要明白賽瑟莉,也就是《寂靜風暴》中的主角,是一個生活在1930年代的女性,一名馬來亞的妻子與母親,只能重複做著她母親與母親的母親之前做過的事。她對自己和家人有更多的期望,卻沒有一個行為範本告訴她要怎麼替自己做出改變。然後,有人(藤原茂)出現了,向她展示了一個不同的世界,而且理論上,她是可以為了建立這樣的世界有所貢獻。從這角度來看,她會擁抱這樣一個有缺陷的未來,也是有其道理的。
Q8. 本書是您首次在臺出版的文學作品,可否請您向臺灣讀者說幾句話?
陳惠珊:親愛的台灣讀者,非常榮幸我的作品能與你們見面。我曾多次造訪台灣,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你們是個如此友善、美味(食物!),而且善良又美麗的地方。並且,你們同樣也能深切體會,另一個國家覺得自己有權左右你們的命運,還不停持續這樣的威脅,是什麼樣的感覺。希望你會喜歡跟著賽瑟莉、小棗、亞伯和茉莉一同進入他們的世界,也希望你能記住他們的故事。感謝你的閱讀!
(文章首圖來源:Photo by Joshua Fuller on Unsplash)
關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閱讀與風格採買的書店誌,紙本刊物每月1日準時於全台誠品書店免費發刊。每期封面故事討論一個讀者關心的生活與消費的議題,推薦給讀者從中外文書籍、雜誌、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線上閱讀《提案on the desk》
☞《誠品書店eslite bookstore》粉絲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