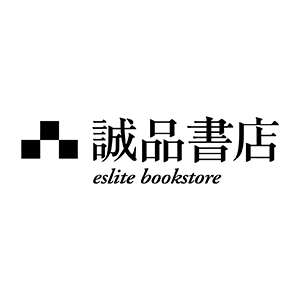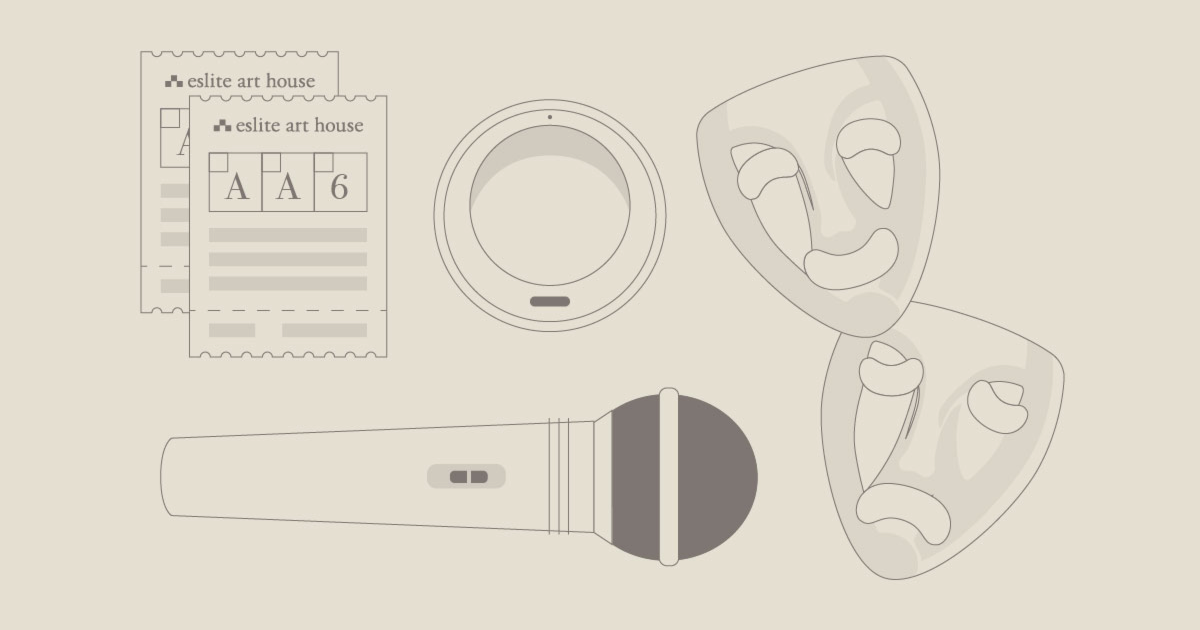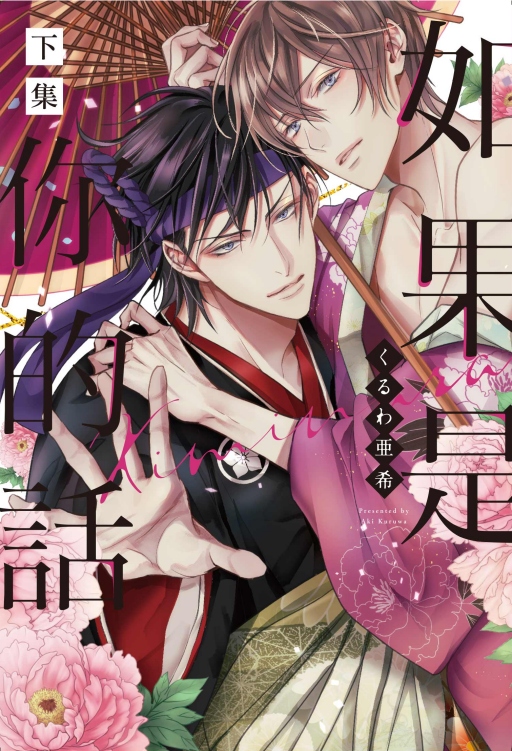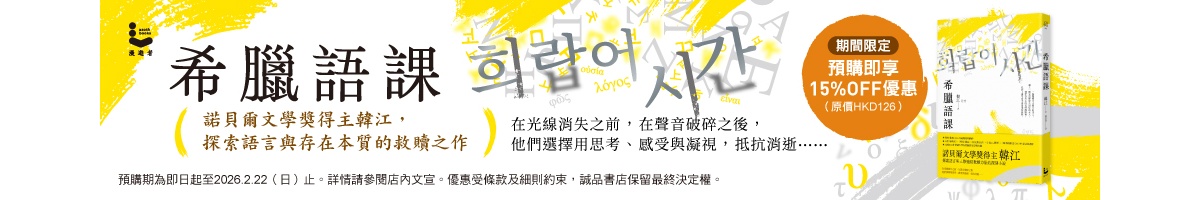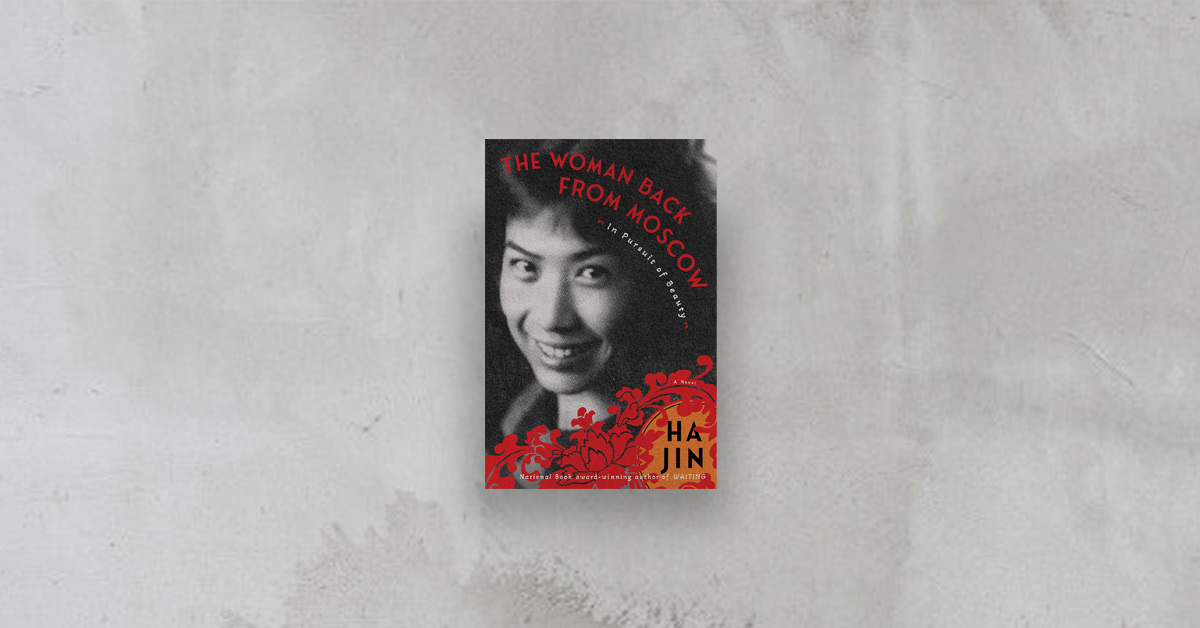誠品主題專欄|從《國寶》的歌舞伎劇目談起,兼談原著與電影之別
撰文 香港誠品書店據聞吉田修一為了寫就《國寶》,在與樂屋親身擔任幕後「黑衣」三年,以深入了解歌舞伎的世界。在原著中,及名的劇目不計其數,電影就挑選了六齣最具代表性的劇目重點拍攝,分別是《積戀雪關扉》、《連獅子》、《藤娘》、《二人道成寺》、《曾根崎心中》、《鷺娘》,每齣劇目並非單純是日本劇場藝術的展現,而是經過作者及導演用心安排,演出順序與劇中主角喜久雄、俊介藝術人生的每個關鍵時刻互為表裡,連動故事情節、人物感情的發展。下文將逐齣分析,過程兼談原著小說與電影的分別。
一、《積戀雪關扉》
小說和電影起首都是以日本黑幫立花組的新年聚會開場,喜久雄作為立花組老大權五郎的兒子,與跟班德次上演了《積戀雪關扉》的其中一幕,作為他的首次亮相。《積戀雪關扉》屬於舞蹈劇,於1784年首演,講述了在小町櫻花盛開的逢坂關,叛賊大伴黑主冒充關兵衛潛伏於少將宗貞身邊,意圖覬覦天下,關口一棵過百年的櫻花樹藏身了櫻花妖,櫻花妖假裝成遊女墨染挑逗關兵衛,逼其現出真身,與自己對決。《積戀雪關扉》作為第一齣歌舞伎劇目,其實是揭示關於假身分/隱瞞/背叛的命題(「這墨染與關兵衛,其實都是假身份」),因為就在喜久雄下台後不久,立花組遭到另一黑幫宮下組突襲,權五郎被手下辻村背叛槍殺,與《關扉》大伴黑主潛伏作亂有暗合之處,而回頭去看喜久雄扮演墨染時的唱詞:
「深雪櫻花影如幻
旦為朝雲暮行雨
怎奈何,花開花落薄倖名……
誰憐我,自幼長在煙花巷」
遊女之於煙花巷;喜久雄之於波譎雲詭的黑道之家,勢力更迭朝雲暮雨,一夜間就家破人亡,電影改編要喜久雄親眼目睹父親之死,父親要他好好「看」,「看」拳(權)如何彰顯與落空,正視黑道世界/人間世的殘酷——一切都是道統、階級、派別,沒有老大,你什麼都不是。正如他之後要進入的梨園世界,其實和黑道的秩序別無二致(沒有父母,就如無頭鬼一樣)。
二、《連獅子》
《連獅子》在小說和電影之間的改動較大:小說裡《連獅子》是喜久雄襲名丹波屋第三代半二郎時演出的劇目,電影將其提前至喜久雄剛抵大阪,仍未拜師學藝,首見俊介之際。初踏劇場的他,穿過藤花滿佈的長廊,一切如此新鮮,直至他在後台偷看赤毛、白毛兩頭獅子搖曳長毛,被歌舞伎的世界震攝。筆者認為這個改動相當的好。《連獅子》是一齣關於父母愛與期望的劇目,狂言師會在舞台講述關於古代的習俗——獅子將幼獅反覆推下懸崖,只有那些能夠從峽谷中爬回來的才有資格被繼續養護,過程中,獅子會不時俯視山谷,擔憂幼獅的安危,嚴苛之中蘊含望子成龍的心緒。
這裡演出《連獅子》,透露半二郎對俊介的寄望,也是他之後會離家出走,飽經歷練再重回歌舞伎界的預告。最重要的一點,是深化電影一直加強的,關於「血脈」的話題。喜久雄與俊介初見於劇場,而非丹波屋的改動,顯示二人的起步點不同,俊介一出現已經前呼後擁,與父親共演,丹波屋繼承人的身份相當突出,喜久雄更多被視為俊介的「陪練」。《連獅子》是點題,後續對「血脈」的探討更多,例如俊介到後台探望代演《曾根崎心中》的喜久雄,原著寫喜久雄想飲俊介的「血」:「我啊,現在最想要的,是俊寶的血。我好想把俊寶的血倒在杯子裡大口大口喝。」電影卻在其後增加了一句「守護我的血脈都沒有了」。失去父母,也等於失去父母提供的庇蔭,這裡換指歌舞伎世襲的正統與資源,也可以說是世代流傳下來歌舞伎演員的賦能。
師母角色的改動也是證明。原著的師母比電影溫和,得知喜久雄要演出《曾根崎心中》,只發出弱弱一句「怎麼可以……」,但電影改為「怎可以讓一個『外人』代你演……」;喜久雄要襲名,師母心酸希望他拒絕,但埋怨過後還是心軟應允(「我認命了。誰叫我是貪得無厭的演員的老婆、母親、師娘。既然這樣,什麼髒水爛泥我都吞。」)。「老婆」、「母親」、「師娘」,在小說中,師娘心中有喜久雄的位置,電影卻只有責備(「奪走俊寶的一切,太污穢了。」)
身份問題可以說是電影的主軸,也是喜久雄一生的課題,生於黑道中貴,父親卻橫死;襲名丹波屋,卻被視為忘恩負義,師傅歿後備受冷待;落泊鄉野仿藝伎演出維生,卻連被狎玩都遭到質疑(「你這假貨」),難怪他會向天泣訴「我在看什麼?到底在看什麼?」
三、《二人藤娘》、《京鹿子娘道成寺》
《藤娘》同樣是舞蹈劇,《藤娘》舞台後方的松樹纏繞上巨大低垂的紫藤蔓是標誌性裝置,據聞是由名演員第六代尾上菊五郎在小村雪岱繪畫的道具帳上加以佈置,強化道具與情景的融合,讓觀眾投身其中,反映了歌舞伎舞台藝術自江戶時期以來跳躍式的進步。
原著中喜久雄和俊介的成名作是《京鹿子娘道成寺》,在電影改為先演《藤娘》,被三友社長賞識後再到大阪出演《道成寺》,此舉令劇情的過渡更加自然。《藤娘》開場,少女頭戴斗笠,肩披藤枝自畫作中現身,背後是盛開的花卉,此齣劇目的特色是唱詞會介紹日本近江八景,還有藤花精略含醉意的舞蹈,風格偏調皮活潑,傾訴少女初戀的純真與羞澀,及對男子多情的怨嗔,非常適合來影射主角兩位女形新星在歌舞伎界初出茅廬的景象。到了《京鹿子娘道成寺》,劇目的技能要求更高——主角二人會不斷透過「引拔」變裝(輔助人員「後見」抽線,演員配合時機褪去外層戲服),以展現少女在不同戀愛階段的心情,同時需獨自一個人跳一小時的舞蹈,正好向觀眾交代主角二人在技藝上的成長。重點是,電影裡俊介是展演手持三連斗笠的輕快舞蹈(「花笠踊」);喜久雄則表演以絹為鏡傾訴思念與期待面見戀人的舞蹈(「恋の手習い」),是劇目的重點場景,預示二人將有不同的發展前路。同時,《道成寺》的結局,少女戀慕寺廟憎侶被背叛,妒嫉與怨恨交加下化成巨蛇,將藏身吊鐘內的憎侶燒死,亦正好預告二人之後會因妒忌而分離,展開長達多年的互鬥。
《道成寺》演出了兩次,初演展現了青春的激烈與競爭,再演時,俊介已經重返丹波屋,喜久雄亦重返歌舞伎界,十幾年後的二人習藝更為成熟,變得合拍且遊刃有餘,但同時也逃不開結局的悲色,二人臨上吊鐘之際,俊介就因糖尿病影響倒地,下次再踏上台時,已經失去了一條腿了……
四、《曾根崎心中》
《曾根崎心中》在六套歌舞伎當中唯一一套世話物(呈現江戶時代的平民生和風俗),由著名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所寫,最初為木偶戲(人形淨琉璃),講述遊女阿初和醬油店伙計德兵衛殉情的故事。《曾根崎心中》在電影中同樣演了兩次,具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原劇目主題所表達的對命運的不甘、向死的意志,都是和故事轉折有莫大的關係,並重點塑造了俊介的角色。首次演出時,花井半二郎因為車禍揀選了喜久雄而非自己的兒子俊介代演,電影安排二人在《曾根崎心中》同步「覺醒」,覺醒何謂一個真正的歌舞伎演員——喜久雄在醫院病房,被師傅啟蒙,淚眼下終代入阿初的角色;俊介在原著中是聽到劇場人員在喜久雄採排後的閒言閒語,感到自己「體內丹波屋的血簡直清淡如水」,第一次意識到才藝勝過血統。電影將此深化,刻意捕捉俊介觀劇的一幕,當他親眼目睹自己與喜久雄的差距,當劇場唸到「他如此活下去也是徒然」,指的是劇人物,也是俊介,俊介第一次「死亡」,是「丹波屋繼承人之死」,他真真正正知道自己現在的能力擔不起名門之後的盛名,於是電影安排他在演出的一半落荒而逃。
第二次演《曾根崎心中》,俊介已經因為糖尿病截肢,其中一幕講遊女阿初伸腳,試探躲於房廊下的德兵衛是否決志與自己殉情,電影近鏡展現俊介因病發黑的腳掌,以及喜久雄毫不猶豫的緊握,是俊介對自己最後一次演出的堅持,當中有喜久雄的理解和成全,一個歌舞伎演員一腳缺失,另一亦即將留不住,「他如此活下去也是徒然」,俊介第二次死亡,是為「歌舞伎演員之死」,所以,當他耗盡全力來到最後一幕,呼喊出「殺了我吧」「就此了斷吧」是與自己的藝術生涯告別,而喜久雄亦將面對與自己亦敵亦友多年,鏡像般的靈魂伴侶訣別。
五、《鷺娘》
《鷺娘》講鷺鳥精化身身穿白無垢、持傘的少女,在大雪下出現,追求無果的戀情,最後回復鳥的姿態,因爲禁忌之戀受到地獄般的折磨。全劇一人獨舞,對演員的要求相當高。《鷺娘》在小說和電影的呈現不同,歌舞伎名家小野川萬菊在小說首次出場,是飾演《隅田川》的班女。班女的兒子不幸被拐走,遠道從京都至隅田川,卻獲悉兒子早已喪命,劇目重點在於呈現痛失愛兒的癲狂之狀。小說藉著《隅田川》去塑造小野川萬菊的攝人魅力,形容他是「很美的妖怪」,讓主角二人目睹他對歌舞伎、對美近乎入魔的追求,也為後續喜久雄沈溺於藝術世界留下了伏筆(喜久雄用嘲笑、逃避拒絕萬菊的孤絕)。如果小說的喜久雄害怕進入萬菊的境界;電影就是故意將二人用暗線連結。萬菊在電影的首次出場改為出演《鷺娘》,與喜久雄演《鷺娘》作結呼應,以示喜寶已經達到了萬菊當年的高度,成為了新一代的「人間國寶」。這點,從電影改編萬菊臨終前召見喜久雄可以印證。年幼的喜久雄滿臉憧憬看著《鷺娘》的雪景,以及蔓延至整個劇場的漫天飛雪——或可以稱之為「藝術的靈光」,最後他自己再跳《鷺娘》,他見到父親要他「好好看」卻失落的,在劇場重現的,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太美麗了」形容的是《鷺娘》,也是歌舞伎這門藝術自身。
小說的結局是出世的,喜久雄達至旁人無可企及的藝術高度,從劇場跳到大街,現實和演出對他而言已經緊密不分,可以說是有幾分寂寥;電影則相對入世,以一代宗師的演出作結,加重史詩式的調性。
從《積戀雪關扉》到《鷺娘》,不論是小說和電影,這些經典的歌舞伎劇目都為兩位主角的人生下了華麗註腳,演的既是角色,同時亦都是他們自己,種種情愫:傾慕、渴望、試探、好奇、怨懟、嫉妒、不忿、憐愛,從江戶跨時代至今,在《國寶》,在劇場,在喜久雄與俊介,及其他歌舞伎演員身上,仍然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