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的分享是我享受的」──专访莫子仪再谈《亲爱的房客》
撰文 釀電影:專為影癡而生的媒體(張硯拓)其实莫子仪是一个腼腆的人。
去年十一月在金马奖典礼上,获颁最佳男主角的他以一席庄重、大器的感言席卷网海,充分展现他对舞台的掌握;但如果阅读近年各种专访,又会感到十足的慎重,和甚至是距离感。怀抱这些想像,我在冬日的阳光里和他约在公馆的隐密咖啡厅,聊表演,聊《亲爱的房客》,聊在过快的时代如何守住个人节奏。一个下午下来,最大的发现是:原来莫子仪是个腼腆的人。
这腼腆背後,是对自己满满的想法能不能准确地/需不需要用力地被推到众人面前,的慎重思量。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酿电影(原标题:「这样的分享是我享受的」──专访莫子仪再谈《亲爱的房客》)}

*星系之一:「对我来说,表演是痛苦的」
在演员莫子仪的核心,是一句自我期许:「我想透过表演,让他人看见不同生命存在的样子。」
过去在许多访谈,他都说过中学时期叛逆、抽菸打架:「那时候升学至上,你成绩不好、翘课不念书,就是没有救的坏学生,不配拥有光明和希望。」直到接触表演,「我在戏剧里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的面向,人可以有很多样子,也有很多方式去评价,所谓分数还有操行成绩不代表一切,这让我觉得自由。」那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麽表演才华,遑论演员之路:「是价值观的开启,在困顿少年期把我接住,告诉我:世界其实很宽广。」
这般宽广,渐渐张开成一片星系,他在其中换上一张张面具,兀自飞行。不过,当我问起总是全然投入「成为」他人,有没有「体验不同人生」的新奇感?他斩钉截铁地否认了:「对我来讲表演是痛苦的,完全不觉得有趣。」
这麽杀的一句话在他说来,并不严厉,而是慎重。「当我扮演一个角色,要承受他所有喜怒哀乐,就像承载另一个生命,这是痛苦的,一点也没有开心或享受。」是因为任重道远?「因为这件事永远没有一个完成点。你表演得再好,都不可能完全呈现另一个人的人生。」
「譬如我今天要演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变成你,我只能趋近,不能僭越说我就是你。」所有角色都是揉合而成,是剧本上的样子、他的想像、加上「莫子仪」本身。「就算是我自己,也有不了解我的地方,某些时刻莫子仪会做出连我都预料不到的事。」身在表演的异度空间,他会逼「自己」尽量後退,才不会局限、甚至辜负了角色。
「但我选择做这件事,因为知道我可以,而且它有它的意义。我想透过表演,让他人看到不同生命存在的样子。这件事是重要的,但整个过程是不容易而且慎重的,痛苦而慎重──」说到这,他忍不住歉然地笑了:「我这样子是不是讲太严肃?」

*星系之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要跟世界相处的方式」
那天下午,莫子仪不断在掏心分享一大段之後,露出歉然而自觉的笑。这和舞台上那个顶天立地的影帝,判若两人。我说出我的观察:他曾说过不喜欢宣传,不想过度「解释」戏,想把诠释留给观众,但在各种访谈里、或像这样的下午,他又是推心置腹的。这会不会矛盾?「当然不矛盾。」
「我从以前到现在,长期在做一个抗争(歉笑 again),譬如之前宣传,因为处在资讯非常快速、消费性很高的环境,那些讯息传达不是为了理解作品或角色,而是要吸取焦点。那当然另有意义,但就不是我想做的,我不是为了展现自己各式各样的魅力存在的。」
努力抗争的莫子仪,不否认票房、点阅率很重要,「但如果静下心来,花一两个小时好好看一部电影,或十几分钟看一部短片──或像我们现在,有足够一个多小时针对几个话题好好聊,这样的分享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是享受的。」他反问,身为一个演员,「我只能在这个产业里当一个『明星』吗?我能不能同时有『人』的思辨和批判?」
「纵使这个社会因为资本主义,整个产业必须往标签化、标题化的方向,但我想至少在某些地方维持自己想要的样子──当然这会有所牺牲,我的曝光率、知名度、甚至收入都会更少,这些都是我知道,而且愿意的。」
他也强调这没有对错之分,都是因人而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有很多人不习惯快速的讯息和消费,或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喜欢纸本的书,他不习惯用电子产品跟人沟通,你不能说这些人就没资格活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想要跟这世界相处的方式,我觉得我在做的也是一样,我在维持一个跟世界抗衡的力量。」

*星系之三:「很多情感是没办法用言语解释的」
在《亲爱的房客》,健一同样在跟外在的世界、内在的风暴抗衡,但他的方式是「不沟通」──不辩驳,不反抗,面对误解和甚至责备皆然。这背後是怎样的心思?
「我自己觉得,人生中有很多情感是没办法用言语解释的。譬如健一对淑芳阿姨,他就算真的要解释清楚、请她原谅,而她也接受了,那也只是他辩论赢了,但实际上在心里,真的是这样吗?」
莫子仪顿了一下,更用情地说:「有时候说一句『我爱你』很简单,但要怎麽用行动或生命去表达?就像父母对小孩,是用整个青春和甚至一辈子去照顾你守护你,直到他们老去、离去,用四五十年的时间来告诉你我爱你,这个是更难,更珍贵的。」
这些付诸实行,远比言语上的倾诉、说服重要。「健一身上的情感,他曾经造成的伤害,同样没办法用『对不起』来交代。他能做的就是用一生身体力行,去赎罪也好,去爱去照顾也好,那些辛劳、无助、疲惫,一点一点累积,才能够证明。」他说如果是自己,可能也会做一样的事。
片中有场戏:健一被留在警察局讯问,终於离开後他飞也似地跑回家,在幽暗的客厅抱着悠宇说对不起:「那个画面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呈现一个小孩独自在家的孤单,然後终於有一点光进来,彷佛是透过画面告诉你:不论多麽黑暗,我都会像这样拥抱你。」
另一幕则是透露健一的心意:「他忙完一整天,煮完年夜饭吃完、照顾完家里,自己一个人回到顶楼加盖,镜头跟着健一的背影,直到他慢慢躺到床上。那个画面我可以感觉到健一的人生状态,一个角色的背影就是他承受的所有生命经历。」

*星系之四:「不管碰到什麽困难,他都是稳定军心的那个人」
十八岁那年,莫子仪遇见了郑有杰。「某方面我们很像,年轻时都有过不断批评、怀疑自我的阶段,害怕自己不够好。」2006 年两人合作《一年之初》,「当年有很多冲劲和叛逆,都留下痕迹在创作里。现在我们彼此都更柔软了,更包容,不会刻意彰显自我。」
2000 年,郑有杰以短片《私颜》出道,片中自导自演。「其实我一开始对有杰的印象──这样讲好像不太好(笑)──他年轻的时候很帅!二十几岁的他,真的可以直接当男一,但他不会耽溺於只当个漂亮的演员,他最想做的还是创作。」
二十年来,郑有杰持续导戏、编剧,偶尔也接演出,双重身分不互相垫高,而是相互理解。「他不会因为是得奖导演,就自认比别人懂,去参演别人的作品还是战战兢兢,尽力完成导演的指令。有几次还来问我的意见,我就觉得哇,有杰真的很谦虚又用心。」
这样的谦虚,也影响了「导演」郑有杰:「他很珍惜当演员遇过的困境,更能够设身处地,知道我们跟角色相处需要很长的心力,也感激我们的投入。我觉得人可以这样子,是很难得的。」
莫子仪再度形容,拍《房客》时郑有杰就像是这大家庭的爸爸:「不管碰到什麽困难,他都能稳定军心,而且不是严厉的,是很温柔、安稳告诉大家不用担心,任何状况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这个父爱的力量──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笑)──渲染了所有人,让大家相信无论如何有这个爸爸在,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完成。」

*星系之五:「我很感激跟他们工作过」
彷佛一家人的拍摄经验,以及戏里戏外「家」的主题,让我问起十二年前,莫子仪也曾参演姜秀琼执导的《艾草》。《艾草》里的妈妈潘丽丽,面对女儿带着混血外孙女归国,儿子莫子仪的同志性向又昭然若揭:「《艾草》的家人最後在彼此身上找到归宿,找回了爱,《房客》的健一就无法这麽幸运。」即使相隔十二年,同婚已经合法化了,「但是同志在社会、甚至家庭里受到的注目和压迫,并没有完全消失。」
两部片对照,莫子仪以「眼神」作关键索引:「在两个母亲身上,你可以看到她们其实『知道』──《艾草》里从妈妈的眼神,你可以看到她从知道到接受;而《房客》里的淑芳阿姨也早就知道,但是她不接受。」两部片也都有某种「爱」的延续──《艾草》是宋海对外甥女的爱,《房客》则是健一对悠宇的爱。
还有一个关於眼神的细节:「在《艾草》後面有一场戏,是妈妈跟姊姊和解,当时我只是站在旁边,但是秀琼很信任我们都在角色里,後来拍完我才发现:她在某一刻捕捉到我的表情,像是终於看到妈妈愿意接纳姊姊的感动,那根本不是『演』的,是自然而然的反应,但是她察觉到了,很精准拍下来。」
他形容秀琼导演的观察力敏锐,拥有独特的「鹰眼」;有杰导演则是谨慎、细腻地看待一切。「两部片都在讲家庭里『爱的结构』──当冲突发生时,我们是家人,能不能找到互相包容的方法?两部片都在讲家人跟爱。」他说两位都是影响他很深、很重要的导演,「我很感激跟他们工作过。」

*星系之六:「相信自己活着的力量,你就存在」
《亲爱的房客》之後,莫子仪已经马不停蹄又完成三部片,其中短片《黑风筝》是二二八题材,从受害者女儿、小女孩的视角去看悲剧的荒谬,看她的童年被摧毁,大学时认真了解过二二八的莫子仪,很荣幸可以参与;长片《该死的阿修罗》则是「愤怒」的故事:「在这疯狂的社会,你我都有可能成为阿修罗,成为下一个失去理智的人。这背後是怎样的社会结构与共业?」
另一部长片《溟溟》,说一个天文学家花了一辈子,想观测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如果它的发生是在几百年後,此刻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吗?如果我们对此刻的存在失去信念,其实你就不存在了。」
他想了想,继续说:「我这二十几年来都想鼓励大家:不被看见、被重视,不代表你不存在,而是你相信自己活着的力量,你就存在。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我,是因为我这二十几年努力照着自己的样子活着,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对这世界有所影响,可以用你的方式和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对不起我都讲太多!(笑)」

*尾声
2020 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工作从上半年被挤到年尾,此刻莫子仪最大的遗憾是:过年前没有时间大扫除。「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密集地工作,特别觉得疲累但其实这样说不太好意思,在这种时刻还有人持续找你拍戏、演出,都应该要珍惜,但又很想要休息,就会很矛盾、拉扯(笑)」
访谈最後,我问起《溟溟》共事的邓九云告诉我的小秘密:英国影帝丹尼尔.戴.路易斯是莫子仪的偶像。为什麽是他?「他总是专心投入、诠释角色,结束後就回归自己单纯的生活,做自己的手工艺。这也是我习惯跟喜欢的状态,全然投注在表演这件事,我希望自己可以跟他一样。」
莫子仪形容,当他看到自己对表演的追求,对成为角色的努力,有另一个人也同样投入实践:「好像隔着很遥远的山,看到另一个很高的山顶上有个人,而我也很努力在往那个方向前进。」他抬起手往前指,下一秒又腼腆地笑了,不过那一秒间,我已经看见影帝望向高山的眼神。
采访、撰稿:张砚拓
摄影:ioauue
全文剧照提供:CATCHPLAY+、牵猴子
场地协力:AGCT apartment

*采访後记一:
那天下午,我和莫子仪聊得入神,偶尔会想起去年六月,编辑他和杨小黎的通信时感受到的赤诚、自剖。他是个「想很多」的人,而这天的情境令他放松,不只是侃侃而谈,还可以感觉他的表达是把你放在很近很近、慎重以待的。
期间他常常犹豫,或停下几秒,不只一次说出:「不好意思我有时候自己讲一讲就会讲太多」,再露出腼腆的笑。
访谈结束後,我们跟他解释最後一个任务:在《酿电影》ig 限动,我们向读者募集对影帝提问,一天下来收到破纪录的 158 则──酿编很客气地建议:「可以回个 20 则就好了没关系~」莫子仪也客气说好。然後说他先到楼下抽根菸休息。过没两分钟,我们发现他已经开始在手机上填答了:
「小莫可以不要结婚ㄇ我会心碎」
「可是我妈妈会心碎」
「有可能出柜吗?」
「你怎麽知道没有:)」
「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向或目标」
「我通常都是靠 Google」
「小莫喜欢的类型」
「你」
?!
(影帝到底抽了什麽,可以跟我们说吗?)
P.S 以上举例是比较顽皮的部分,在总数 88 则的回覆里,多数时候他还是很「莫子仪」,温暖又诚恳又多话。非常值得一读,别忘了去《酿电影》ig 精选限动朝圣喔!

*采访後记二:
2 月 18 日起,《亲爱的房客》在 CATCHPLAY+ 独家上架,我们请莫子仪推荐给准备二刷的观众私房看点,他提了两个:
「我自己觉得──虽然这样讲很不好意思(笑)──大家可以注意年轻版的健一和後来眼神的差别。在年轻的健一眼里,你可以看到他的愤怒、恨、不信任,跟他对爱的期待和火光。後来的健一,则是会看到他眼神里的怜惜、疲惫、包容,温暖与爱。
其实我自己莫子仪跟年轻的时候,眼神也不一样了。如果大家还有力气,可以多看看健一的眼神,看能不能在当中看到不一样的情感我自己讲得很心虚(笑)」
「第二个是山。电影一开场就是山的画面,而且不是阿尔卑斯山,是合欢山,那上面的云雾、风吹过的样子,是台湾的我们熟悉的地貌。山的隐喻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包容万物,还可以有释放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山学习,去包容身边各种不同的存在,和它们共存?是不是可以把心中的思念、悔恨、遗憾,释放出来?山的意象对我来说是很美,很喜欢的。」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酿电影(原标题:「这样的分享是我享受的」──专访莫子仪再谈《亲爱的房客》)}
▌延伸阅读:更多电影/演员专访
《天桥上的魔术师》导演杨雅喆 × 演员庄凯勋
聆听海潮的人——专访导演是枝裕和
林予曦:「疗癒」就是能让你在一瞬间之内全面被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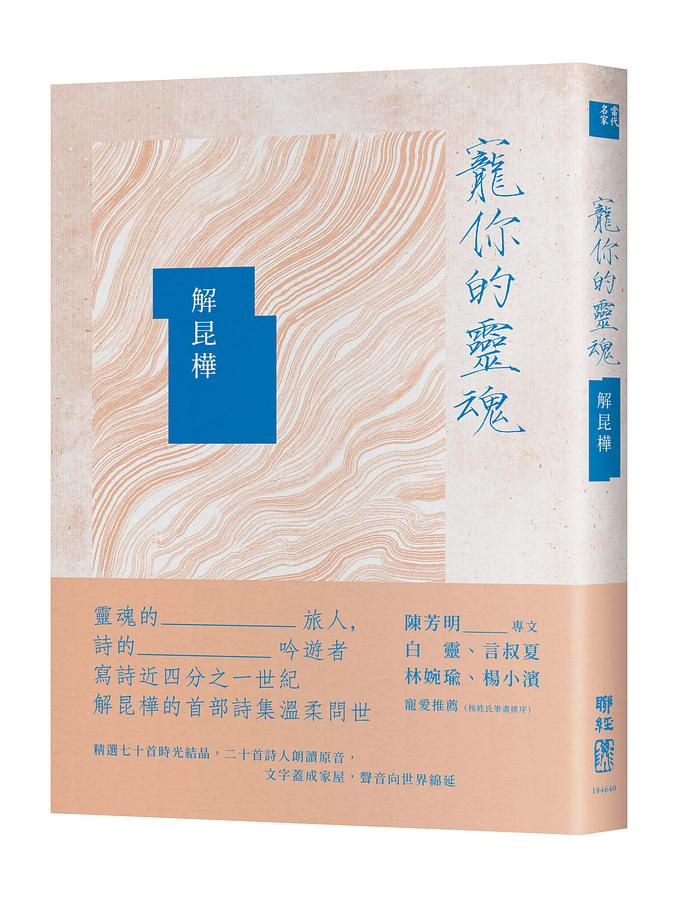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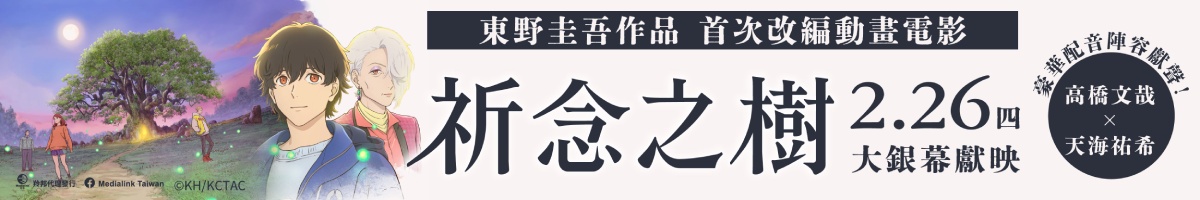



_2025042814263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