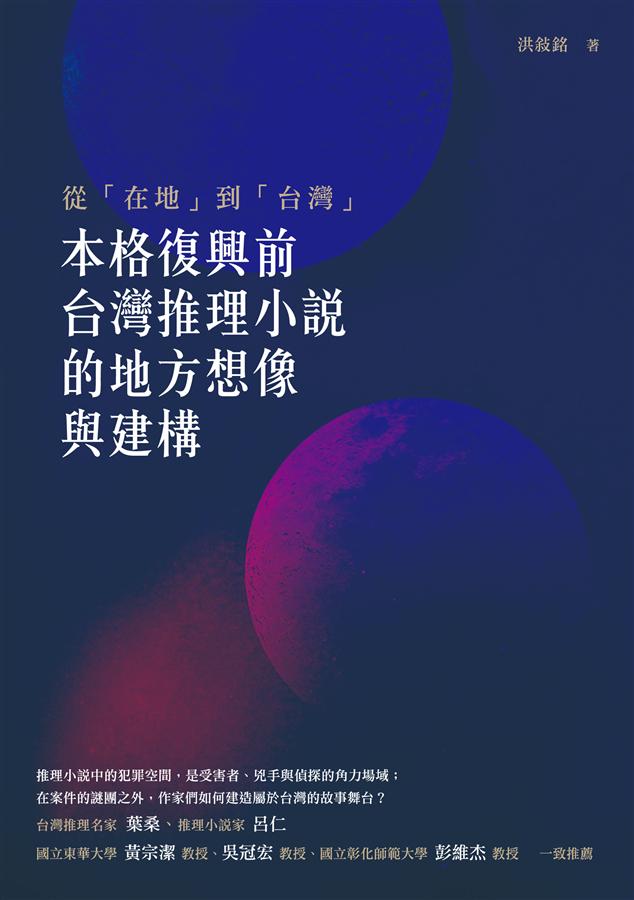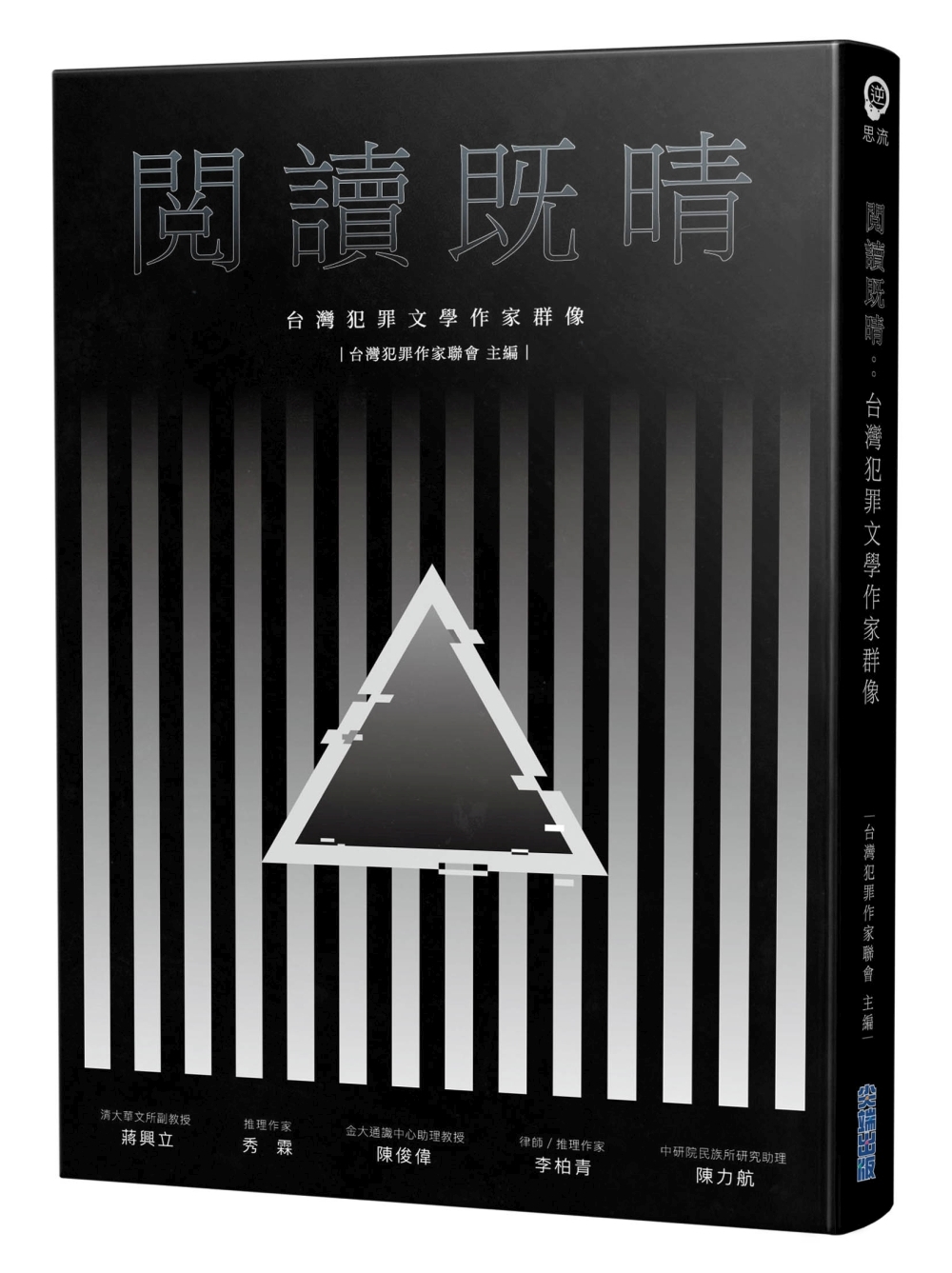用逻辑方法解决问题,小说的路径就走出来了──冬阳谈各国推理特色
撰文 李奕樵.攝影|林昶志.場地協力|Aura微光咖啡与推理文学的结缘:从《夜半惊魂》到撰写导读
冬阳与推理文学的缘分,始於童年。小学三年级,他在百货公司书店邂逅了《夜半惊魂》这本福尔摩斯故事。明明不是鬼故事,读後却做了恶梦,不甘心的他隔天主动要求再去书店,从此一头栽进侦探推理的世界,接续阅读了东方出版社的亚森.罗苹系列等作品,找到了「名侦探」、「推理」等关键词。
国中时期,他购入第一本属於自己的推理小说──艾勒里.昆恩《X的悲剧》,因其限时特价49元。这本书标志着他从图书馆阅读转向个人收藏与书写心得的起点。冬阳认为,早期接触推理,是从本来以为的恐怖故事,逐渐理解到能跟随英雄角色冒险办案,甚至抢在侦探前解谜的智性刺激。这段历程也伴随着他从注音读物进阶到成人阅读,并在脑中逐步建构起对「推理」这一类型文学的完整认知。
冬阳的创作主要体现在导读与解说。大学就读生命科学系的他,因缘际会下,被曾在联经出版社工作的前辈引荐入行。原来,时任脸谱总编辑、《X的悲剧》译者唐诺,在BBS时代便注意到冬阳在网路上发表的推理相关心得与评论,认为他对推理的认知、爱好与热情,适合担任选书编辑。
进入出版社後,唐诺将撰写导读的任务交给冬阳,「书是你选的,导读就该你写」──冬阳的导读创作,旨在「野人献曝」,以八成篇幅阐述「这些故事多麽有趣」,两成介绍背後的知识背景,也因此建构他的阅读世界观:先广泛认识作品,再培养出个人品味,进而影响选书决策。
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滥觞:从网路社群到实体聚会
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成立,源於BBS与早期网路社群的凝聚力。冬阳大学时期曾管理BBS推理版,同时也活跃於远流「谋杀专门店」网站的「推理擂台」留言板。该网站的即时聊天室功能,促成了每周五晚上的线上聚会,由不同人轮值「酒保」介绍新旧朋友,交流阅读心得。随着线上互动热络,实体聚会的期待油然而生。加上《推理杂志》「读者园地」让同好们认识诸多前辈与创作者,众人兴起了效仿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也就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前身的想法。时任「推理擂台」版主萨卡在中正大学担任助教,便向学校借用场地,召集同好,於 2001 年前後成立协会前身的俱乐部,举办了第一届大会。
各国推理特色与文化背景
冬阳认为,华文世界的推理元素并非始於现代推理小说概念。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如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已具备事件、侦探等要素。这些故事常涉及超自然或宫廷秘辛,核心价值观与正义、因果善恶、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它们作为大众文学,透过说书等形式流传,後与侠义小说结合。「这些故事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当年的创作者有『推理小说』的概念,而是他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事件发生、我要去解决。」当「解决问题」靠的不是鬼魂托梦、也并非刑求,而可以用逻辑推理侦破案件时,一种推理小说的路径就走出来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推理小说方面则深受福尔摩斯影响,晚於爱伦坡约半世纪。清末民初,福尔摩斯已被翻译引进华文世界,「福尔摩斯」的译名即源於广东译者的方言发音。日本将西方推理与自身文化结合,例如二战後出现的「社会派」,便深刻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台湾在日治时期(1895-1945),恰逢西方推理小说的黄金时期。当时报章上出现以日文撰写的「侦探实话」,记录警察办案过程,偏向非虚构写作。江户川乱步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引进,甚至出现过福尔摩斯来台办案的本土创作。
战後,尤其在解严前後,台湾社会对案件的呈现,初期更多体现在《玫瑰瞳铃眼》这类充满人情纠葛的戏剧,而非严谨的科学办案小说。直到1990年代,大量欧美日推理小说的引进,才让读者接触到更严谨且兼具娱乐性的作品。近年,台湾本土作家开始展现特色:卧斧将食安问题融入小说;张国立描写台湾警察、记者与小人物的生活。香港作家陈浩基的《13.67》则巧妙结合香港警察制度,通过不同年代的香港办案风格来侧写政治氛围,对台湾创作者亦有启发。
冬阳指出,推理小说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19世纪末福尔摩斯侦探形象的确立,到二战後犯罪小说的兴起,更侧重犯罪者心理与动机,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早期推理满足了读者对现实中悬案未解的心理补偿,渴望在故事中看到正义伸张、凶手伏法。现代推理则更深入探讨犯罪动机与社会成因,如宫部美幸的《模仿犯》。
科技发展对推理创作带来挑战与机遇。约25年前CSI犯罪现场影集的出现,普及了DNA等监识技术,一度让传统推理中依靠侦探智慧查案的模式面临困境。然而,创作者会逐渐将新科技融入叙事,例如利用交通工具的时刻表诡计,尤以日本铁路发达为背景者着称。CSI的影响甚至延伸至现实,陪审团成员可能反问检方为何无DNA证据。
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推理创作。克莉丝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巧妙织入一战後欧陆的混乱氛围;美国冷硬派的诞生与二战後退伍军人难以融入社会、转而从事私家侦探等行业有关,他们处理的城市犯罪如同另一种战场;北欧推理则揭示了福利国家光鲜外表下的阴暗面,探讨跨国犯罪、性暴力等议题。日本本格派对诡计的沉迷,某种程度上也与其相对较低的犯罪率和高破案率有关,现实社会问题较少成为本格派直接的书写核心。
相较之下,台湾因监视器普及,连续杀人魔等题材较难令人信服。冬阳形容推理小说如「寄居蟹」,不断吸纳新元素,扩大其外延,甚至可以融入科幻,如英国影集《黑镜》的某些集数。
台湾推理文学的未来展望:多元与沃土
对於台湾推理文学的未来,冬阳抱持「既期待,也不抱特定期待」的态度。他认为台湾有「弯道超车」的潜力,创作者无需完全依循推理史脉络,不同世代的作家会基於各自的时代经验、对推理的理解创作。例如,薛西斯的作品可能受到《告白》、《恶之教典》等日本影视风格强烈的作品影响。台湾年轻一代创作者已逐渐打破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壁垒,这是台湾的优势。他期待看到更多不同领域的人投入推理创作。
要滋养台湾推理的发展,冬阳认为关键在於提供「发表园地」与「肯定标的」。例如推理杂志、推理作家协会举办多年的徵文奖、各类写作课程等,都是重要的土壤。这些平台让创作者的作品能被看见、被讨论,并获得回馈与修正的机会。此外,作品的市场能见度、改编潜力、海外版权等,也是外部的驱动力。
他乐见台湾推理创作的跨界合作与跨代传承,使其不仅仅是类型小说,更能成为台湾文学创作中充满活力的一环。相较於科幻、武侠等其他类型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推理文学仍保有令人期待的能量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