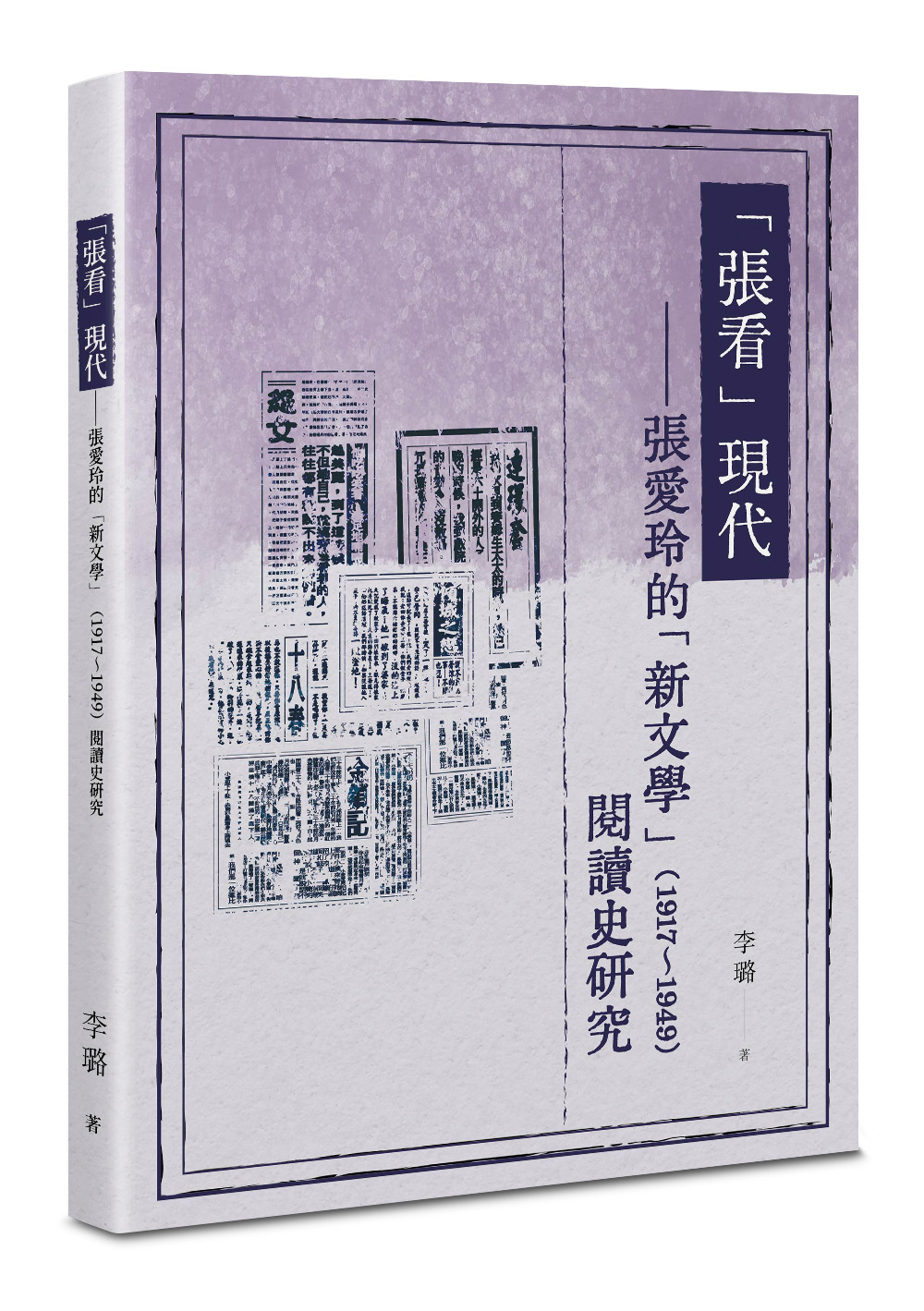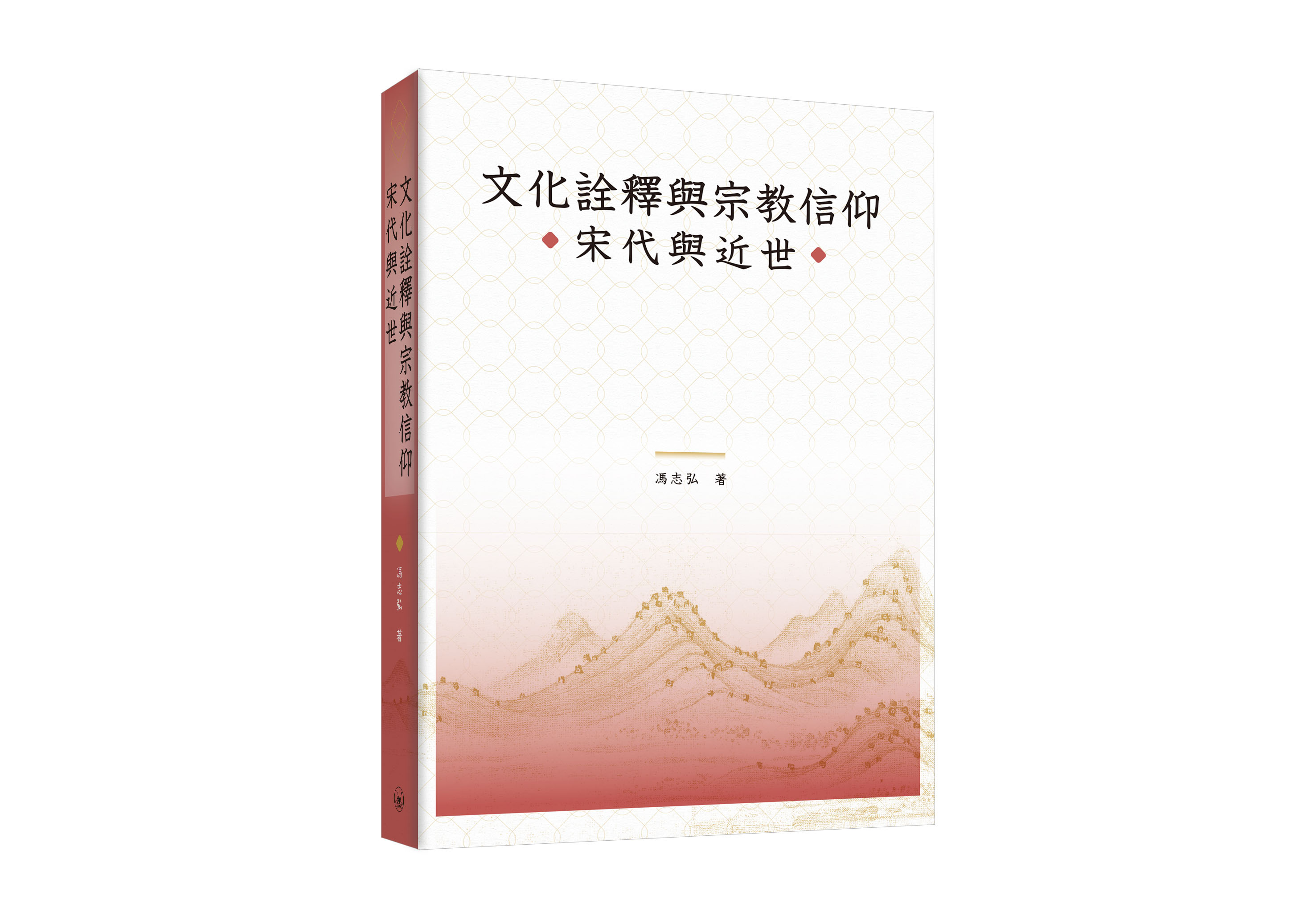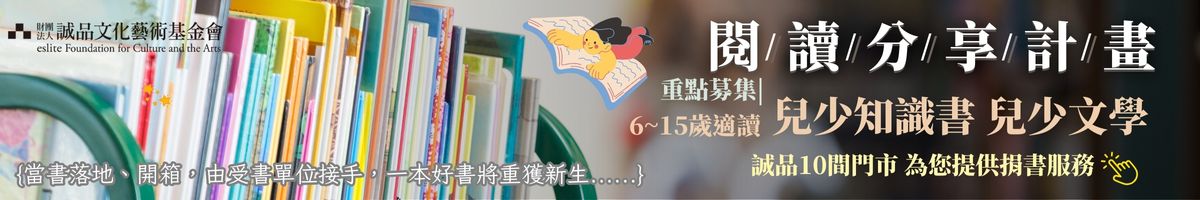想像力是飄蕩在萬事萬物間的神祕物質|專訪《夜晚的潛水艇》作者陳春成
撰文 朱嘉漢(作家)王德威老師說:「他的文字清晰典雅,在年輕世代作家中並不多見。他的故事天馬行空,字裡行間在在顯示鍛鍊的痕跡。世界文學和傳統典故巧妙糅合,『舊山河和新宇宙』奇特接軌。」
作家余華說:「他的寫作既飄逸又扎實,想像力豐富,現實部分的描寫又很扎實,敘述中的轉換和銜接做得非常好。是一個前程無量的作家。」
他是陳春成,1990年生,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人。《夜晚的潛水艇》是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獲《亞洲週刊》2020年度十大小說、豆瓣讀書2020年度中國文學(小說類)Top 1、第六屆中國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作品、首屆PAGEONE文學賞。
九篇故事,筆鋒游走於舊山河與未知宇宙間,彷彿開啟了一個新視野。
在這篇訪談中,小說家朱嘉漢和陳春成有一場精采的對談。從「如何開始走上了文學,被什麼打動,又怎麼開始寫?」、「是否覺得可以寫得更好?」等文學寫作經驗,到「想像力是什麼?」、「波赫士小說跟陳春成的小說有什麼關係?」等問題,試圖去探究想像力的邊界。

{本內容由撰文者及麥田出版提供,僅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誠品立場;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Q=朱嘉漢|A=陳春成
Q:春成好,在提出第一個問題之前,容我先說明一下閱畢後的感受。我感到「似曾相識」。我有一種早就認識你的感覺。不過,我暫且先不濫情,先來聊聊小說本身。諸多的篇章,或者說是每一篇,我都感到似曾相識,除了令我聯想起波赫士外,也想起卡爾維諾、艾可,甚至培瑞克(Georges Perec)。我猜想,你應該是一位已經相當有自覺的作者了。意思是,不論自己感覺寫得如何,他人評價如何,你很清楚自己在寫什麼。因此我可以想像,你或許也不需要為作品辯護或解釋了。
我感覺你的作品要寫出的,就是這種似曾相識,「déjà vu」的感覺。像是你小說裡面陳透納的畫,葉書華未能呈現出的文章。也許這些小說已經寫出來過,被閱讀過。以夢的形式、潛意識的形式,在生活中以雲彩、樹木的形狀、鳥鳴聲等方式展現過了。
作為第一個問題也許有點奇怪,這種「似曾相識」感,是你寫作時想追求的,並給予讀者的嗎?在明顯的隱藏、逃逸、消散主調外,整體而言,我認為這是你小說想要捕捉到的感覺,並且是相當積極的。
A:謝謝朱老師。你所說的意思,或許類似古人所說「疑此江頭有佳句,為君尋取卻茫茫。」——文章在凝聚為文章之前,預先以其他形式存在。我欣賞這想法的趣味,因為它把人類編織符號的技藝提升到了與自然事物一樣確鑿而神祕的地位。不過說實話,寫作時我沒有預設過這個,包括隱藏、逃逸的主調,醞釀階段我只是專注於某種氛圍。
Q:除了〈夜晚的潛水艇〉之外,許多的時候,我仍然想到波赫士。譬如讀〈《紅樓夢》彌撒〉時想到了波赫士的〈永生〉、〈巴別塔圖書館〉,甚至〈鳳凰教會〉。跟你分享一個趣事,當我讀著讀著,心裡正想著「不過這集子似乎沒有像波赫士的鏡像概念」,結果就恰好讀到〈尺波〉,馬上讓我想到了〈環形廢墟〉。
同樣喜歡波赫士的我想問,你最喜歡波赫士哪些作品?哪個部分吸引你?若是可以,我想問你,波赫士與你的小說的關係是什麼?
A:我喜歡波赫士的幾乎所有作品,喜歡他的玄思、書齋氣質和對無限的迷戀,因此同名的那篇小說,讓他開頭的甲板上登場了一下。他的故事多數都在講一次精神遭遇,沒有多少外部的情節,是一種明顯「內傾」的小說。我認為古文中的一個詞很能形容他的風格:冥搜。向內部,向幽暗中盡情發掘。我承認我受了他很大影響。現代作者似乎輕視繼承而強調原創性,古人則反之,謙卑到願為更古的人做僕役,傳得一點神髓就歡喜踴躍。但波赫士的玄思趣味供給寫作的養分沒有持續性,也許是他寫得很少的一個原因。或許以後我不得不偏離他的版圖。另一個源頭是汪曾祺,在語言方面的啟蒙和示範。沒有這兩位,我或許根本不會寫小說。如果說他們是矗立在往昔的瑰偉宮殿,我的寫作只是拾起一小片殘瓦,研磨成我的硯台。不過也不好說,到現在小說創作不過兩三年,新鮮感尚存,還想多試試各種路子。第一本小說集如一張專輯一樣,反映一個時期的創作風格,今後如何發展,非我所能預料,因此不去設限。

Q:《夜晚的潛水艇》喚起我的很大一部分的情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好像這些小說,反反覆覆所涉及的,好像就是文學本身,或說文學之愛本身。再更確切來說,文學之愛,是愛的追求。我感覺你心中有個相當「純粹」的念頭,展現在〈夜晚的潛水艇〉、〈傳彩筆〉、〈釀酒師〉等篇章了。這種絕對感,讓我想到韓波的〈告別〉:「我應該埋葬我的想像與回憶!」尤其是〈夜晚的潛水艇〉,你用了一個相當令我驚喜的方式,只用想像來告別自己的想像力,我讀到的時候,忍不住拍了自己的大腿一下,我立刻肯定這不是單純的模仿波赫士的形式的作品了,因為你直接掌握到想像力的邊界,你「看過那邊的風景了」(即使也許代價是遺忘,是無法言說)。
然而我想問的問題相當簡單,看了小說寫了這些角色的初衷、追尋與惆悵,我想聽你說一說你文學的初衷。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走上了文學,受什麼打動,又怎麼開始寫的呢?
A:其實這篇看似荒誕而自傳性最強,我確實一度為想像力困擾,無法專注與學業,青春期一直在勉力克服。我初中時的志向是寫舊體詩,從未想過寫小說,一直默默在課堂筆記的背面寫古詩,虛構一片山水,吟遊其間,有時一連數日沉浸於一行詩句中。我迷戀那種一字不可動搖的圓融之美,我的野心是留下二十或二十八個字(五絕或七絕)傳世就足夠。但似乎力有不逮。寫散文是二十多歲的事,那時我信奉汪曾祺的語感、文氣、節奏意識,開始喜歡散文的舒展之美。寫小說是前幾年開始,某日忽然有了一個故事,覺得非寫不可,於是就開始寫了,直到如今。不過我還是認為短篇小說是次於詩的體裁。
Q:對你而言,想像力是什麼?是現實的反面,抑或現實更深裡面的真實?在讀〈竹峰寺〉時,我感動當中某種「確認」感。這「確認」感是一但產生了,無論記得與否,重新拾獲與否都不在意的,無形的卻是更確然存在的事物。
A:我傾向於認為它是飄蕩在萬事萬物間的神祕物質,出入其中,無往不在。但對現實生活也構成一點干擾。我似乎有一點強迫症,不喜混亂和歡變,更因此確認感對我很重要。
Q:另外,這問題也許有點直接,但我想知道,這些作品當中,我個人首愛是我上題說到的〈竹峰寺〉(另外是〈夜晚的潛水艇〉、〈釀酒師〉)。不過對你來說,這些作品寫完,是否有感覺到力有未逮的部分?覺得應該可以寫得更好的地方?
A:就我個人目前的閱讀趣味而言,我覺得已經很滿足了,找不到可以改的地方。我一度擔心出版後某日發現某處還想修改,可已白紙黑字流諸四方,就很焦灼。慶幸現在還沒發生。人常說寫作的初心僅在取悅自己,可取悅自己是多麼難的事,眼下讓你心滿意足的作品,也許三五年後再看時覺得尷尬。也許這並不意謂著你寫作上進步了,僅僅是閱讀口味改變了。因此應該享受眼下的心滿意足。
Q:我讀完〈音樂家〉時有點詫異,也去搜尋些你的相關訪談。我覺得除了翻譯語言的仿效、除了諜報的形式外,你試圖在這篇小說裡做點不一樣的嘗試的,這樣說對嗎?這本小說集裡面,有哪些作品是對於你而言挑戰比較大的作品?
A:應該是〈音樂家〉和〈竹峰寺〉。前者是蘇聯故事,沒法用慣常的語言來寫,我想模仿汝龍翻譯契訶夫的語言風格(我覺得是極好的譯本),因此動筆之前埋頭讀了一個時期,且收集了一個文件夾的資料。還有一個就是長度,我從未試過信馬由韁地寫作,而是習慣將短篇故事想到七八分熟,再一氣寫出,超過兩萬字腦筋就跟不上了,比較艱難。挑戰方面,應該還是〈音樂家〉,是外在的挑戰,寫作時不相信這故事能發表或出版,完全抱著寫出來給自己和幾個朋友看看就好的心態來寫。這就不細說了。
Q:有人說翻譯猶如作品的輪迴轉世。以繁體在台灣出版雖然跟翻譯仍然有差別,但你心中是否會期待這本書有另一次不同的命運?或是換一個比較普通的角度來問,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台灣的讀者說的,你會怎麼對台灣讀者介紹你的作品與想法?
A:就我個人的閱讀經驗,我覺得台灣作家的語言習慣和大陸已有微妙甚至明顯區別,像口袋妖怪伊布分別進化成火伊布和雷伊布一樣,相互比對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一向讚同汪曾祺的觀念,寫小說就是寫語言,不可分割,不存在「內容很好就是語言差了一點」的說法。一點點微小的用詞習慣差異,可能滋生出全然不同的閱讀體驗。因此我對能得到台灣讀者的喜愛毫無信心,順其自然而已。我覺得作者能對讀者所說的最得體的話就是:希望不令你們失望。
✦
▌採訪者簡介|朱嘉漢
1983年生。曾就讀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班。現為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寫小說與Essays。著有《在最好的情況下》、《禮物》、《裡面的裡面》,文哲學導讀書《夜讀巴塔耶》等。

▌延伸閱讀
☞《想像的動物》|附全球獨家精印藏書票


☞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