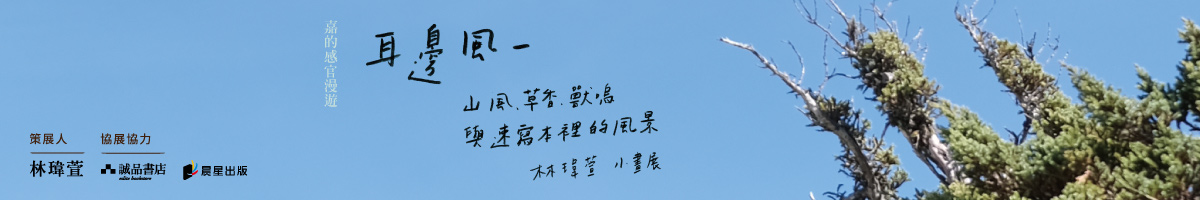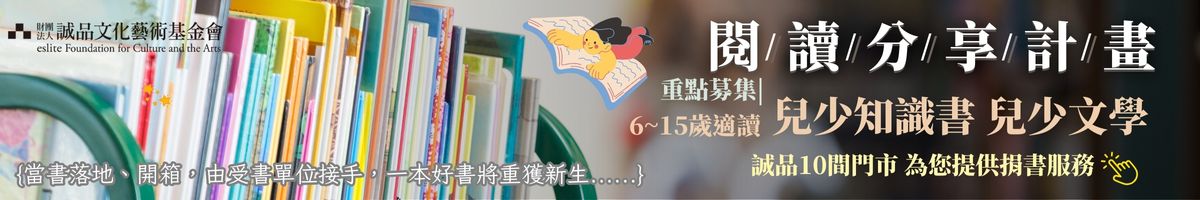夜的大赦——專訪曹馭博
撰文 張立雯.攝影|楊雅淳.採訪場地|本然生活nisarga cafe但詩人的世界一直都不是那樣簡單。在二〇一八年出版首部詩集《我害怕屋瓦》的曹馭博,對自己的第二本詩集《夜的大赦》有更大的野心:「我們有些朋友覺得,寫(這些很少人讀的)詩是一場壯旅……除了希望達到某種美學的高度,我更想同時也下探到一些階級。我發現我喜歡的作家也有這樣的傾向,比方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或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後來發現,作家的廣度,比我想得還要寬廣;跟在學校裡學到的不一樣。」

自稱是比較直覺性的寫作者,曹馭博習慣蒐羅日常所見事物、以即景的方式記錄下眼睛見到的或耳朵聽到的,因此他提到兩本詩集相似的部分是,裡面都有相當多的社會事件——但在《夜的大赦》裡,他藏了更多思考在裡面,而且藏得更深。
「如果說《我害怕屋瓦》是單面鏡,《夜的大赦》就是雙股螺旋。」曹馭博一層一層、有條理地剖析自己的寫作。他以都柏林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所舉辦的翻譯競賽為例:眾人在討論〈夜的大赦〉這首詩,「大赦」的翻譯應做宗教性字義或政治性字義解,自己當時並沒有給出一個肯定的答覆。他希望讀者有自己的思考,而非服膺作者給出的解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大聲朗誦詩歌的年代了。你大聲,總有人會比你更大聲。我希望自己的詩能讓人思考、潛移默化,像一場暗中進行的革命。」
光與暗的意象襲擊
「第一本詩集我想寫屋瓦,是因為它象徵了壓迫。但這壓迫也不是當權者這麼簡單,有時候壓迫可能來自血親,或是平常之物……第二本我想寫『光』。《我害怕屋瓦》出版後隔年,二○一九世界開始動盪——你可以看到,科技跟政治纏繞在一起、變成另一個雙股螺旋;關於光明與黑暗的隱喻,至此又被翻轉了一次……『光』是否具有欺騙性?
『黑暗』在這個前提下,是否提供了我們遨遊的可能?我開始思考在這個時代,黑暗會不會才是我們的庇護所?我是寧可相信這個時代的黑暗,不信任這個時代的光明。」
曹馭博解釋道,光,過去常包含了「啟蒙」這個概念,是由內而外地、照亮自身也照亮了外界,是獲取了知識;但在這個時代,一如班雅明所言:所有被壓迫者都是碎片。(我們)碎片反映出各種光亮,但它不是來自內部,而是反映壓迫者追索的強力探照燈,甚或是科技……「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曾說,二十世紀的詩歌是追尋的詩歌,它過度了戰爭與廢墟,重構對未來的想法;我個人認為二十一世紀的詩歌,則是一種歷史的、或說文化的退步觀,我們真實地成了『失敗者的碎片』——我們盯著手機看影片、看短影音,這裡面沒有在收集知識、沒有獲得啟蒙,只是在反射,在破壞我們的虹膜罷了。」
他喜歡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這樣的形容:從神經科學的角度,黑暗是看得見的,因為光的缺席,眼睛細胞分泌了某種叫「黑暗」的酵素。也許同一時代的詩人、不合時宜的詩人,他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看見黑暗」。曹馭博相信,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的詩人都在構築這件事,雖然他們並沒有大張旗鼓地論述,直到二十世紀末期,眾人才開始討論它。

在第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裡,曹馭博提到集子裡一部分是在淡水讀大學的習作,一部分是研究所在花蓮所寫成,反映也奠定他即景式、速寫式的寫法與收斂的主題和風格;第二本詩集《夜的大赦》除了全數在淡水完成,他也變換了寫法:加進小敘事,並強調速寫的意象到了極致後還必須升級、有更多思考參與其中,也給出他對世界的看法。因為他了解,世界並不是單一的靜止鏡頭這麼簡單,而是連續動態,所以在第二部詩集,他想用長鏡頭,或某個碎片的鏡頭,完備他對主題的速寫。
其中在「當幼鹿尋覓語言」一輯中,曹馭博笑稱這是每個詩人/作家出現在他夢中的記錄——而且都是他喜歡的作家。當幼鹿尋覓語言一詞來自辛波絲卡,而他想在此論創作:為他深愛的作家們寫文學小傳,對他們創作的思考與從中獲得的與反饋的,以及作品中的他們。「我最常夢見楊牧,但夢裡他什麼都沒跟我說,只是一直背對著我在書架上找書。」
曹馭博近期閱讀書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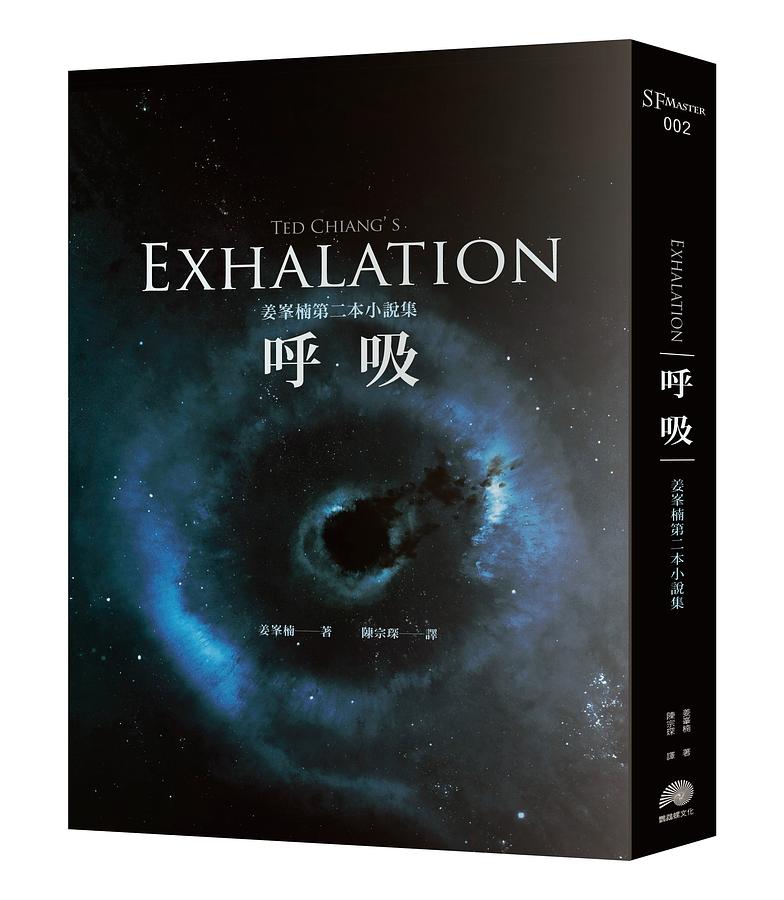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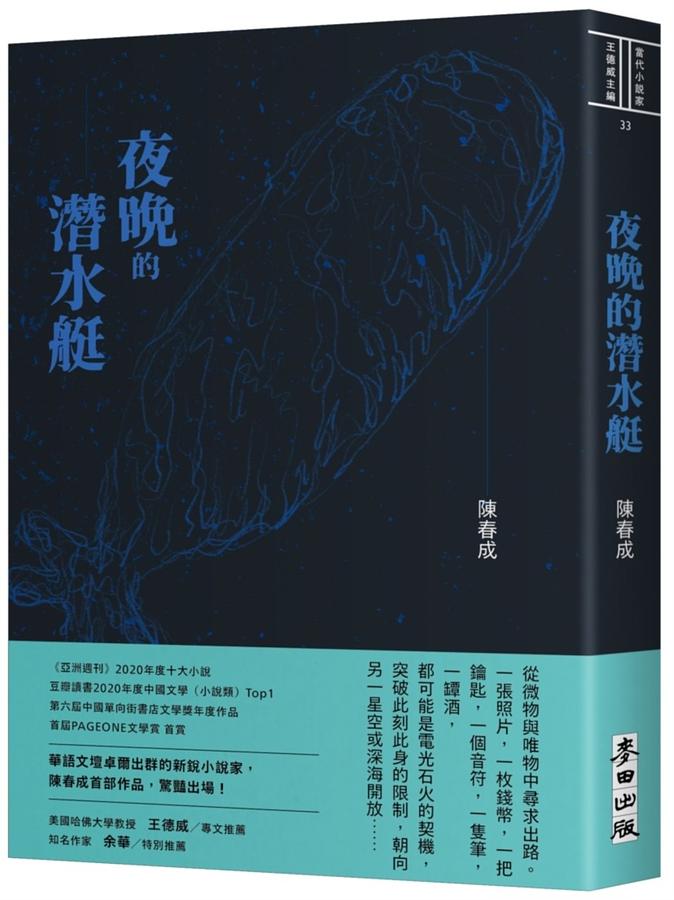
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
安妮.卡森(Anne Carson)
奈莉.沙克絲(Nelly Sachs)
小說:《拾貝人》安東尼.杜爾(Anthony Doerr)
《呼吸》姜峯楠
《夜晚的潛水艇》陳春成
關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閱讀與風格採買的書店誌,每個月1日準時於全台誠品書店免費發刊。每期封面故事討論一個讀者關心的生活與消費的議題,並於全台書店展示議題的「延伸主題書展」,推薦給讀者從中外文書籍、雜誌、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除紙本刊物,另有線上版與《誠品書店 eslite bookstore》粉絲專頁,隨時更新封面故事背後的最新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