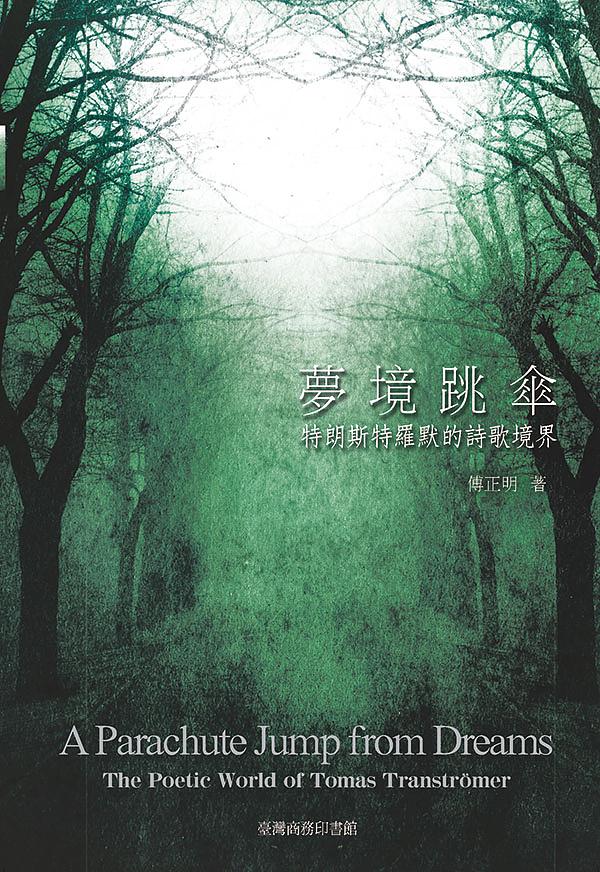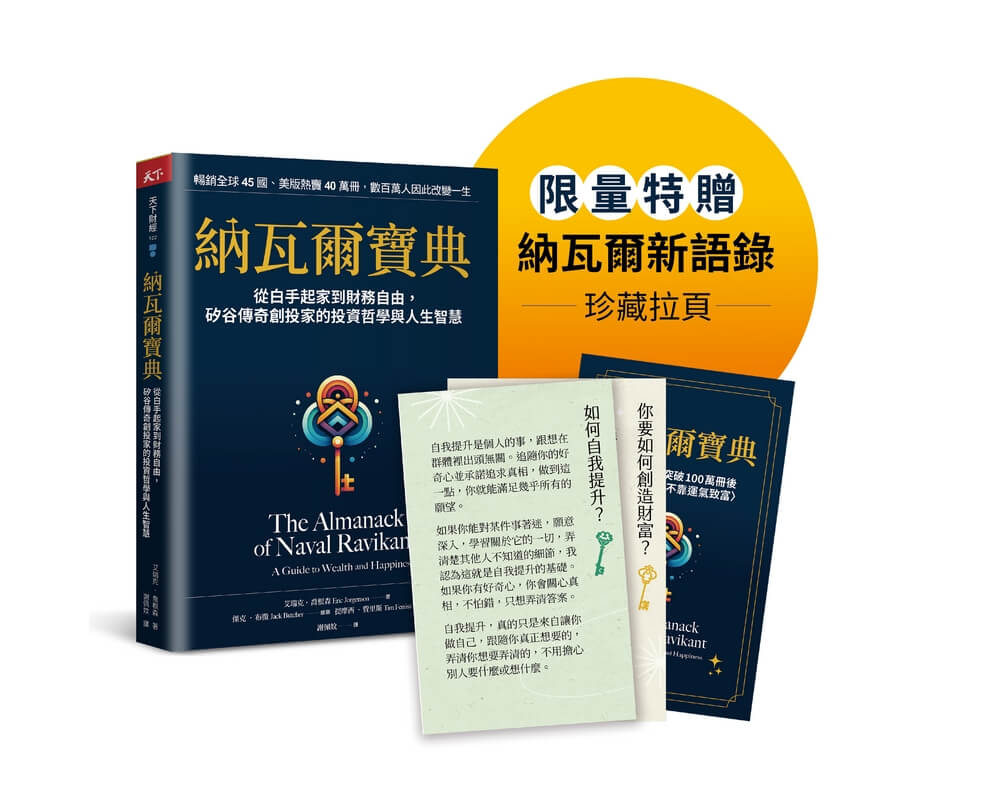夜的大赦——专访曹驭博
撰文 張立雯.攝影|楊雅淳.採訪場地|本然生活nisarga cafe但诗人的世界一直都不是那样简单。在二〇一八年出版首部诗集《我害怕屋瓦》的曹驭博,对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夜的大赦》有更大的野心:「我们有些朋友觉得,写(这些很少人读的)诗是一场壮旅……除了希望达到某种美学的高度,我更想同时也下探到一些阶级。我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也有这样的倾向,比方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mer),或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後来发现,作家的广度,比我想得还要宽广;跟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

自称是比较直觉性的写作者,曹驭博习惯蒐罗日常所见事物、以即景的方式记录下眼睛见到的或耳朵听到的,因此他提到两本诗集相似的部分是,里面都有相当多的社会事件——但在《夜的大赦》里,他藏了更多思考在里面,而且藏得更深。
「如果说《我害怕屋瓦》是单面镜,《夜的大赦》就是双股螺旋。」曹驭博一层一层、有条理地剖析自己的写作。他以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所举办的翻译竞赛为例:众人在讨论〈夜的大赦〉这首诗,「大赦」的翻译应做宗教性字义或政治性字义解,自己当时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覆。他希望读者有自己的思考,而非服膺作者给出的解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大声朗诵诗歌的年代了。你大声,总有人会比你更大声。我希望自己的诗能让人思考、潜移默化,像一场暗中进行的革命。」
光与暗的意象袭击
「第一本诗集我想写屋瓦,是因为它象徵了压迫。但这压迫也不是当权者这麽简单,有时候压迫可能来自血亲,或是平常之物……第二本我想写『光』。《我害怕屋瓦》出版後隔年,二○一九世界开始动荡——你可以看到,科技跟政治缠绕在一起、变成另一个双股螺旋;关於光明与黑暗的隐喻,至此又被翻转了一次……『光』是否具有欺骗性?
『黑暗』在这个前提下,是否提供了我们遨游的可能?我开始思考在这个时代,黑暗会不会才是我们的庇护所?我是宁可相信这个时代的黑暗,不信任这个时代的光明。」
曹驭博解释道,光,过去常包含了「启蒙」这个概念,是由内而外地、照亮自身也照亮了外界,是获取了知识;但在这个时代,一如班雅明所言:所有被压迫者都是碎片。(我们)碎片反映出各种光亮,但它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反映压迫者追索的强力探照灯,甚或是科技……「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曾说,二十世纪的诗歌是追寻的诗歌,它过度了战争与废墟,重构对未来的想法;我个人认为二十一世纪的诗歌,则是一种历史的、或说文化的退步观,我们真实地成了『失败者的碎片』——我们盯着手机看影片、看短影音,这里面没有在收集知识、没有获得启蒙,只是在反射,在破坏我们的虹膜罢了。」
他喜欢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这样的形容:从神经科学的角度,黑暗是看得见的,因为光的缺席,眼睛细胞分泌了某种叫「黑暗」的酵素。也许同一时代的诗人、不合时宜的诗人,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看见黑暗」。曹驭博相信,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诗人都在构筑这件事,虽然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论述,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众人才开始讨论它。

在第一本诗集《我害怕屋瓦》里,曹驭博提到集子里一部分是在淡水读大学的习作,一部分是研究所在花莲所写成,反映也奠定他即景式、速写式的写法与收敛的主题和风格;第二本诗集《夜的大赦》除了全数在淡水完成,他也变换了写法:加进小叙事,并强调速写的意象到了极致後还必须升级、有更多思考参与其中,也给出他对世界的看法。因为他了解,世界并不是单一的静止镜头这麽简单,而是连续动态,所以在第二部诗集,他想用长镜头,或某个碎片的镜头,完备他对主题的速写。
其中在「当幼鹿寻觅语言」一辑中,曹驭博笑称这是每个诗人/作家出现在他梦中的记录——而且都是他喜欢的作家。当幼鹿寻觅语言一词来自辛波丝卡,而他想在此论创作:为他深爱的作家们写文学小传,对他们创作的思考与从中获得的与反馈的,以及作品中的他们。「我最常梦见杨牧,但梦里他什麽都没跟我说,只是一直背对着我在书架上找书。」
曹驭博近期阅读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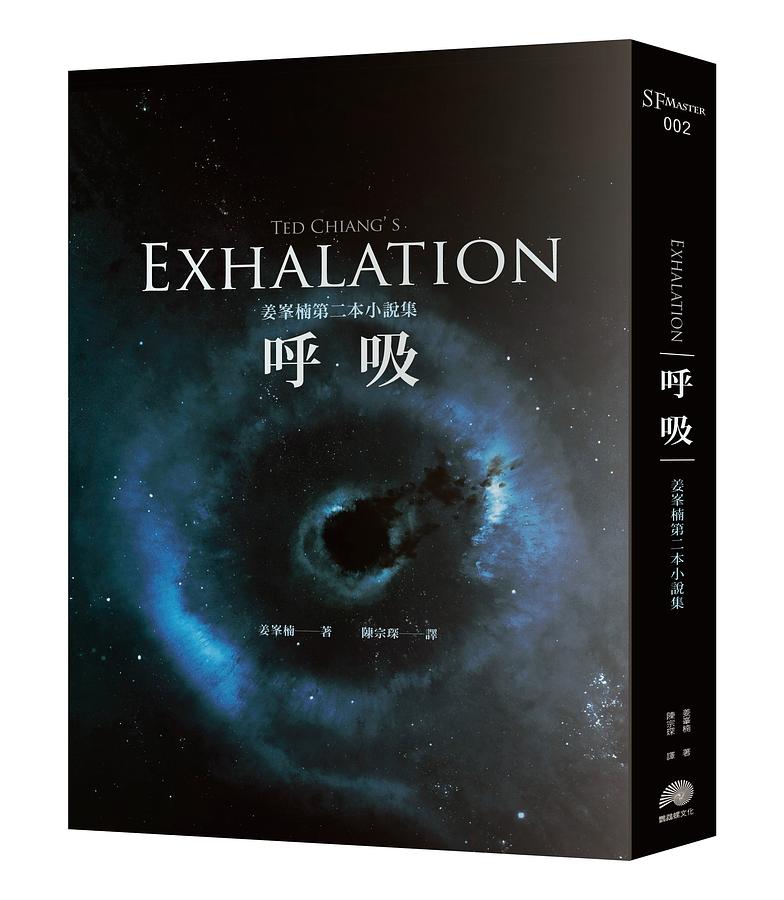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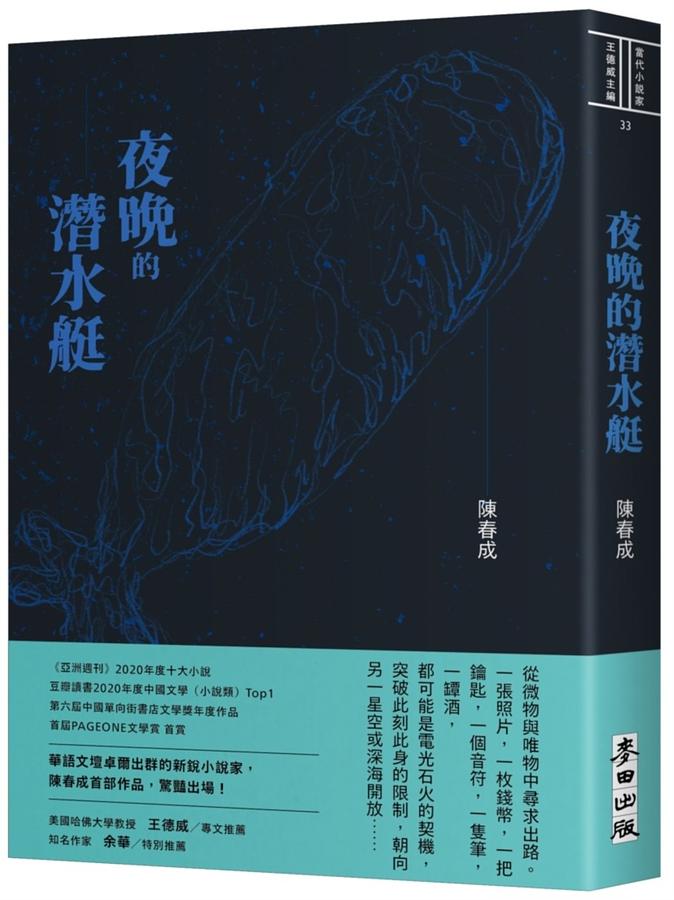
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
安妮.卡森(Anne Carson)
奈莉.沙克丝(Nelly Sachs)
小说:《拾贝人》安东尼.杜尔(Anthony Doerr)
《呼吸》姜峯楠
《夜晚的潜水艇》陈春成
关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阅读与风格采买的书店志,每个月1日准时於全台诚品书店免费发刊。每期封面故事讨论一个读者关心的生活与消费的议题,并於全台书店展示议题的「延伸主题书展」,推荐给读者从中外文书籍、杂志、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除纸本刊物,另有线上版与《诚品书店 eslite bookstore》粉丝专页,随时更新封面故事背後的最新动态!
《诚品书店eslite bookstore》粉丝专页
Apple Books《提案》线上读
US帐号
JP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