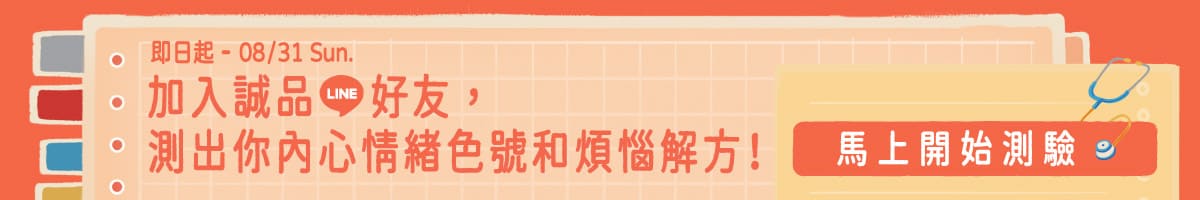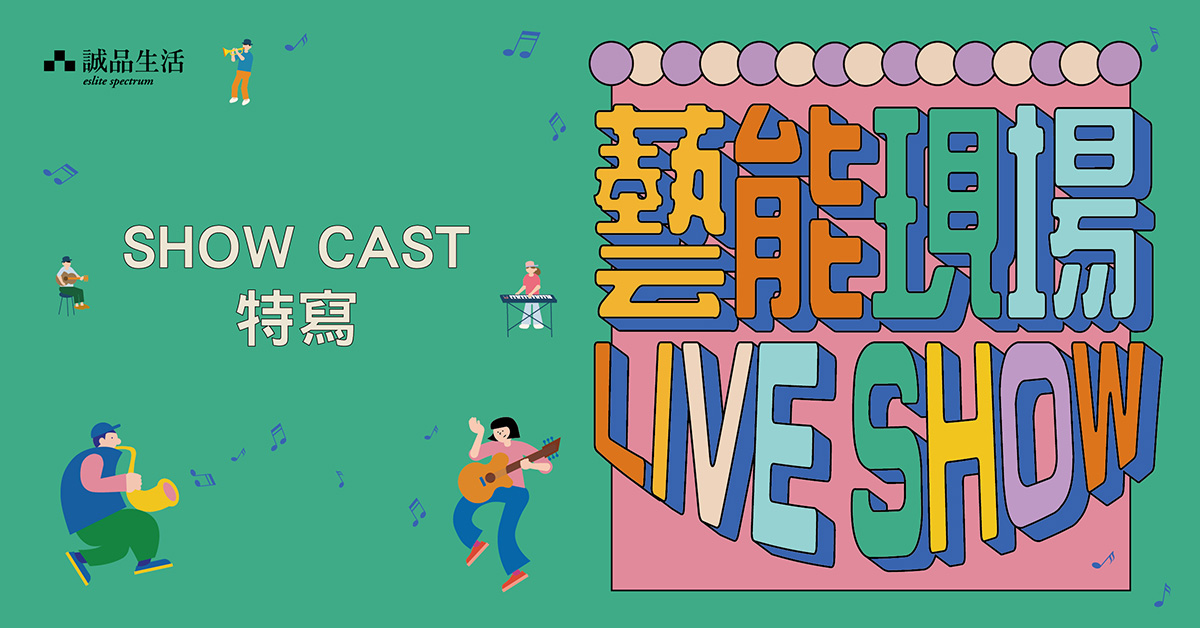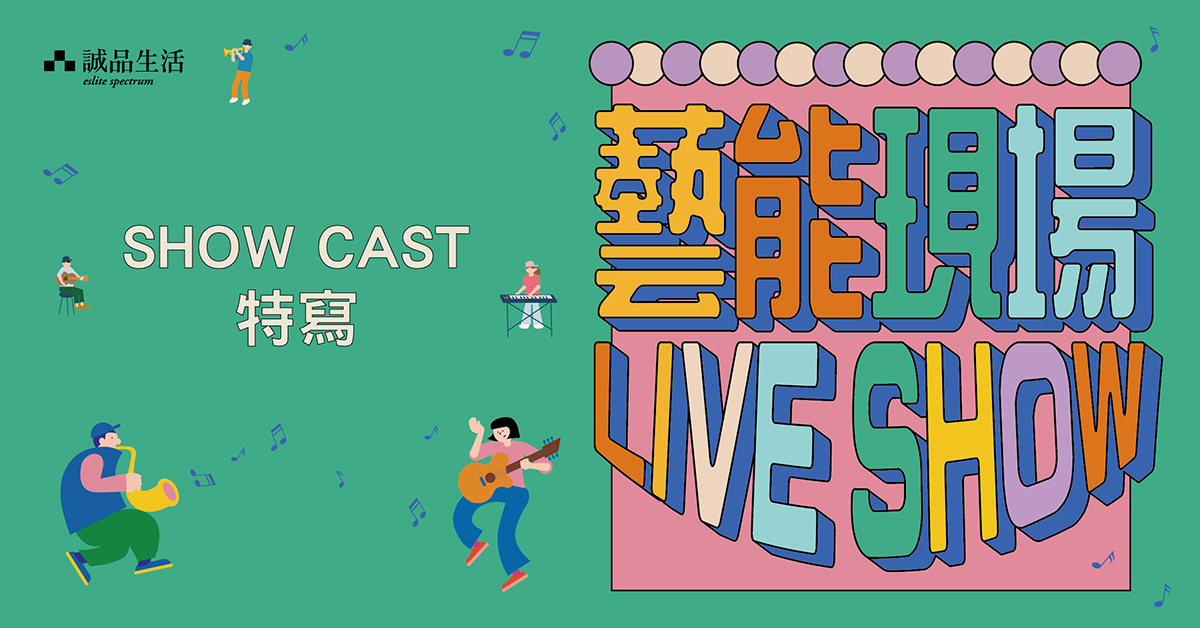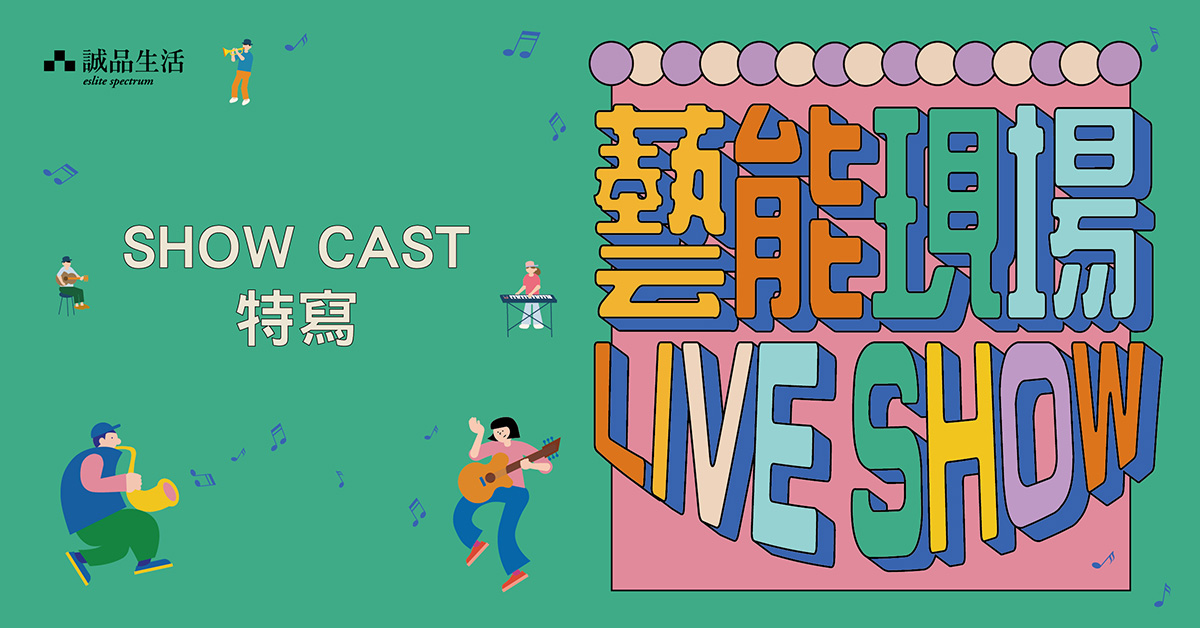致無名者的一封情書(下)——胡晴舫╳聶永真 從書封設計共談無名性
撰文 莊勝涵睽違多時,胡晴舫再出新作。本期【提案】邀請她由《無名者》聊起,再與聶永真共談此次系列書封設計合作。如同一封致無名者的情書,作家以文學起筆,設計師用圖像彌封,為不安年代留下經典。
胡晴舫的新書《無名者》與《濫情者》等七部舊作改版,封面皆由設計師聶永真操刀設計,兩人的合作帶來一場圖像與文字間的對話。我們將看聶永真如何以圖像詮釋胡晴舫,胡晴舫又如何通過聶永真之眼反照自我,攜手演繹當代經典性。
從《旅人》與《濫情者》開始,胡晴舫即以文字刻畫城市與人際的當代浮世繪。聶永真則擅長以視覺符號編織感性體驗,精準道出小時代的輕盈與敏感。對於這次新書與舊作改版的封面設計合作,胡晴舫提醒:「絕對不可小看永真封面設計帶來的意義。」

以設計打造精緻、可口的當代讀本
聶永真一直是胡晴舫的讀者,當問及如何理解從《旅人》到《無名者》的核心關懷 ,他不假思索便說:「胡晴舫一直在解構許多事情。」這次他選擇野獸派畫家馬諦斯的畫作,作為演繹視覺符碼的參照對象。「我們希望圖像的整理風格介於抽象與具象間,但降低馬諦斯鮮豔的色彩,讓它呈現出柔和與曖昧的感覺。」
「我對新的讀者有期待」,聶永真希望系列封面具有「當代感」,在視覺調性上能與胡晴舫舊作產生區別,因為「如果書封能具有當下時空環境的氣味與要素,就能營造讓年輕的讀者把書拿起來讀的氣氛。但是這不代表要放很多年輕人的符號,故意裝作年輕是一種很拙劣的表現方法。」此外, 他採用13.5cm╳19cm這個略小的開本,目的也在做出精緻、可口且富有當代性的讀本。
從個別書封的呈現來看,以《人間喜劇》為例,「我們給它一張空的臉,但因為這張臉帶有抽象的風格,所以又像各種東西拼接成的組織結構體。」,聶永真抓出globalization(全球化)、disruption(瓦解)、reorganization(重組)等關鍵詞,指出在全球化情境中事物的連結、分裂與重整,所以這張「臉」象徵了人們失去固定不變的本質。事實上,這也符合胡晴舫筆下的「無名性」,正如她說:「我們以為自己是孤島,但絕對不是,因為人類社會的命運是集體相連的,這確實是無名者的一個重點。」
然而《無名者》對於「無名性」的討論無疑更為完整,聶永真從最打動他的〈無名的人〉找到設計靈感。本篇提到胡晴舫不斷追問一位活過二戰、柏林圍牆倒塌,來到當代社會的老婦人,此刻生命是何種風景,她終於回答:「親愛的,你只需知道我活下來了。」聶永真認為這裡道出的是「一種人生不可避免的路途」,於是他在封面用四個背影排列出一條路徑,失去面目的芸芸眾生終將以生命的千姿百態消失在命定的盡頭。
01 02
02 03
03
04 05
05 06
06
07 08
08
▲ 01-08 分別為新書《無名者》、改版舊作《濫情者》、《機械時代》、《旅人》、《我這一代人》、《她》、《人間喜劇》及《城市的憂鬱》。八本系列書封皆由聶永真操刀設計,整體以馬諦斯的畫作為靈感,並選擇使用略小的開本製作。
聶永真:她把自己看成眾生中,極其渺小的一個人
時光匆匆, 二○○一年聶永真與胡晴舫分別以《社會咪咪檔案》(《永真急制》前身)和《旅人》出道,迎來一個黃金時代的開端。如今,兩人也已走入中生代之列,讀者在《無名者》中能輕易讀出胡晴舫步入中年後的微妙轉變,例如語氣上明顯刻劃出的歲月景深。聶永真說:「晴舫早期的文字像一把冰冷的劍,文字比較直接。但也許是中年的緣故,《無名者》的調性變得比較抒情一點,有更多的牢騷、糾結與人情世故。
「胡晴舫則戲稱自己是從少女變成歐巴桑」,個性放鬆了,所以《無名者》中可見更多游移與不確定,且「有了餘裕把空間讓出來,讓讀者進來」。當然這個空間裡依然不提供解答,「我很討厭正確答案這種東西」,她這麼強調。
我提及「無名性」在「中年」的帶領下拓深了問題的層次,從國族與文化來到自我認同,其中有一種流離與恍惚的迷失感。聶永真卻不同意,他認為與其說迷失,倒不如說是細膩而豐富,「但她又很喜歡把這些豐富壓縮為米粒般的小個體,以旁觀者的姿態隱藏在人群裡,把自己看成眾生中極其渺小的一個人。」
胡晴舫並未直接回應聶永真,卻冷不防拋出了一個意象:「如果自我是一襲華美的袍子, 或許有人會選擇把它掛好,我的選擇是把它穿出去,讓它沾滿城市的灰塵,任其風吹雨打, 當纖維開始老化,最後或許會敗壞成一堆破布,我也不介意,我覺得那才是人生。」
這令我不禁好奇,中年心境會阻撓年輕讀者進入嗎?聶永真說:「我自己覺得晴舫的文字對任何一個世代而言,都是必讀的經典。」胡晴舫則說:「老實說如果他們感覺到年齡的距離,那就是我的失敗,因為我始終相信文學如星辰,而仰望是人類的天性。」

☞致無名者的一封情書:胡晴舫╳聶永真 從書封設計共談無名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