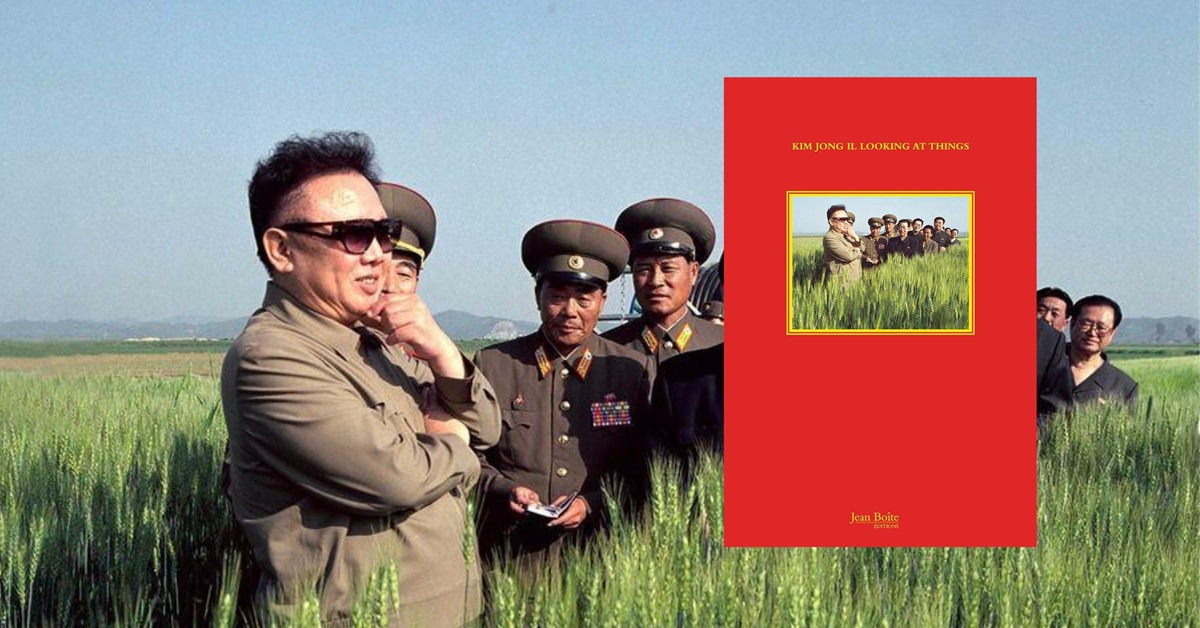對一個群體貼上標籤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我」這麼認為就可以肆意隨便貼上一些莫須有的誤解。但卻不曾深思,這些被擅自貼上標籤的人該做何感想?面對這些流言蜚語,就算不斷反駁,也輕易地被「偏見」洗刷掉所謂的現實。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我們都被貼滿了標籤》透過一個服務弱勢族群的社工者視角,帶領讀者了解第一線社工的真實寫照,也從不同視角看待他們與弱勢族群所遭受的不平等對待和汙名化的現實。但事實上,他們都是人,也都存有情緒,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支持。
{本文內容由這邊出版提供;僅反應作者意見,不代表誠品立場;未經授權,請勿轉載;首圖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
我是社工,不是志工
「你大學考得怎麼樣?」一名親戚在家族聚會開啟話題。
「還可以啦。」
「考上什麼學校?」
「北大社工系。」我回答道。
「北大?你是說北京大學?」他露出疑惑的表情。
「不是,是台北大學。」
「我知道。北科大?還是台北商業大學?」
「都不是──是台北大學,以前叫做中興法商。我們學校在三峽,不過我是在台北校區。」
「噢,我知道了。」不,你不知道,你只是不想再爭辯了。
他決定轉個話題,既然不知道你到底念什麼學校,讀什麼科系總搭得上話吧?
「你是說社工系?我不知道當志工還要讀大學。」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這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猜至今爸媽可能也不知道我的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但至少他們不會再錯把社工唸成志工。熟能生巧嘛。
同事告訴我,她當社工已經三年了,家人偶爾還是會把社工唸成志工。
「再過幾年他們可能就不會唸錯了。」我再補充:「也有可能即便唸錯妳也懶得糾正了。」
我正準備去買電影票。
「先生,請問你辦卡了嗎?平日看電影享六六折喔!」
我身為社工,勤儉持家幾乎是標準配備,當然不會放過省錢的好機會,於是停下了腳步。
「請問你在工作了嗎?」
「對。」我心裡很急切,不是說辦卡看電影享六六折嗎?
「方便請問你是做什麼工作嗎?」
「我是社工。」
「志工?」
「不對,是社工。」
「噢,志工啊……那個有薪水嗎?」
「有。」我辦卡的意志已經開始動搖。
「是車馬費嗎?」業務員很努力想要拿到業績。
「不是,是月薪。」我說完後,他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那應該沒問題,我不知道志工也有薪水呢!這邊幫我填辦卡資料。」
後來我當然辦了卡,畢竟不管被誤認為是志工或什麼的,看電影享六六折還是比較重要。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我跟同樣當社工的朋友填了餐廳的滿意度問卷。對,肯定又送了什麼東西,八成是提拉米蘇。
「哇!你們是社工呀!」
看來服務人員很懂社工啊!我差點感動落淚。
「你們一定很有愛心。」
我們沒有回應,這不過是大眾對社工無數的誤解之一。這麼多年過去,我們已經學會不爭辯了。這位服務人員真的很熱情,沒有枉費我們在服務態度那欄打了五顆星。
「我媽退休後也去當社工,你們這麼年輕就當社工,很不簡單耶!」
大姊,我猜妳把社工跟志工搞混了──但我可是很會做人。
「哈哈,妳媽媽一定很有愛心。」我乾笑。
算了,有提拉米蘇比較重要。
社工很常開會,對象或許是同行,或許是其他職業的夥伴,會議往往聚焦在如何促進特定服務對象的福利。
或者互踢皮球。
噢抱歉,是「劃分權責」。
不過當天會議比較像是相互認識,介紹我們為身心障礙者辦的活動──我好像還沒說過,我在社工的領域是「身心障礙」。
一位社區發展協會的大姊上台致詞提到我們。她說:「我們都很感謝○○中心的志工們,很用心辦活動讓身心障礙者參加。」
「社工。」我們其中一位同事糾正道。
「他們志工真的很用心,辦的活動也都很豐富,每一位志工都很熱情!」
「是社工。」另一位同事拉高音量。
「我們○○社區有這群志工真的很棒。」
大姊下台以後,換我上台講話。
「其實○○社區發展協會的大哥、大姊比我們更棒、更辛苦,很感謝她這樣稱讚我們。不過,我還是要強調,我們是社工,不是志工。」
我下台後,同事都在偷笑。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是殘障還是身心障礙?
「你是社工呀?」
某天我將鞋子拿去永和一間知名的洗鞋店,留下姓名電話並付錢給商家時,老闆看見我的名片,上頭寫的職稱是「社工」。
「太好了!我們最近想要開始用殘障人士,你對殘障熟嗎?」
殘障其實是民眾慣稱「身心障礙者」的舊稱,就連他們持有的「身心障礙證明」,也習於被民眾稱為「殘障手冊」。不過,由於「殘」字帶有貶意,所以多年前政府已經嘗試去汙名化,改稱為身心障礙者。通常我們並不會直接糾正仍這麼代稱服務對象的民眾,而是潛移默化地用我們的方式導正。
「我剛好是服務身心障礙的社工!」
「身心障礙?跟殘障是一樣的嗎?」
「沒錯,殘障聽起來比較不好聽,不過我知道你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們接觸的是智障那種,還是跛跤的那種呢?」
「都有,真的很感謝你!很難得會遇到願意聘用身心障礙者的雇主呢!」
「我這裡的工作很簡單,加上越來越聘不到人,想說他們那種殘……不是,是……」
「身心障礙。」我微笑道:「要花一點時間才會習慣。」
「對不起唷!」老闆接著說:「你們那裡可以幫我介紹嗎?不過……那種精神病的我可能要再想想。」
身為社工,絕對不會放過衛教的機會。
於是我花了一點時間跟老闆說明,其實並不是所有精神障礙朋友都會像媒體描述的那樣,有攻擊傾向或紀錄,他們大多性情溫和且用藥穩定,只是有部分精神症狀,難免稍稍干擾生活。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最後,我提供了老闆職業重建中心的聯絡方式,那是政府設立專門協助身心障礙族群就業的單位,店家可以主動表達聘雇身心障礙者的意願。他們聽到一定會很開心,畢竟這樣的雇主真的只是少數。
再者,會落入社會福利──尤其是我這種承接政府標案、負責個案管理──的服務對象,大多都還在與自身疾病和障礙對抗,就差那麼一步復歸社會。我很感謝老闆的好意,但多少會擔心介紹的身心障礙朋友力有未逮,所以不如讓在職業重建中心完成訓練、等待伯樂的身心障礙者嘗試看看。
當天,我在店裡待了半個多小時,向老闆解釋聘用身心障礙者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老闆很專注聆聽,畢竟他也擔心一個善意卻因為沒有準備或者哪裡不禮貌,而讓身心障礙朋友感到不舒服。
我相信未來老闆肯定都會改口稱為他們為「身心障礙者」了。
是標籤太黏還是不夠努力倡權?
從前面幾件事可以看到,無論是社工或身心障礙者都很容易被貼上標籤。社會大眾仍有刻板印象,不一定明白社工與志工的差異,即便朝夕相處的家人也未必清楚社工到底是什麼樣的職業。
身心障礙者同樣如此,家屬很可能沒有相關醫療知識,或許也會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誤解,更別說社會的「汙名化」。
標籤是中性詞彙,而汙名化則是更負向的詞彙,身心障礙者往往必須一輩子跟負向標籤對抗。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儘管經過不同社會福利單位的倡權與努力,並在政府逐漸重視下,身心障礙者逐步擺脫了「形式上」的標籤與汙名化─諸如改革專法,讓他們從沒有適用法條的困境一步步發展出「殘障」福利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到現在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然而很多人仍然不知道為什麼要修法,對他們而言,身心障礙者似乎永遠都是「殘障」。
雖然歧視與排斥隨著教育普及與提倡平等而逐漸減輕,但彷彿只是把不平等的目光從檯面上轉變到檯面下。當身心障礙者前往政府公辦的國民運動中心運動,仍然會遭到巡場教練的異樣眼光,宣稱除非家屬在場否則身心障礙者不得獨自入場。
即便我今天遇見了一位願意給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的雇主,但是,在社會上各個角落,多數雇主卻都不願意提供機會,導致他們求職往往處處碰壁。嘗試無望以後,他們最後只能退回家中,反倒讓周遭鄰居、朋友甚至家人,認為他們單純是因為懶惰而不外出就業。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圖片來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劇照
每一名社工在專業養成的歷程中,都會被教導要為服務對象提倡權益,只可惜無論社工或者政府,經歷過這麼多年努力「倡議」後,那些在身心障礙者與社工身上的標籤仍然被貼得緊緊地,只是稍稍翹起一角罷了。
身為社工,我能夠做的就是讓更多人知道,他們不一定跟你們想像的一樣。
身心障礙者需要的只是多一點包容,還有尊重。
這是一部社工與身心障礙者生命交會的故事。一邊是弱勢族群,一邊是服務弱勢族群的弱勢工作者,同樣不被認識,同樣不被理解。
社工不是活菩薩,不只做功德,他們有血有肉,當然也有情緒;身心障礙者則除了有形的障礙,還有更多隱形的需求,除了現實層面的資源,也需要情感層面的支持,只是我們往往看不到,或者選擇不去看。
▌正視呼喊的聲音,撕下誤解的標籤!
無形之中,我們會給既定的人事物貼上莫須有的標籤,然後對這些誤解產生無法抹滅的既定印象,擅自強加自身想法在他人身上。
《我們都被貼滿了標籤》以現役社工的身分,以實際現場工作經驗看待這些不平等。不只是弱勢族群,服務弱勢族群的弱勢工作者也遭受不被理解的困境。
很多時候,我們都只看的到自己,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物,卻不曾望向那些名為真實的殘酷。就算蒙蔽雙眼,也依然存在事實。現在正眼看看那些我們不曾在意,或者說不願在意的現實。
▊作者
王晨宇
1986年生,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2015年因八仙塵燃事件導致主管被調去支援,便臨危受命當上社工督導,從此改變了看待社會工作的角度。為了治癒升職後的「冒牌者症候群」,從抗拒證照化轉而於當年內取得高考社工師及格,認為與其消極抵抗制度,不如努力戰勝它,如此才能擁有話語權。誓言只要待在社工圈,就會當個認真盡責的社工,也會努力成為讓同事都能夠不討厭工作的社工督導。
✦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