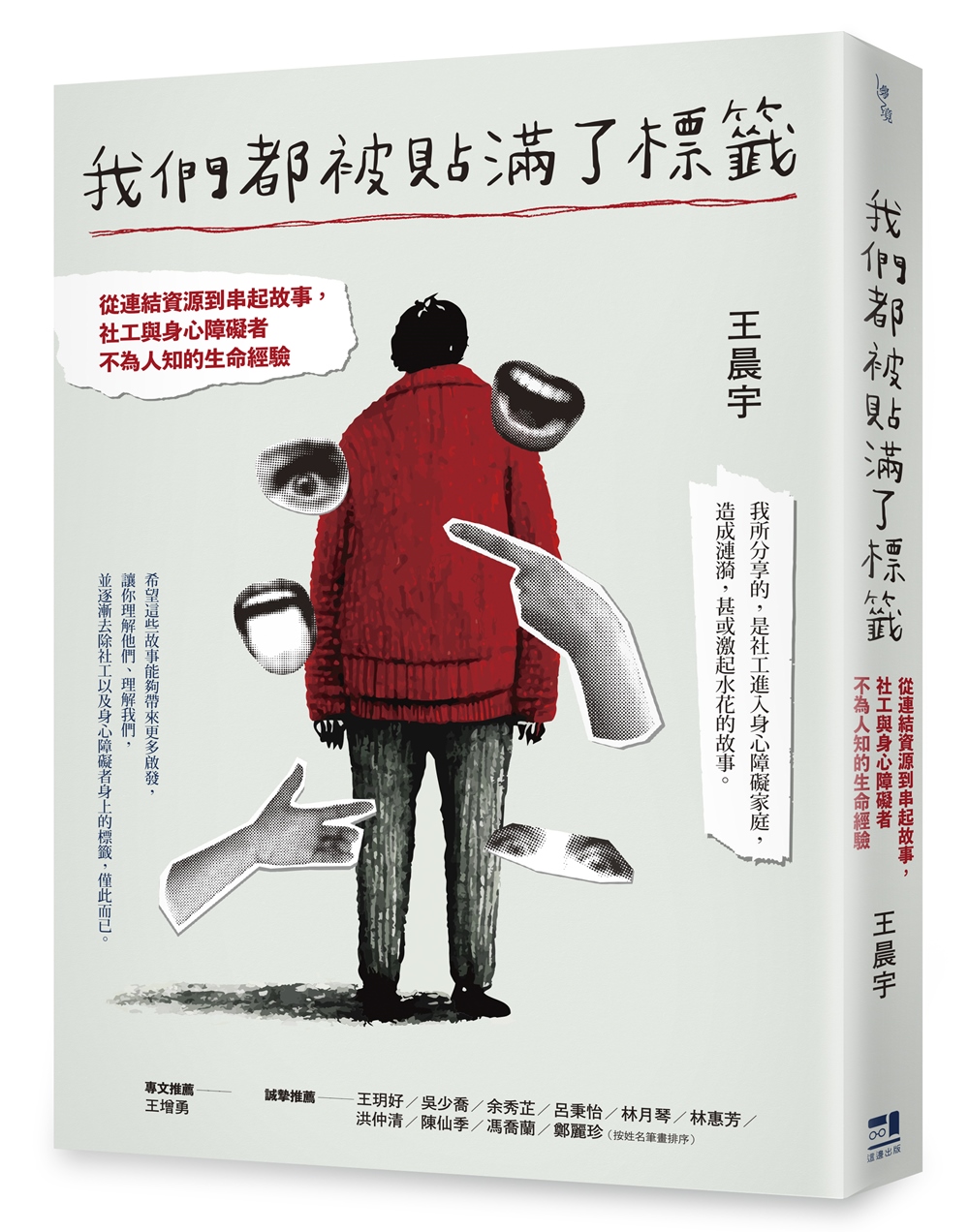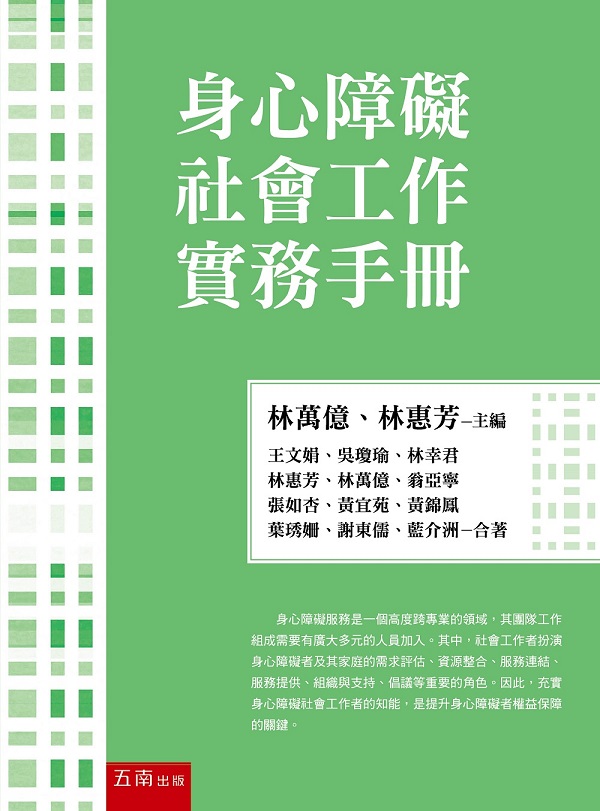对一个群体贴上标签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我」这麽认为就可以肆意随便贴上一些莫须有的误解。但却不曾深思,这些被擅自贴上标签的人该做何感想?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就算不断反驳,也轻易地被「偏见」洗刷掉所谓的现实。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我们都被贴满了标签》透过一个服务弱势族群的社工者视角,带领读者了解第一线社工的真实写照,也从不同视角看待他们与弱势族群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和污名化的现实。但事实上,他们都是人,也都存有情绪,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支持。
{本文内容由这边出版提供;仅反应作者意见,不代表诚品立场;未经授权,请勿转载;首图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
我是社工,不是志工
「你大学考得怎麽样?」一名亲戚在家族聚会开启话题。
「还可以啦。」
「考上什麽学校?」
「北大社工系。」我回答道。
「北大?你是说北京大学?」他露出疑惑的表情。
「不是,是台北大学。」
「我知道。北科大?还是台北商业大学?」
「都不是──是台北大学,以前叫做中兴法商。我们学校在三峡,不过我是在台北校区。」
「噢,我知道了。」不,你不知道,你只是不想再争辩了。
他决定转个话题,既然不知道你到底念什麽学校,读什麽科系总搭得上话吧?
「你是说社工系?我不知道当志工还要读大学。」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猜至今爸妈可能也不知道我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麽,但至少他们不会再错把社工念成志工。熟能生巧嘛。
同事告诉我,她当社工已经三年了,家人偶尔还是会把社工念成志工。
「再过几年他们可能就不会念错了。」我再补充:「也有可能即便念错你也懒得纠正了。」
我正准备去买电影票。
「先生,请问你办卡了吗?平日看电影享六六折喔!」
我身为社工,勤俭持家几乎是标准配备,当然不会放过省钱的好机会,於是停下了脚步。
「请问你在工作了吗?」
「对。」我心里很急切,不是说办卡看电影享六六折吗?
「方便请问你是做什麽工作吗?」
「我是社工。」
「志工?」
「不对,是社工。」
「噢,志工啊……那个有薪水吗?」
「有。」我办卡的意志已经开始动摇。
「是车马费吗?」业务员很努力想要拿到业绩。
「不是,是月薪。」我说完後,他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那应该没问题,我不知道志工也有薪水呢!这边帮我填办卡资料。」
後来我当然办了卡,毕竟不管被误认为是志工或什麽的,看电影享六六折还是比较重要。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我跟同样当社工的朋友填了餐厅的满意度问卷。对,肯定又送了什麽东西,八成是提拉米苏。
「哇!你们是社工呀!」
看来服务人员很懂社工啊!我差点感动落泪。
「你们一定很有爱心。」
我们没有回应,这不过是大众对社工无数的误解之一。这麽多年过去,我们已经学会不争辩了。这位服务人员真的很热情,没有枉费我们在服务态度那栏打了五颗星。
「我妈退休後也去当社工,你们这麽年轻就当社工,很不简单耶!」
大姊,我猜你把社工跟志工搞混了──但我可是很会做人。
「哈哈,你妈妈一定很有爱心。」我乾笑。
算了,有提拉米苏比较重要。
社工很常开会,对象或许是同行,或许是其他职业的夥伴,会议往往聚焦在如何促进特定服务对象的福利。
或者互踢皮球。
噢抱歉,是「划分权责」。
不过当天会议比较像是相互认识,介绍我们为身心障碍者办的活动──我好像还没说过,我在社工的领域是「身心障碍」。
一位社区发展协会的大姊上台致词提到我们。她说:「我们都很感谢○○中心的志工们,很用心办活动让身心障碍者参加。」
「社工。」我们其中一位同事纠正道。
「他们志工真的很用心,办的活动也都很丰富,每一位志工都很热情!」
「是社工。」另一位同事拉高音量。
「我们○○社区有这群志工真的很棒。」
大姊下台以後,换我上台讲话。
「其实○○社区发展协会的大哥、大姊比我们更棒、更辛苦,很感谢她这样称赞我们。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是社工,不是志工。」
我下台後,同事都在偷笑。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是残障还是身心障碍?
「你是社工呀?」
某天我将鞋子拿去永和一间知名的洗鞋店,留下姓名电话并付钱给商家时,老板看见我的名片,上头写的职称是「社工」。
「太好了!我们最近想要开始用残障人士,你对残障熟吗?」
残障其实是民众惯称「身心障碍者」的旧称,就连他们持有的「身心障碍证明」,也习於被民众称为「残障手册」。不过,由於「残」字带有贬意,所以多年前政府已经尝试去污名化,改称为身心障碍者。通常我们并不会直接纠正仍这麽代称服务对象的民众,而是潜移默化地用我们的方式导正。
「我刚好是服务身心障碍的社工!」
「身心障碍?跟残障是一样的吗?」
「没错,残障听起来比较不好听,不过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们接触的是智障那种,还是跛跤的那种呢?」
「都有,真的很感谢你!很难得会遇到愿意聘用身心障碍者的雇主呢!」
「我这里的工作很简单,加上越来越聘不到人,想说他们那种残……不是,是……」
「身心障碍。」我微笑道:「要花一点时间才会习惯。」
「对不起唷!」老板接着说:「你们那里可以帮我介绍吗?不过……那种精神病的我可能要再想想。」
身为社工,绝对不会放过卫教的机会。
於是我花了一点时间跟老板说明,其实并不是所有精神障碍朋友都会像媒体描述的那样,有攻击倾向或纪录,他们大多性情温和且用药稳定,只是有部分精神症状,难免稍稍干扰生活。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最後,我提供了老板职业重建中心的联络方式,那是政府设立专门协助身心障碍族群就业的单位,店家可以主动表达聘雇身心障碍者的意愿。他们听到一定会很开心,毕竟这样的雇主真的只是少数。
再者,会落入社会福利──尤其是我这种承接政府标案、负责个案管理──的服务对象,大多都还在与自身疾病和障碍对抗,就差那麽一步复归社会。我很感谢老板的好意,但多少会担心介绍的身心障碍朋友力有未逮,所以不如让在职业重建中心完成训练、等待伯乐的身心障碍者尝试看看。
当天,我在店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向老板解释聘用身心障碍者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老板很专注聆听,毕竟他也担心一个善意却因为没有准备或者哪里不礼貌,而让身心障碍朋友感到不舒服。
我相信未来老板肯定都会改口称为他们为「身心障碍者」了。
是标签太黏还是不够努力倡权?
从前面几件事可以看到,无论是社工或身心障碍者都很容易被贴上标签。社会大众仍有刻板印象,不一定明白社工与志工的差异,即便朝夕相处的家人也未必清楚社工到底是什麽样的职业。
身心障碍者同样如此,家属很可能没有相关医疗知识,或许也会对身心障碍者产生误解,更别说社会的「污名化」。
标签是中性词汇,而污名化则是更负向的词汇,身心障碍者往往必须一辈子跟负向标签对抗。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尽管经过不同社会福利单位的倡权与努力,并在政府逐渐重视下,身心障碍者逐步摆脱了「形式上」的标签与污名化─诸如改革专法,让他们从没有适用法条的困境一步步发展出「残障」福利法、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到现在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然而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为什麽要修法,对他们而言,身心障碍者似乎永远都是「残障」。
虽然歧视与排斥随着教育普及与提倡平等而逐渐减轻,但彷佛只是把不平等的目光从台面上转变到台面下。当身心障碍者前往政府公办的国民运动中心运动,仍然会遭到巡场教练的异样眼光,宣称除非家属在场否则身心障碍者不得独自入场。
即便我今天遇见了一位愿意给身心障碍者就业机会的雇主,但是,在社会上各个角落,多数雇主却都不愿意提供机会,导致他们求职往往处处碰壁。尝试无望以後,他们最後只能退回家中,反倒让周遭邻居、朋友甚至家人,认为他们单纯是因为懒惰而不外出就业。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图片来源:《健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剧照
每一名社工在专业养成的历程中,都会被教导要为服务对象提倡权益,只可惜无论社工或者政府,经历过这麽多年努力「倡议」後,那些在身心障碍者与社工身上的标签仍然被贴得紧紧地,只是稍稍翘起一角罢了。
身为社工,我能够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不一定跟你们想像的一样。
身心障碍者需要的只是多一点包容,还有尊重。
这是一部社工与身心障碍者生命交会的故事。一边是弱势族群,一边是服务弱势族群的弱势工作者,同样不被认识,同样不被理解。
社工不是活菩萨,不只做功德,他们有血有肉,当然也有情绪;身心障碍者则除了有形的障碍,还有更多隐形的需求,除了现实层面的资源,也需要情感层面的支持,只是我们往往看不到,或者选择不去看。
▌正视呼喊的声音,撕下误解的标签!
无形之中,我们会给既定的人事物贴上莫须有的标签,然後对这些误解产生无法抹灭的既定印象,擅自强加自身想法在他人身上。
《我们都被贴满了标签》以现役社工的身分,以实际现场工作经验看待这些不平等。不只是弱势族群,服务弱势族群的弱势工作者也遭受不被理解的困境。
很多时候,我们都只看的到自己,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物,却不曾望向那些名为真实的残酷。就算蒙蔽双眼,也依然存在事实。现在正眼看看那些我们不曾在意,或者说不愿在意的现实。
▊作者
王晨宇
1986年生,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毕业。
2015年因八仙尘燃事件导致主管被调去支援,便临危受命当上社工督导,从此改变了看待社会工作的角度。为了治癒升职後的「冒牌者症候群」,从抗拒证照化转而於当年内取得高考社工师及格,认为与其消极抵抗制度,不如努力战胜它,如此才能拥有话语权。誓言只要待在社工圈,就会当个认真尽责的社工,也会努力成为让同事都能够不讨厌工作的社工督导。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