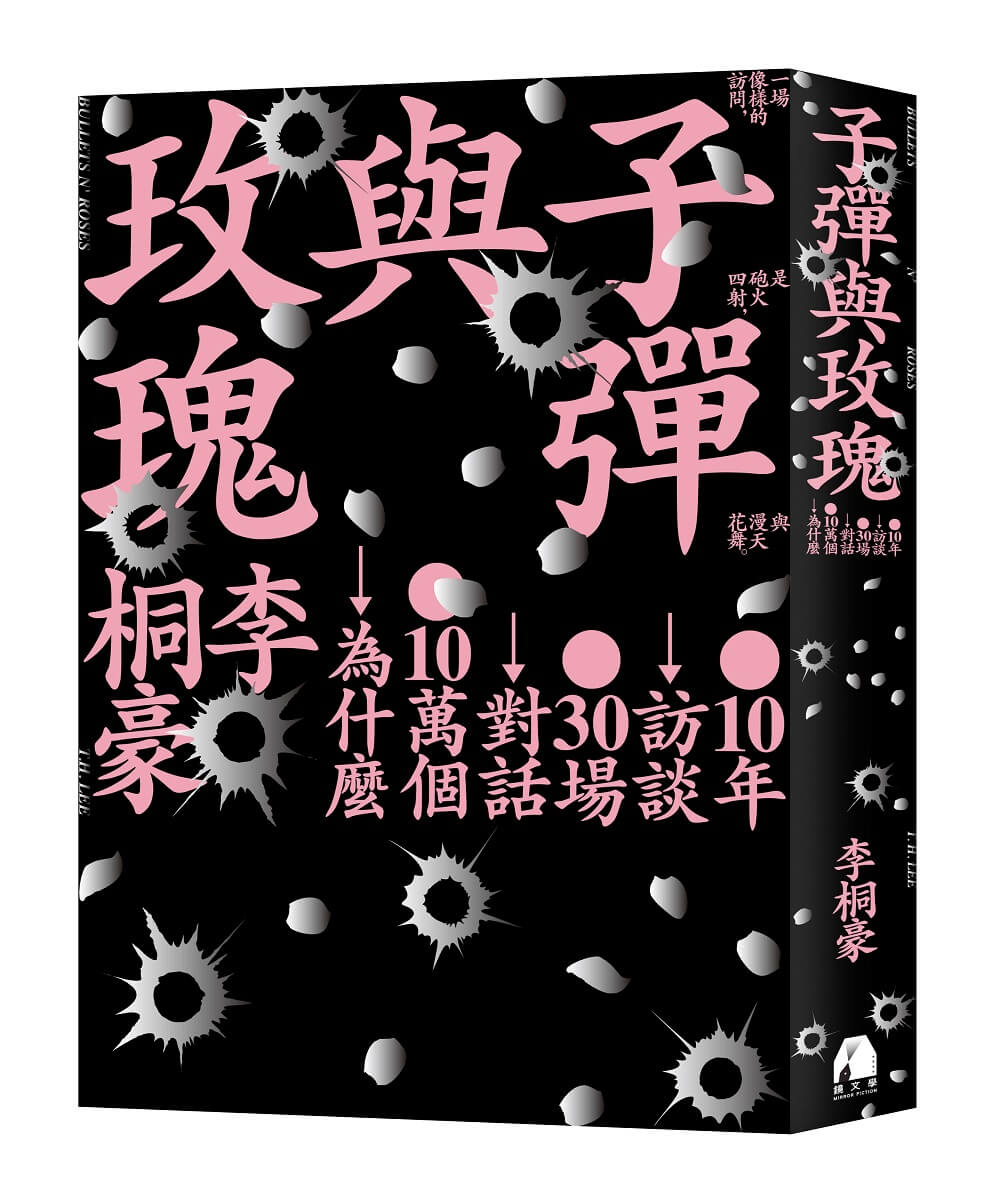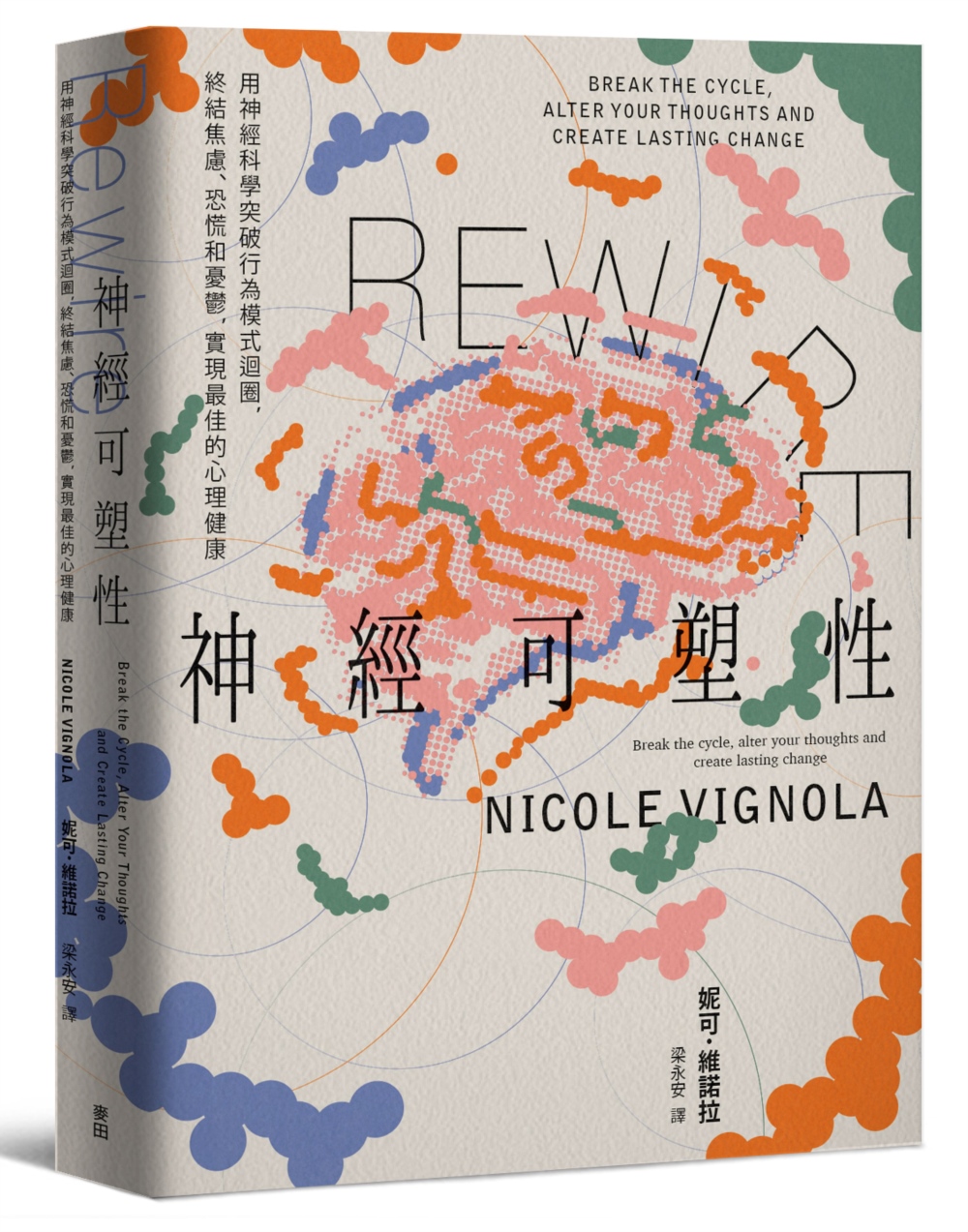没人可以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专访记者李桐豪,与他手中的风月宝监
撰文 翟翺.攝影|Ogawa Lyu.場地協力|達文西咖啡──「访问不是按下录音笔才开始,从第一眼你看到那人就开始了。比如说今天为何翟翺迟到了(按:迟了两分钟),你今天穿了一条有束绳还要系皮带的裤子,一件鸽子图案的上衣,是不是因为出门前在搭配这身衣服?」
──「其实我只思考了五分钟穿啥。」
──「所以你不是很在乎这个访问?」
──「没,单纯我找衣服比较快。」
──「那为何要刺一只鸭子两只鹅在身上——难道是因为你叫翟翺吗?为何名字叫翺,可是刺鸭子这种水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能高飞?(按:并不是)」
以上是李桐豪亲身为我示范了一场访问该如何进行。
但与其说这是他访问人十年积累的功夫,不如说是内向者如他拆解并重组访问的心法。「其实我不是很会说话,一开始我接人物采访,根本不知道要怎样进行,甚至去找CIA教你判断人说谎这种书参考。但有天读到应该是葛林写的,一个才情的女孩,只要经过一个军营,就可以写出军营的故事,这点醒了我,我是写作者,那我就去发挥写作者最大的功力。」
所谓最大的功力,如今都在这里了,李桐豪十年人物采访集结:《子弹与玫瑰》。
访不到真话怎办?
何以叫《子弹与玫瑰》?「因为访问应该要恩威并济,亮出玫瑰与子弹跟一样重要,前者像是哄对方说话,後者有逼供威胁的感觉。还是你访问人都是亮出玫瑰?」(又一个反问。)
《子弹与玫瑰》收录约三十篇采访,分为「笔杆之下」、「光影之中」、「庙堂之上」三辑,分别对应访者的写作者、娱乐圈、政治界身分,从白先勇到黄山料,李安到李登辉,个个都是大咖。
然而读过一遍会发现,辑一里李桐豪比较常把「话筒」交给受访者,通常一个他的提问之後,就接着对方一连串回答——通常是有排面的话,金句夹针,棉里藏刀,但辑三访政治人物,侧写多了,大块的回答少了。
对此,李桐豪的说法是:「访问有各式各样方式去抵达那个人,用旅游记者的比喻来说,有搭直达车,有迂回的转车或普快站站都停。访政治人物,重点反而不是说话内容,因为他们讲话都有所本,常常很无聊,不如去写他用怎样的方式、气势、姿态说话,才好看。」
一个例子是,收录於书中的2016年王金平访问。老狐狸答非所问,李桐豪就描摹他打太极的本事;即使刻意诘问,王金平「面对我们质疑,他音调未有起伏,侃侃而谈。」於是,这篇充满「侃侃而谈」又「开口闭口都是佛教修辞」的采访,李桐豪下的标题是「却把官场做道场」。官场与道场,并无高下,重点在个「却」字。这是访问者的微言大义了。
这点,多少跟领李桐豪进人物采访领域的前主管董成瑜有关。「我写人物组三四个月後,董成瑜就去写剧本了,但我记得她讲过一次,说如果一个人是泳池,你不应该只写有人在游泳,偶尔也看看天气如何,泳池规模空间感,或是其他泳客。」因此,人物组的训练是,访问一个人要访问他身边各种人,亲朋好友冤亲债主,至少五个以上侧访。
访到真话,又该怎办?
提到人物组,前後主管同事包括董成瑜、房慧真都出版过采访集,会不会害怕被拿来跟他们比较?李桐豪的回答是:「不会。」
因为他觉得自己跟他们访问人的方式很不同,也曾观察他们的采访,「董成瑜有种古怪的幽默感跟新奇的比喻,房慧真像是斗犬,咬住一点就不放;董成瑜曾说采访要彷佛跟受访者谈恋爱那样努力,而房慧真采访则是彷佛要变成那个人。」
谈恋爱跟想变成,都很深情,但李桐豪不是。「其实我很怕对方跟我说真心话,如果访者要跟我说一个秘密,我会说我不需要那麽多,只要我的标题有了,问到想问的就好了。」像是访写小说怨毒着书的朱天心,提到跟昔时文坛友人如黄锦树「失联」,直接给了一个「很直接粗暴的说法」。
「我跟她说,你知道你正在对一个狗仔记者说话吗?但讲了三四题之後,朱天心又绕回来说:『你让我把这些讲完。』我跟她说,你这样会让我困扰不知道要不要写。」
写出来了吗?看官不用急着翻书,答案是没。我问李桐豪:「如果你今天面对的是政治人物,你会不写吗?」李桐豪拐个弯答道:「访问人,我自己会有一个终极问题想问,例如访王小棣,我想问他为何不去变性,访白先勇则是『你到底把王国祥当什麽』(按:真的都有问也有写)。所有访问的软玉温香,刀光剑影,都是为了问到那个终极问题。」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书名《子弹与玫瑰》,而我的子弹(或玫瑰)并未特别有效。我接着问,害怕别人说真心话跟做访问有冲突吗?「当然有冲突。我很庆幸是在成瑜要离开时接下人物采访,我觉得她的方式没有很适合我。她看起来很温柔的,但其实咄咄逼人。当然那时也在纸本很有权威的时代,可以像用枪抵着对方,逼对方说出来,但媒体环境已经不像过去会让人想受访。」
「现在文字不是那麽令人相信了。」李桐豪说。
访到假跟错,还可以怎麽办?
很难想像曾「绑架张爱玲」,三不五时用典《红楼梦》的李桐豪会作如是想。但纸媒光环不再,人物组的招牌应该还是很吸引人吧?「应该说受访者愿意接受访问,都会预期受访可以得到什麽,然而,我都会想打破那个预期。例如访问《湾生回家》的田中实加,算是因此幸免於难。访问前,我都会帮访者制作年表,但我做她的,时间跟生平怎麽做都对不上。我问她『你的中学在哪读?』最後她回我说她是在台湾读的。」
李桐豪对此的定义是:「问到某种所谓的真相,这与冒犯无关,比较像是事实查核。」
或者,按照李桐豪的比喻,那是「系统柜露出的衣角。」「我是一个收纳狂,秩序的建构者,然而访问好看的地方,在於发现你没办法收纳的线头或物件。人都是有想被倾听的欲望,有的人是系统柜,很有秩序也很无趣,但即使是系统柜,你也会看到一截内裤或衣角,这时就会让你想去抓,抓住没那麽理所当然的事,人的冲突跟反差,采访才会中。也因此我命名文章的方式常常是对比的。」例如书中收录的黄山料〈中二与中年〉,蔡琴〈女王与仆人〉,赖清德〈白袍与西装〉,童仲彦〈西门庆与贾宝玉〉。
采访像帮人收纳,这个说法李桐豪不止讲过一次,这心法是一开始就掌握的吗?「不是,是我後来自己找出的,觉得应该是要成为访问界的近藤麻理惠,帮采访者收纳人生故事。」
但这是一个连近藤麻理惠都放弃完美收纳的世道了。李桐豪回我:「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我觉得没人可以真正走进一个人内心,只有那人摆设出来的模样。」曾觉得没访到真相吗?「描写性格比他说了什麽重要,讲话可能前言不对後语,但我比较不会较真,反而人设崩坏才是人们在意的。」或许访问界的近藤麻理惠,明白收纳後的房间跟IKEA样品屋无异。
如同此刻访问,我对李桐豪最深刻的了解是:他有整理分类癖,但仅限於务虚,现实中不会,例如色情片跟iTunes,他都会仔细分类好,「iTunes有的封面不正确,我会上网抓到正确的丢进去。」也例如谈到《红楼梦》,他说自己只重看前八十回,因为「会把後四十回拿来说事的人都不可原谅。」又例如,连问他如何整理受访者文稿都得不到答案:
──「那你的分类逻辑是啥?」
──「就是东洋、西洋……」
──「我是指受访者。」
──「但你不想知道我D槽的标签吗?」
用子弹与玫瑰取话,却害怕真心剖现;自言秩序的建构者,但仅限於虚拟世界。当最真实的爱憎,都在风月宝监,以假为真,又何烧此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