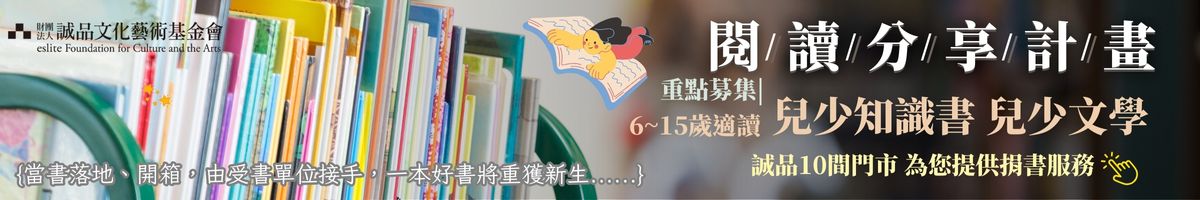無法被定義的人性面貌:電影裡的情感真相
撰文 Kristin(一頁華爾滋)世界上出現過無數令人髮指的社會案件,寫成看似公正客觀的報導文字與新聞畫面時,尤其顯得驚世駭俗,但往往在深入了解前因後果,甚至是時代背景之後,反而會萌生一股感同身受,讓許多看似天理難容的行為,變為一曲情有可原的生命悲歌。那才是真相,真相不是毫無溫度的監視器畫面,真相還必須將人的感受、情緒、記憶化為故事,那才是屬於身為一個人、而非機器的情感真相。
「如果你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或許才是藝術試圖達到的。於事實與真相之間打破隔閡,化解人心的成見及衝突,進而改變人們看待現實的紋理,無數故事的創作初衷便奠基於此。
因而,這一次選了五部圍繞於此的電影,假使以駭人聽聞的程度循序漸進來區分,第一部談論的應為2018年的《小偷家族》(万引き家族)。是枝裕和暖調性的故事以一場光天化日的竊案開啟,看似父子又不似父子的兩人,以絕佳默契在超商偷取生活所需的食物與用品,如此模糊而朦朧的家庭關係掩蓋著一些見不得光的過去,建立在搖搖欲墜的血緣關係之上,就這麼於此處被高樓大廈環繞、只看得到半邊煙火的民宅裡生了根。裡頭有一位奶奶、一對父母,還有姊姊與弟弟,彼此看顧,相互照應,事情卻因一個四歲卻渾身傷痕的小女孩尤里加入而掀起波瀾。
可想而知,新聞媒體與外界眼光會這麼予以批判:誘拐兒童、四處行竊、從事特種行業,甚至還有殺人犯藏匿其中。但換成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又無法粗暴憑單一是非標準來衡量這一家人。

在一層一層暴露人性缺陷的過程中,觀眾彷彿隨著故事見證,日子過得去就好,生存之外更重要的是生活之中的平淡與快樂。安藤櫻四弦一聲如裂帛的驚人詮釋,一箭刺穿整個社會的表象。追根究柢,家的本質究竟為何?有生育能力就等於具備為如父母的資格嗎?是枝裕和將這個無解的問題拋給觀眾,畢竟,任何事物都可以竊取,除了羈絆,那也並非因血緣而與生俱來。而唯有真實的情感,才足以於道德標準反覆擺盪之際,撼動觀眾們根深柢固的價值觀。

▶︎圖片來源:光年映畫
同樣習慣將目光放在社會邊緣分子的韓國導演李滄東,其代表作之一《綠洲》(Oasis),則透過一對不容於世的戀人之愛情,以善與真直接碰撞我們過去判斷大是以及大非的底線。一位是三度進出監獄的更生人洪宗道,一位是重度腦性麻痺患者韓恭洙,他們之間扭曲畸形的愛情從一場強暴未遂底下萌芽,化為將軍與公主的浪漫戀曲。
相由心生,就是多數旁人看待他們的批判目光,性、愛的本質是再自然不過的行為,卻於社會的有色濾鏡裡成為髮指罪刑。這是後話,因為尚未觀看《綠洲》之前,應該不會有人秉持著如此想法。李滄東覺得,這些稱不上討喜,承受痛苦、奮力求生之人,才是貼近自己生活經驗的角色,正因如此,他沉重的鏡頭感受不到一絲上對下的憐憫,始終平視,如實呈現洪宗道的毫無心眼、不可理喻,如實呈現韓恭洙的孤立無援、弱勢處境,如實呈現一個人身上同時散發著光明與黑暗,同時扮演受害者與加害者。
雖無同情,卻有憐惜,李滄東亦選擇透過魔幻手法,在與大象、印度女子與孩童共舞的想望裡,將真實帶到觀眾眼前,注入了美和自由的力道,那是形體難以禁錮的人間至善。因此,在體制之外,有沒有可能真相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故事?有沒有可能,世間確實存在千百種愛情?當我們的社會一廂情願簡化問題時,再也不會有人能理解,那名瘋子為何千辛萬苦逃出看守所,只為鋸掉路旁某棵不起眼的枯樹。

▶︎圖片來源:IMDb
至於,問題不應被簡化,悲傷背後永遠藏有悲傷,痛苦之外往往是更深的痛苦,而這些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因為那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韓國先有《熔爐》,從外界眼光審視從,而後臺灣誕生《無聲》,內在觀點出發,故事主要源自於2011年台南一所特教學校爆出的醜聞。私以為後者更加出色,在於創作者無意強調正邪對立,或直接喚醒集體良知,巧妙避開單薄劃分是非對錯,拒絕採用一目了然的粗糙手法將罪狀歸於體制弊病或權力壓迫,只為塑造一個反派讓觀眾可以獵巫、咎責,甚至人們得以為自己平時的多數默不作聲卸罪。而是轉了方向,凌駕於單一事件之上,層層剝開聾啞孩童的內在困境,設法呈現他們有口難言、極度恐懼、面臨絕望深淵的模樣,也深入挖掘這群身不由己的孩子保持沉默、長期隱忍,且不停歸返的原因。
「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鏡頭隨一位初來乍到的聾啞少年張誠步入陌生啟聰學校開展,純真笑聲於祥和寧靜的校園中此起彼落,似乎是一塊屬於聽障孩童遠離塵囂的樂土,卻無處不瀰漫詭異壓迫、坐立不安的氛圍,似乎某個不知名陰影潛伏在角落蠢蠢欲動。隨他一步步接近風暴核心,拉著唯一可信的大人四處奔走,才漸漸認知那無法明說的悲劇全貌早已超乎他們所能控制、改變的範圍。
探究真相,並不是只為讓壞人罪有應得,而是拒絕目睹悲劇持續在其他孩子、下一代、下下代身上重演,偏偏那有如地獄之中的惡性循環,無法單憑司法懲戒、輿論撻伐逼出代罪羔羊。若想解決問題,第一步得先承認問題存在;若想面對癥結,則須培養長遠而宏觀的視野,勇於溫柔追問,勇於承擔責任。痛也是癒合必經的過程,這才應是人們關注社會問題的真正目的。

▶︎圖片來源:IMDb
沒多久之前上映修復版的《感官世界》,為導演大島渚改編自1936年撼動日本社會的真實新聞「阿部定事件」,她在東京的茶室將情人勒斃並割下其性器官,引發軒然大波,最終判決結果卻出乎意料地只有六年刑期。法官認為阿部定的行為是太過癡情所導致,也因事件相當獵奇,不但在日本大眾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比起指責,更多的是理解,也使她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更啟發好幾部經典作品,包括渡邊淳一的小說《失樂園》與森田芳光的改編電影,黑木瞳飾演的女主角就是以阿部定為人物原型,當然,還有這部真槍實彈演出的《感官世界》。

大島渚鏡頭下的男女主角,透露著一種病態的情慾和對死亡的迷戀,雖然整部電影涵蓋無數性愛場景,但如此畫面既不香豔,亦不煽情,卻可以為此廢寢忘食、醉生夢死,無法填補的慾望成為兩人世界中最自然的一部分。他們猶如格雷安葛林筆下更幽黯獵奇的凡夫俗子墮落愛情,茫然,麻木,任由妒恨與身體本能主導理智,將觀眾捲入愛慾難分難捨的困惑之中。就如《失樂園》所言:「若沒有將一切燃燒殆盡的愛,如何留下一片焦原?」

究竟沒有太多時間深入交談、認識、了解彼此的阿部定和吉藏譜出的是單純的慾望,還是更超越我們所能理解的愛情?若是愛,那也是無異於普遍的愛情嗎?若不是,難道世間存在著別種無法定義的愛情?有時候那無關乎道德,更難以抽身,在愛情與毀滅之際,人們方能領悟,死亡才是永恆的高潮。《感官世界》的結局大膽挑戰了觀眾的底線,為世不容的瘋狂,是戰時肅殺氛圍多一點,還是感官放大到極限的愛多了一點?大島渚真正從藝術價值潛入心境的更深一層,以奇觀面對人性與時代勾勒出的各種輪廓。

▶︎圖片來源:金馬影展
放在最末的,是楊德昌時隔三十年仍恆久不墜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聚焦於一起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的青少年情殺案件。這部作品不只關注著1960年代的生活,同時嘗試重新定位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凶手?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原本只是小成本的製作,關於一對少男少女的青春愛情故事,以悲劇收場,最後卻越寫越大,越寫越完整,最後的成品散發出一股史詩氣勢。純真的失落,道德界線的崩壞,是楊德昌不停透過電影探討的核心,他正是親自走過1960的最後一代,始終著迷於這個時空背景,台灣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社會極端不自由,他以精準嚴謹的歷史態度傳遞了彼時人們的生活與心理狀態,因而寫下了電影開頭一段敘述: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然而,在這下一代的成長過程裡,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往往以組織幫派,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英文片名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Brighter」一詞尤其耐人尋味,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小四是一個敏感壓抑又帶有些正義感的少年,生活的一切卻漸漸擊潰了他的理想主義,一句「我和世界都是不可改變的」,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把短刀殺死了愛與純真,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所有美好期許,青春、信念被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因此,小明的隕落,就是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他則成為應運而生的恐怖分子。
回望這些無法受陳規定義的是非對錯,每個故事皆有各自身不由己的情感真相,即使無法作為犯罪的正當理由,卻是大眾必須理解、傾聽的複雜面向,那才是藝術為人們,為社會帶來力量的真正原因。
「永遠都存在著一個夢想,一個嚮往,一種對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存在的信心、期待、依據。」
——楊德昌
✦
{本文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誠品立場;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撰文者簡介|Kristin(一頁華爾滋)

☞閱讀更多Kristin@迷誠品專文
FB粉絲專頁《一頁華爾滋 Let Me Sing You A Waltz》版主。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英國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國際行銷碩士,文章散見各網路媒體。著有電影文集☞《光影華爾滋》,喜愛透過觀影、閱讀探索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

▌看電影的人
☞《我深愛的雷奈、費里尼及其他》

☞《看電影的人》

☞《反派的力量》

【迷誠品專欄|葉郎電影徵信社】
☞解凍美國隊長:病毒碼過期的超級英雄
☞戀夏35000日:冷氣機如何改變電影產業
☞盧卡斯《五百年後》(THX 1138):一場左右電影史的片廠竊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