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经梦想有这样一家书店──马欣
撰文 馬欣本文授权转载自非常木兰,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从何时开始,任何人的「时代的眼泪」讲起来都是不咸不淡的,甚至上个月还有百来人跟你一起感怀的,今朝起来再提起已是「不合时宜」。
包括这城市里仅有的一间24小时的书店。
我记得五年前,跟一位编辑友人一起走过因耶诞节显得灯光闪闪的敦化南路,我们当时仍可以夸口着那个月的特别企划如何的用心,或是还想要年底的企划找来哪一位摄影师一起完成。但我们那时已经知道那是在超支纸本杂志的梦想,我们很安分地有一日是一日的实践自己梦想。
那一日还是12月初,寒流经过,我们裹得紧实,下意识地就经过敦南诚品的门口,看到他们工作人员在门口为节庆搭景,我那朋友待过《诚品好读》杂志,於是上前一步跟前同事聊天,几个人很快就热闹地在寒风中嘻嘻哈哈起来,即使谈起工作也乐在其中。
那时还有好多小摊位在敦南诚品门口,小黄络绎不绝排队在门口等客人……想来也不过五年而已,朋友与我都已改行,诚品敦南店也将在明年歇业,有如黄粱一梦。
当然这五年,这城市或这世界都改变太多,任何感怀对成熟的大人来说都是该习惯的。
但曾经,只是曾经而已,曾有一家书店坐落在敦南与仁爱路口,不大不小,你踏着楼梯可以听到木质地板的响声、大型木窗是在欧美书报上看得到可以往外推的半掩、书的摆放方式与位置一点都不局促。你转个弯就是绘本区或画册的惊喜,每一块书区的陈列都有对那些书的心意,跟台北早期像文具店或教科书店的摆放不一样。你一进去就明确知道,在这里,主角就是书,是一间像森林一样的书店,人可以没有目的性地去发现,或只要单纯去仰望就好。
一间可以理所当然身为一家书店而且理直气壮存在的大型书店。我们曾经集体做过这样的梦,时间不长不短得来证明这刚好只能是一场梦。
不用附庸在别的商品之下,也不用堆放如仓库,去的人不只是因为买书,而是因为那是为了书而存在的空间,你对那里因此有份敬意,你知道几百年来有多少人接力写着,你知道世上曾经有多少大师的心血与智慧,你挑书,它也挑你,你愈读就愈渺小,并且欣喜於这份渺小。
毕竟这个城市,已没剩下什麽可以让人仰望的,每少一点值得仰望的事物,人们就会少一次感动。
或许现在提到我在书店学会仰望这件事讲起来多麽不合时宜,我因为要拿到上两层的书,要把手伸得老长,让自己感觉像个儿童的那一刹那有多麽开心,或是低下头来屈膝着找某位作家还有哪些书的新大陆滋味。那些藉由身体记忆在一家书店东转西弯,从第一个平台,走到最後人最稀少的一区,然後坐在木头地板上翻着那三五本书,忘记时间的周末午後,中间没有任何咖啡或零食摊位,就是单纯在翻阅与找书中忘记自己而已。
讲起来真太不合时宜了吧,如同三十年前,诚品第一家书店出现时,那时记忆力还很好的母亲像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城市终於有一家很美的书店了,像她在国外看过的那样,於是带着还穿着校服的我去挖宝,我一直难忘那个周末午後,傻子样地跟我妈说:「这好像是我在欧美电影里才看得到的书店。」那天阳光很好,我在木窗旁挑着书,觉得一切梦幻得不像话。
後来它搬到更大的地方,没有那麽单纯的木头与书香,但没关系,有一排排的人跟我一样傻气拿着外国杂志,等着书店的人为我拆封试阅,那麽小心翼翼地不要有摺痕地翻完还给店员,像是交换着一种默契,我们彼此很珍惜这样的试读机会。我在那家书店发现米兰昆德拉,激动地看完《缓慢》,发现读一遍都不够,於是每本珍惜慎重地带回家。
大概在十多年前,我们像书有树的芬多精,吸满了幻觉一般晕陶陶地离开那家书店,不是因为24小时营运後空气变得比较不好,而是自己又变得簇新地出来一般,因为总有几本书让我感觉自己变得不一样,让找到它们的我对这世界更有归属感。像个松鼠可以带果子,然後去过冬的归属感。
曾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排斥书单,甚至会对传给我书单的朋友生气,因为我喜欢把手伸得老长与弯下腰来去找书,我喜欢在偌大的空间里转弯又转弯好像我在挖宝一样,让某一本书认得我,那是我对世界仅剩不多的虔诚。
三十年前,就是1989年吧,我妈妈跟我说:「妹妹,我发现一个好地方。」当时我们每周都去。三十年後,我妈妈已经老到不记得多少字了,然後台北也即将失去一家只为了书而存在的大型书店了。
亲爱的读者,请不要以为我在写什麽业配文,我只是开始想念一进书店如进入一座森林的感觉,里面不需要有饮料,也不要有美食,只有一个想去探险的我跟森林之间的关系而已。
这样跟书的恋爱方式,是否也太奢侈了呢?
本文授权转载自非常木兰,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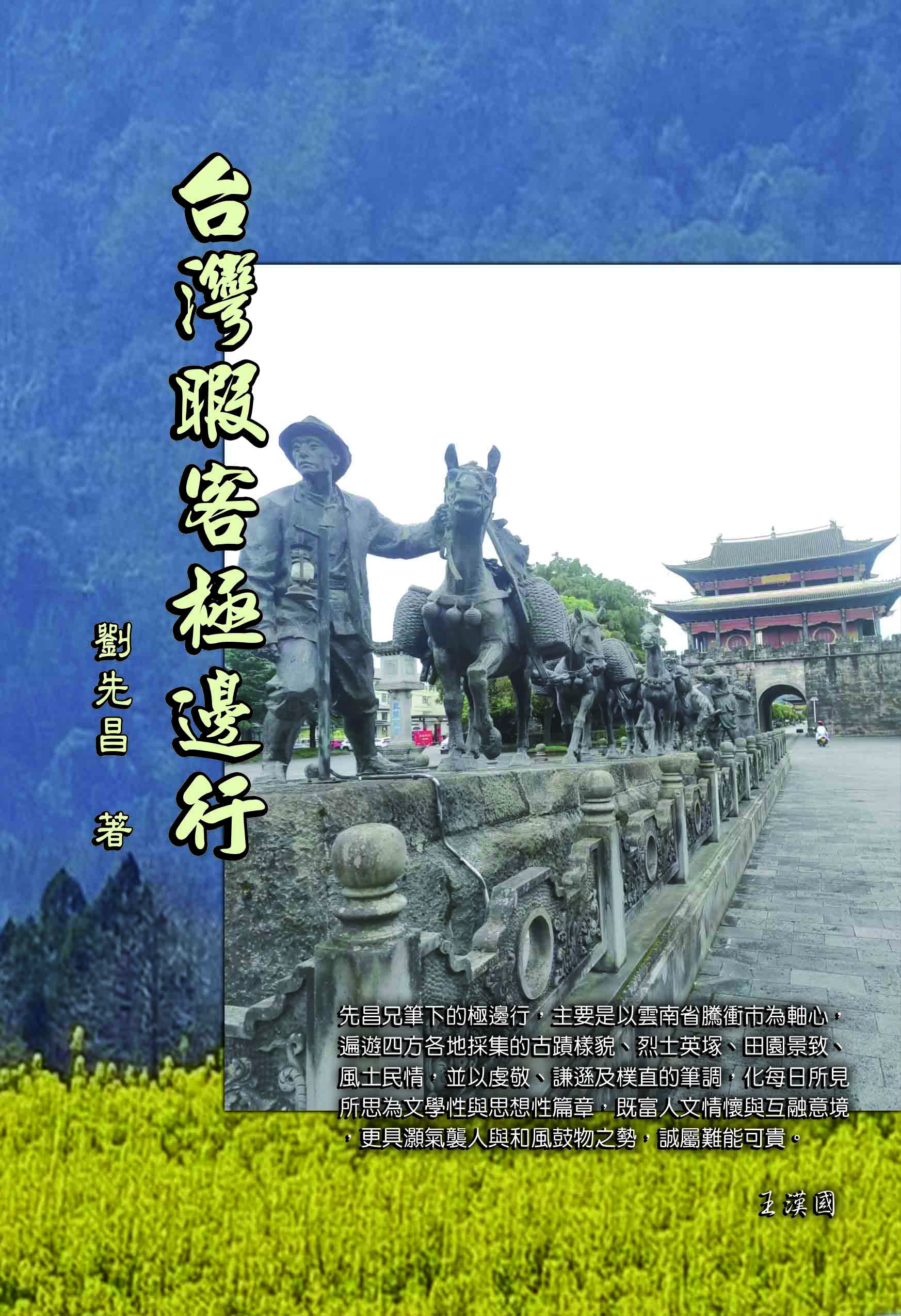









_2025042814263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