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窃听风暴》与《无主之作》中的西方意识型态:艺术保留神圣,排除了罪恶
撰文 釀電影:專為影癡而生的媒體(太空人 Astronautin){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酿电影(原标题: 《窃听风暴》与《无主之作》中的西方意识型态)}
一、前言
接着一位长者从观众席上站了起来,他的声音因压抑的愤怒而颤抖。他说他看过那部希特勒电影,那部电影真是糟透了,他觉得史贝柏格其实很欣赏希特勒。虽然他自己是波兰裔犹太人,家人大部分死於集中营,但「多亏那些动人的演说、美妙的音乐」,那部电影几乎要让他想要成为纳粹。
(Ian Buruma 1999: 116)
以上段落出自於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艺术评论集《残酷剧场》(Theater of Cruelty)的一篇文章〈只有故乡好〉(There’s No Place Like Heimat),描述了 1990 年德国导演史贝柏格(Hans-Jürgen Syberberg)与当代许多文学界人士谈论他 1977 年的作品《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Hitler: a Film from Germany)的景况。
布鲁玛於这篇文章中列举了许多与当代德国思想潮流不符合的知识份子及艺术创作者,如史贝柏格、钧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克丽斯塔.沃芙(Christa Wolf),但他的目的并不在批判这些人的「政治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相反地,他一一检视了这些人的作品及他们所袒护的信念与理想,并且从这些理念中归纳出反对好莱坞的特质、以及重回心灵之乡伊甸园的想望。
这些言论备受争议、遭到当代许多人挞伐,有的批斗史贝柏格为「新纳粹份子」(Neonazis),或是定调沃芙支持共产主义(Kommunismus),尤其史贝柏格在其论文集《战後德国艺术的幸与不幸》(On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rt in Post-War Germany)中对战後西德艺术的发展如是评论道:
现在艺术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战後德国人失去了对德国的认同感,将自己和孕育他们的土地之间的脐带剪断了。战後德国艺术变得「肮脏、病态」,这些艺术「崇尚懦夫、叛国贼、罪犯、妓女、仇恨、丑恶、谎言、犯罪等等不自然的事物」。(Syberberg 1999)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稍微明白大众对於史贝柏格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并非史贝柏格本人是否真的为新纳粹份子,而是他的这一套观点究竟从何而来?这套观点是否禁得起考验与检视?西德、或者是今日的德国艺术,是否真的如史贝柏格所述,不堪入目及入耳?
因此,我们试图藉着分析同样身为德国导演的杜能斯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的《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及《无主之作》(Werk Ohne Autor),来探讨史贝柏格所说的。

《窃听风暴》剧照/IMDb
《窃听风暴》讲述了 1984 年在东德(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DR)国家安全局(die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Stasi)工作的威斯勒(Gerd Wiesler)奉命监视剧作家吉奥(Georg Dreyman)的生活,以确认其存在不能够威胁政府当局。至於《无主之作》,则是截取了一位东德艺术家库尔特(Kurt Barnert)二战前到六〇年代、历时三十年的生命片段。
我们可以分别在两部电影中找到许多值得称颂的人性价值与光辉,如前者的威斯勒、在得知吉奥试图将一篇关於自杀的敏感文章送到西德後,并没有禀报当局,而帮助隐瞒、在监听纪录上造假;或是属於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吉奥在社会主义德国的夹缝中生存。也有如後者的库尔特透过一个个生命事件,进行自我、艺术与存在意义的叩问和追寻。然而,在赞扬这些人物在黑暗的时刻、仍能保有其人性价值的不易时,我们必定无法避免讨论他们在电影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二、艺术的纯真性
首先,吉奥在威斯勒的暗中帮助下,成功地将文章送到了西德并且在《明镜》(Der Spiegel)刊登出来,且在後续上层的调查下躲过了追捕、幸运地活到了 1989 年围墙倒塌,见证了德国的统一。在一次公开的演出上,吉奥遇见了曾经担任文化部长的汉普夫(Minister Bruno Hempf)、问道:「为何我从来没有被监视过?」汉普夫听完笑出声来,「你处处都在被监视。我们知道你的一切。」事後吉奥来到档案室翻阅了资料,才发现自己一直被监视着,且有人似乎在他的资料上动了手脚。

《无主之作》剧照/车库娱乐
再者,库尔特在女友艾莉(Ellie Seeband)的父亲齐班德(Professor Seeband)的百般阻挠下,虽与女友成婚,但是这段婚姻并不受祝福。在得知艾莉怀有身孕後,齐班德告诉库尔特、以艾莉的体质进行受孕,将冒有极大的风险,建议在初期即将胎儿取出,然实则齐班德以延续优良血统的缘由、阻止艾莉受孕,而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对医学一知半解的库尔特,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艾莉接受了堕胎手术。此後,两人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让艾莉重新受孕。
分别就电影中的此两部分来看,艺术家被塑造成一种「天真、不问世事」的形象:吉奥对於威斯勒的帮助完全不知情,并且在此帮助下得以创作不辍,保有他的言论自由直到两德统一。而库尔特对於艾莉所承受的不孕之苦、齐班德的介入也丝毫不知;更甚者,自己深爱的姨妈伊莉莎白(Elisabeth May)最终因齐班德将其分类为「劣等的人类」而送进了毒气室,库尔特同样始终不知。
这样的牺牲与奉献,从威斯勒违抗上级的命令、齐班德对女儿的控制与施加於上的父权观念、乃至於姨妈的死亡,似乎都是为了成全艺术家们的创作。两位艺术家虽然同样在时代的变迁及历史背景下被迫经历了各自的地狱、失去爱人的苦痛,但是在他们承受自己苦痛的同时,还有另一些人自愿地承担了他们的部分痛苦。这些自愿式的行为,是无偿的、被颂扬的、甚至义务性的,彷佛为了成全艺术家,只好放弃自己的某样东西。
艺术──我们这里所指的「艺术」,是指「电影中的艺术形式」、如吉奥的剧作与库尔特的绘画,而非现实生活及当代我们所讨论的艺术──在两部片中除了建立了天真的形象,也被赋予了伟大的特质。吉奥因时代有感而发,编写了自己的剧作、写下了代号 HGW XX/7 的威斯勒的故事《致好人的奏鸣曲》(Die Sonate vom Guten Menschen);库尔特追寻属於自我的真实,将姨妈的照片、妻子怀孕的时刻投射到画布上。我们看见了两位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歌颂这些人、歌颂自己所经历过的艰辛的时代,但是这些歌颂的基础都建立在那些为了艺术家而牺牲的人们上。

《无主之作》剧照/车库娱乐
三、为艺术牺牲
由此可见,「为艺术牺牲」的必要性成为两部电影中的一种意识型态,并且无法轻易地被我们察觉。死去的人们藉由成为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而被记录和流传下来,我们无形中被灌输了这样的牺牲、为艺术的牺牲是光荣而且值得尊敬的事情,这无异於体现出一种基督教式的无条件奉献精神。从此一层面看来,他们为艺术牺牲自我,然而就另一层面而言,此一意识型态也包含了「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牺牲」的光荣与宿命性──所谓的「自己的国家」,并非人物本人所认同的国家或民族,而是西方所认定的「正统」,也就是代表自由与民主的西德、西方世界──因此威斯勒反抗了东德的命令、帮助自由派的知识份子,库尔特和艾莉逃离的东德、最後在西德完成了艺术的自我实践,都是必要的牺牲。
除此之外,若仔细探究两部电影中的女性,我们能发现艺术家生命中的重要女性,是苦难、而且没有自由意志的。吉奥的女友(Christa-Maria Sieland)因为被文化部长所爱慕,因此时常受到肢体上的骚扰、被强暴时无从抵抗,最後更因被迫出卖吉奥而懊悔自杀。库尔特的姨妈因「青年狂热症」(Schizophrenie)而被清洗,或是前述提及被父亲掌控的、库尔特的女友艾莉。这些女性自始至终都服膺於「大他者」(big Other),不论是父权的律法、或是整个社会的权力体系(Jacques Lacan)。最後艾莉虽然得以幸存,但是她与库尔特对於生育的尝试、以及成为库尔特的缪思,也使得她的存在沦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生产工具。
让我们再回来看「为艺术牺牲」的必要性。艺术除了是天真、纯洁的,它也是跟政治毫无相关的。仅管在两部电影中、政治因素都试图对艺术家施加影响力,但是透过他人的牺牲或是艺术家本人的被动拒绝,政治的因素几乎被排除在外。不论是纳粹时期的「政治艺术化」,或是东德共产政权的「艺术政治化」、艺术为政治服务(Walter Benjamin 1935: 102),政治都没能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艺术最终在精神的浩劫中胜出了。它没能记录下时代的晦暗不明,而仅留存了人性的美好价值,对其他的丑恶事物视而不见。
▍窃听风:暴数位修复版 The Lives of Others
前往诚品电影院观赏
▍关注#迷电影,一起重温经典好片
重看5部「超经典电影」,与老电影重逢,回想那年,现在我已经完全不同。
再现大时代恋曲,传奇作家三毛编剧代表作──滚滚红尘
早安!周日经典电影院:新天堂乐园 /数位修复系列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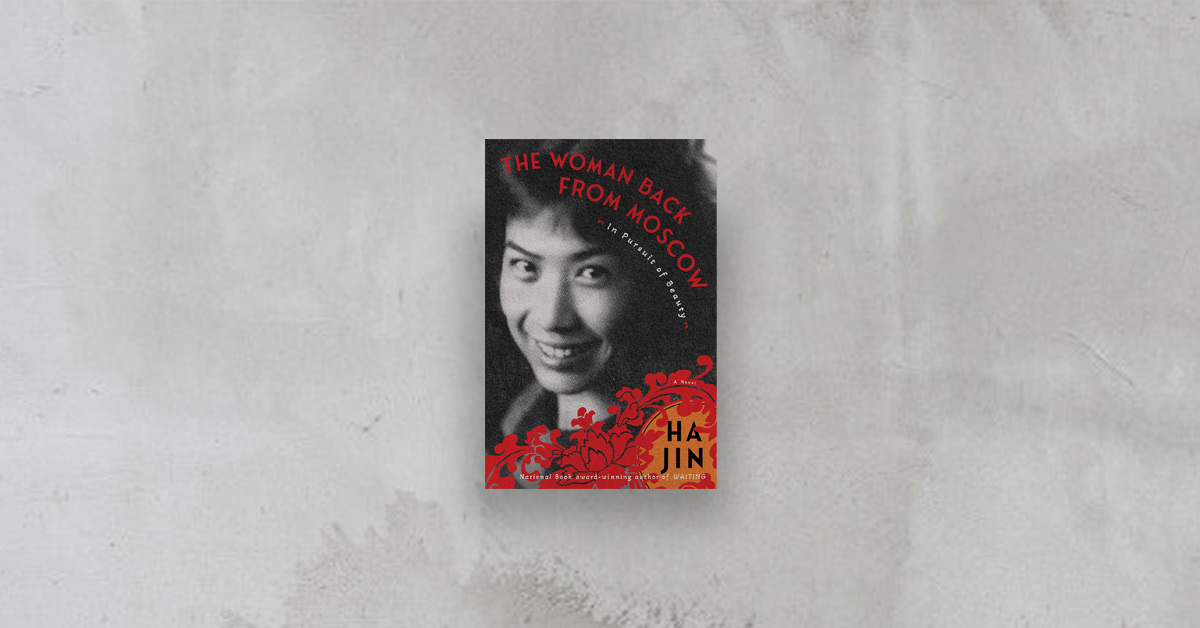

_2025042814263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