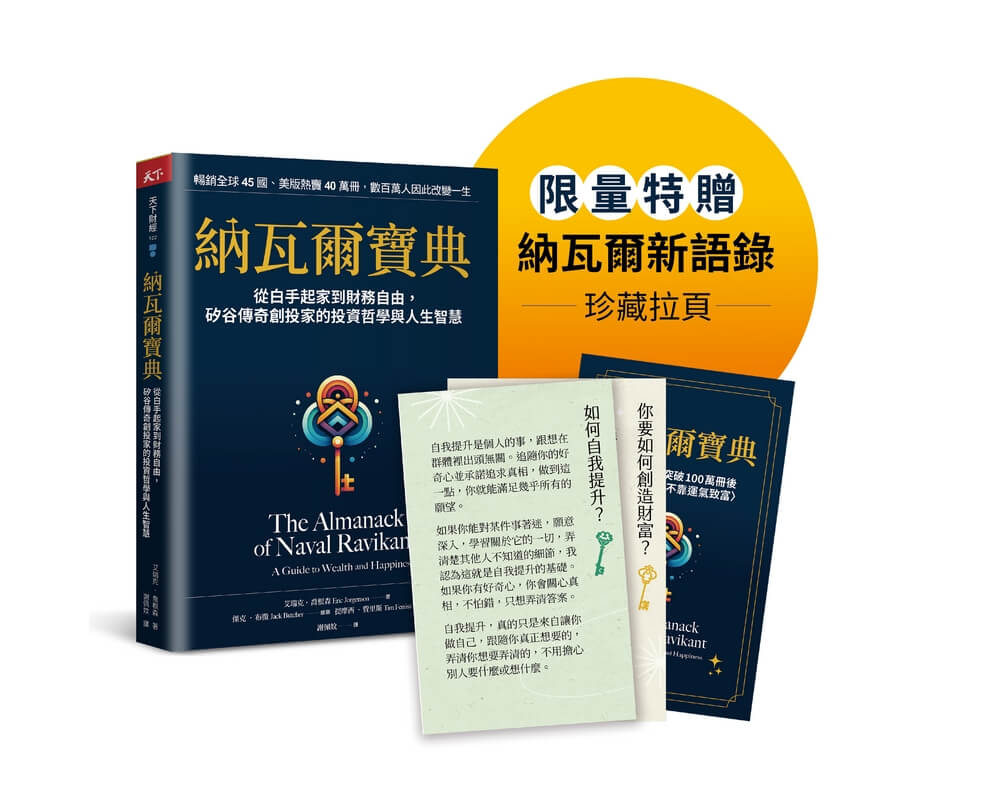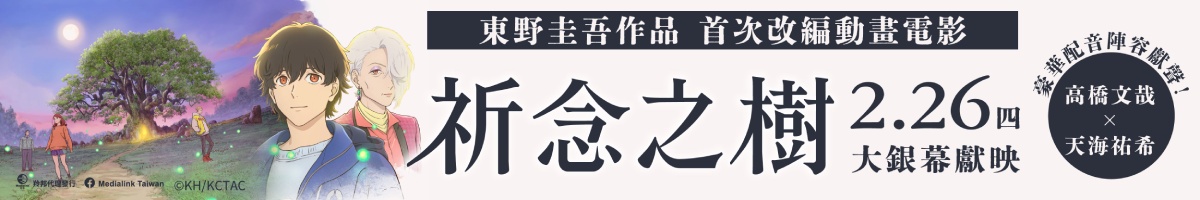吴俞萱 身体不说话──《提案》11月号「完美身体求生记」
撰文 吳俞萱作家的身体观察,是显微镜下的细胞运动,细微的爆炸、宇宙的收缩。
下一秒,他们一样脆弱、再长出新的,每个人无异。
身体不说话,她把我关掉。
融雪的初春来到纽约哈德逊河畔的Dia Beacon当代美术馆,她走近张牙舞爪的铁片雕塑,内凹她的身体,慢慢绕着雕塑尖锐突起的身体。很久没再哼起Anohni还叫Antony的时候唱的Hope There's Someone,不再受困於light and nowhere也就没有了愿。她与我的最大差异,就是她靠近世界没有忧惧也没有希望。
从前,我覆盖一切的时候,她就变成工具──坐在那里七个小时不动像一颗石头,手指一分钟敲出一百三十三个字。在咆啸入耳的时候打开隐形的金属护壳,穿过风暴中的雷电。躺在手术台,双脚打开,任由鸭嘴撑开阴道,小棒子刷落子宫颈表皮细胞,脸上不露出一点表情。我用这世界对我的方式去对她。她的需要和想要我从不过问。
她就澈底哑了。
直到我从大野庆人的舞踏教室走出来,暗夜穿过上星川的地下道,她忽然把我关掉,将自己连根拔起那样地跳舞。她不说话,她让我进入一种不再扮演什麽而是成为什麽的宇宙体。就像大野庆人教我成为婴儿、竹子、荷花、废墟、月亮……透过身体的变形,松脱意识的壳,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成为它们。
从纽约来到法国,我在初夏的古城驻村,遇见一座废弃的石头洗衣场,内部有个长长的水池,像塔可夫斯基《乡愁》里的诗人手持蜡烛穿越的水池。我常待在洗衣场,去感觉空间的温度和光线变化,触摸石墙和地砖,浸泡在冰冻的溪流中,想像以前的女人跪在这里洗衣服。
现在的我,要清洗什麽?洗得掉吗?
想在无用而溪水涌流的长池跳一支舞踏,回应妈妈。妈妈是我掌心捧着的蜡烛。塔可夫斯基说,他的每一部电影都透过某种形式,主张人类并非孑然孤立地被遗弃在空荡的天地里,而是藉着不计其数的线索和过去与未来紧密相连,每一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打造了他和全世界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之间的镣铐。
我要清洗的,是黏在我皮肤上的镣铐。
我调制了散沫花的粉末、柠檬、糖和浓茶,用它们来纹身,把写给妈妈的长诗抄写在肉身上,当成我的舞衣。我叫这一支舞,死生前来。
曾经我如此渴望离开妈妈,在她死後我才明白我渴望离开的是我对她的想像和制约。我想跳舞回应妈妈,而她不想。我在水池搓洗身上的泥巴,乾净了,还留有搓洗不掉的一整副皮囊。死生前来的,不是妈妈,而是透过妈妈来体验我的自我束缚。演出结束,有个观众问我这样或那样跳的时候在想些什麽?我说,没有思考,专心沉浸在当下,不记得上一秒发生了什麽,纯粹活着而已。
没说出口的是,她带我忘我,去到一个不用再脱壳、不用再费力成为什麽的狂喜状态。狂喜ecstasy的字源是「站出来」,不再受限於主客体的分裂关系,敏锐清澈地引发深层的知觉,我能直观地融合外象与自我,不分彼此地共享一座身体,充满力量地用我活成世界。
初秋,来到柏林。不说话的她频繁现身了。每当我专注投入文字一阵子,我就关掉自己,倾听她,放掉叙事的意图、放掉自我命名和意义化,仅仅全神贯注地敞开感官,让她不再担负思想的意涵,纯粹游戏和流动。我是奔跑的她,我是摺衣服的她,我是在厨房水槽清洗瓜果和碗筷的她。
谢谢身体不说话,带我懂得了鲁米的诗──
注意看那些
在窗户光线里移动的尘屑
它们的舞蹈就是我们的舞蹈
-

吴俞萱
诗人。在日本学舞踏,在土耳其学苏菲旋转。目前就读美国印地安艺术学院创意写作研究所。
文章首图插画/Phoebe chen
关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阅读与风格采买的书店志,纸本刊物每月1日准时於全台诚品书店免费发刊。每期封面故事讨论一个读者关心的生活与消费的议题,推荐给读者从中外文书籍、杂志、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线上阅读《提案on the desk》
《诚品书店eslite bookstore》粉丝专页
Current Issue 完美身体求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