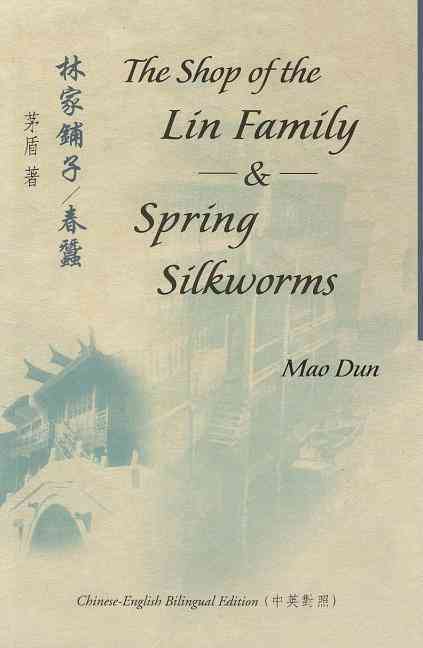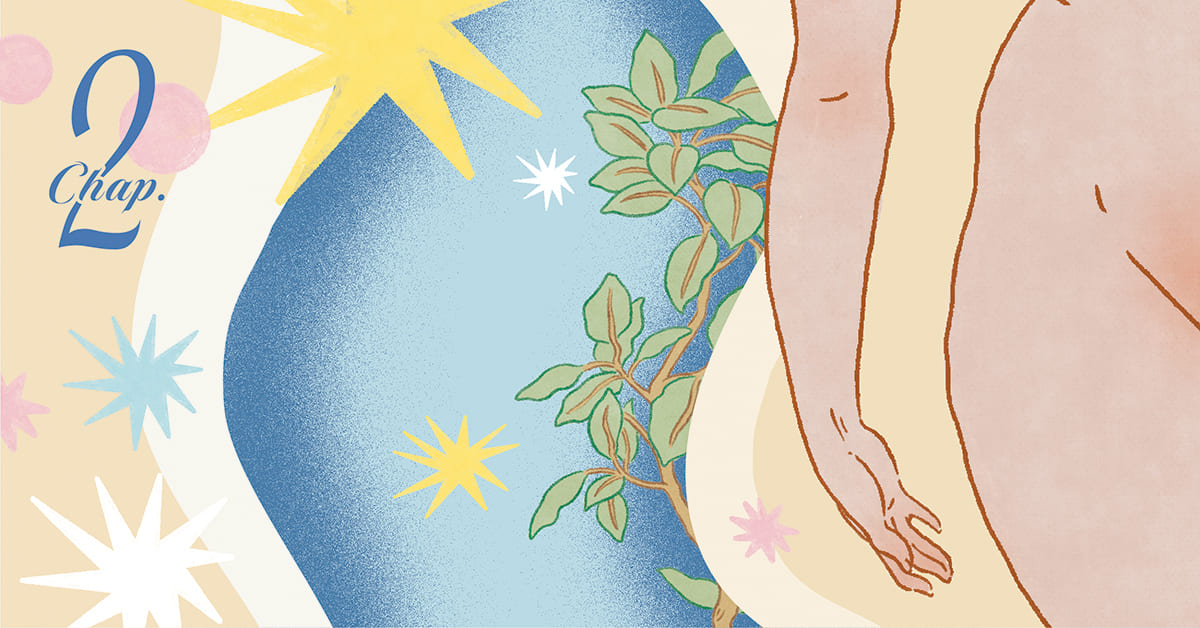
何曼庄 第二次尾椎复原记──《提案》11月号「完美身体求生记」
撰文 何曼莊作家的身体观察,是显微镜下的细胞运动,细微的爆炸、宇宙的收缩。
下一秒,他们一样脆弱、再长出新的,每个人无异。
接到约稿时,我的身体就只是在求生而已,「完美」个屁(名副其实),我想。
不久之前,去照X光,医生低头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我问:「玩什麽摔倒了?」
我也想像海明威那样,在时尚杂志上(Esquire)钜细靡遗地描述自己(第二次)用猎枪射到自己大腿的事情,但我只是(第二次)滑冰/轮摔伤尾椎而已,还是在练习场上很得意地快速倒滑时,没看到地上异物狠摔的。
那之後的三周之间,我都像海象一样左右对称地用手撑着身体移动,打喷嚏的时候特别痛,不过幸好骨头没事。我的同辈中年朋友们听闻,各自都有尾椎经验谈,有的是生产後骨盆像散架了一样,坐了donut seat(顾名思义,中间有一个洞的那种坐垫)六个月、有的是尾椎裂了但是打不了石膏只能等他自己好、还有一位让我看到了他脊椎断裂时期拍的X光片。
但我还是拿出专业素养来请教编辑:「完美身体求生记」到底什麽意思。
编辑认真的回覆中,有这样的一句:「完美是默默植入的时代审美」。
对「完美身体」的追求,不是一个生理议题,是百分之百的心理问题。比完美这个词更暴力的,是预设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追求完美,然而「完美」甚至不是一种追得到的东西,只是一种资本的、虚幻的、会吃人的概念。
我想到美籍亚裔喜剧演员Jimmy O-Yang在节目里说:亚裔父母随时都能马上说出你这张脸有哪里不对劲,台下观众爆笑得有点悲伤。我小时候感受过这种文化压力,任何路人都肩负着让我更接近完美的社会责任,时不时有大人劈头问我:「你什麽都好就是皮肤黑」、「你怎麽可以长痘痘(一颗)」、「你太瘦了不好看」,云云。然而,多年之後,我发现就算没晒黑、不长痘、长胖了,我这副身体,似乎还有几百个其他问题可以批评,不过我已经长成一个坚强的大人了,对这种「关怀」已经免疫了。
从坚强大人的角度,我观察到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承受了多少压力,刚见面他们就会这样对我说:「你应该去做model」、「你怎麽保养」、「你为什麽不当网红」。受到年轻人喜欢的我当然可喜可贺,但比起敷衍地说啊哪有啊谢谢,我总是尽可能诚恳地回答:就算长得比较好看,也可以不去当model或网红,老实说靠脸赚钱非常辛苦,再其实,没有什麽钱是好赚的。
不过,告诉年轻人一个好消息,单纯努力生活也可以过得幸福,在求生跟完美之间,有无数个选项,一定有一个或两个适合你,Surprise。
努力生活的我,终於尾椎不痛了,纽约大淹水後两天,一个微风徐徐的晴天,我的好友先我几个月过了四十五岁生日,我们就像平时一样约在布鲁克林大桥下,吃披萨、喝啤酒、互相报告自己身上又有哪里哪里痛,看手机时同时脱下眼镜(向年轻朋友解释一下,这是老花眼)。
「我回家还得写那篇什麽完美身体的东西。」
「这世上哪有什麽是完美的啊。」她说。
我们走在刚入夜的东河畔往地铁站移动,随意地挑了一张看得见曼哈顿天际线的长椅坐下。
就在那一刻,正面的那艘船突然放起了豪华的烟火,不是一、两朵金花,而是各形各色国庆等级的烟火,足足放了二十五分钟,照亮了曼哈顿下城每一栋摩天楼的脸。
「看来完美的东西还是有的,」我跟她说,「比如说Timing。」

-

何曼庄
台北人,着有《大动物园》、《有时跳舞 New York》等书,现居美国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