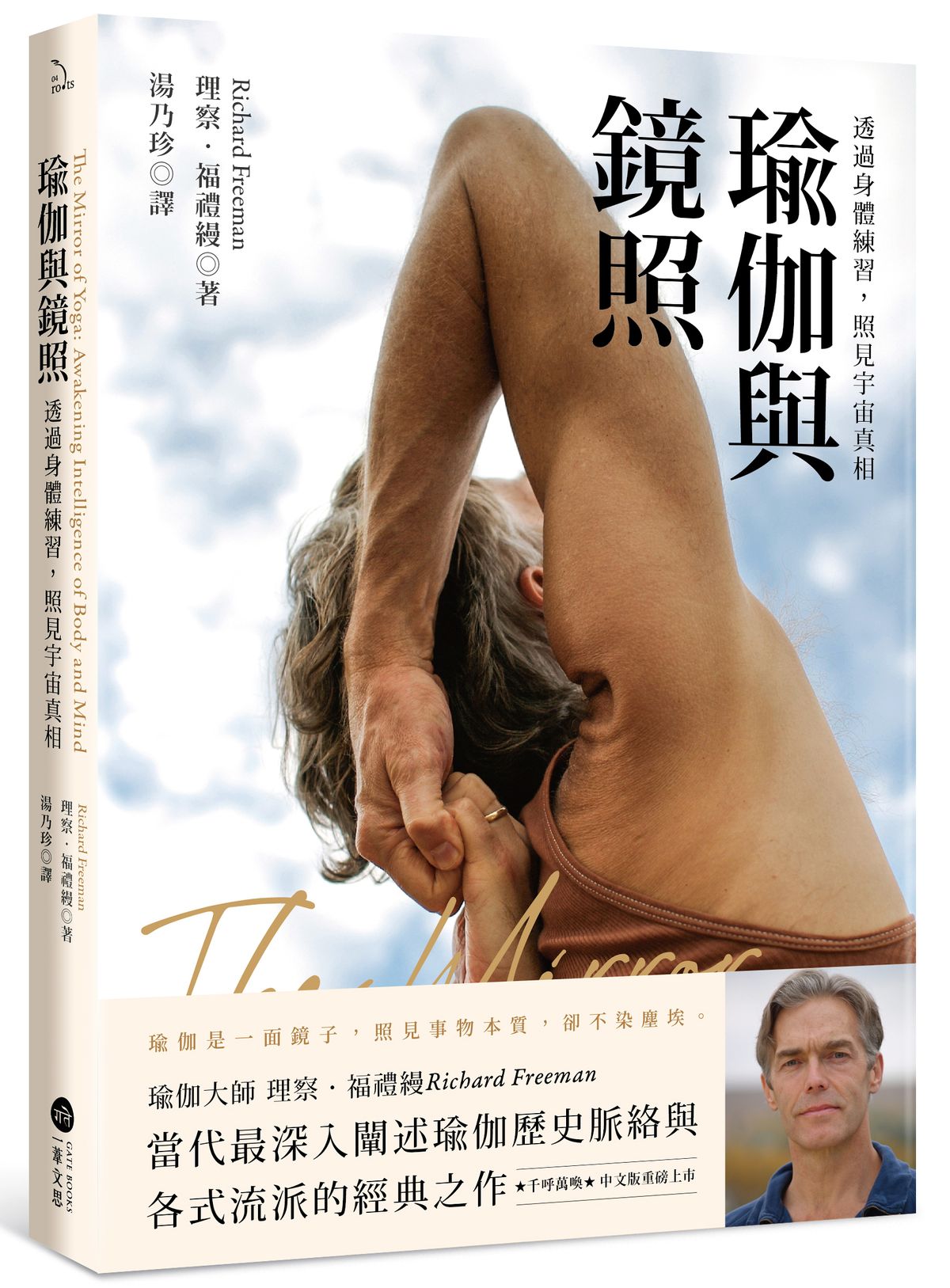吳俞萱 身體不說話──《提案》11月號「完美身體求生記」
撰文 吳俞萱作家的身體觀察,是顯微鏡下的細胞運動,細微的爆炸、宇宙的收縮。
下一秒,他們一樣脆弱、再長出新的,每個人無異。
身體不說話,她把我關掉。
融雪的初春來到紐約哈德遜河畔的Dia Beacon當代美術館,她走近張牙舞爪的鐵片雕塑,內凹她的身體,慢慢繞著雕塑尖銳突起的身體。很久沒再哼起Anohni還叫Antony的時候唱的Hope There's Someone,不再受困於light and nowhere也就沒有了願。她與我的最大差異,就是她靠近世界沒有憂懼也沒有希望。
從前,我覆蓋一切的時候,她就變成工具──坐在那裡七個小時不動像一顆石頭,手指一分鐘敲出一百三十三個字。在咆嘯入耳的時候打開隱形的金屬護殼,穿過風暴中的雷電。躺在手術檯,雙腳打開,任由鴨嘴撐開陰道,小棒子刷落子宮頸表皮細胞,臉上不露出一點表情。我用這世界對我的方式去對她。她的需要和想要我從不過問。
她就澈底啞了。
直到我從大野慶人的舞踏教室走出來,暗夜穿過上星川的地下道,她忽然把我關掉,將自己連根拔起那樣地跳舞。她不說話,她讓我進入一種不再扮演什麼而是成為什麼的宇宙體。就像大野慶人教我成為嬰兒、竹子、荷花、廢墟、月亮……透過身體的變形,鬆脫意識的殼,照著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成為它們。
從紐約來到法國,我在初夏的古城駐村,遇見一座廢棄的石頭洗衣場,內部有個長長的水池,像塔可夫斯基《鄉愁》裡的詩人手持蠟燭穿越的水池。我常待在洗衣場,去感覺空間的溫度和光線變化,觸摸石牆和地磚,浸泡在冰凍的溪流中,想像以前的女人跪在這裡洗衣服。
現在的我,要清洗什麼?洗得掉嗎?
想在無用而溪水湧流的長池跳一支舞踏,回應媽媽。媽媽是我掌心捧著的蠟燭。塔可夫斯基說,他的每一部電影都透過某種形式,主張人類並非孑然孤立地被遺棄在空蕩的天地裡,而是藉著不計其數的線索和過去與未來緊密相連,每一個人過著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打造了他和全世界甚至整個人類歷史之間的鐐銬。
我要清洗的,是黏在我皮膚上的鐐銬。
我調製了散沫花的粉末、檸檬、糖和濃茶,用它們來紋身,把寫給媽媽的長詩抄寫在肉身上,當成我的舞衣。我叫這一支舞,死生前來。
曾經我如此渴望離開媽媽,在她死後我才明白我渴望離開的是我對她的想像和制約。我想跳舞回應媽媽,而她不想。我在水池搓洗身上的泥巴,乾淨了,還留有搓洗不掉的一整副皮囊。死生前來的,不是媽媽,而是透過媽媽來體驗我的自我束縛。演出結束,有個觀眾問我這樣或那樣跳的時候在想些什麼?我說,沒有思考,專心沉浸在當下,不記得上一秒發生了什麼,純粹活著而已。
沒說出口的是,她帶我忘我,去到一個不用再脫殼、不用再費力成為什麼的狂喜狀態。狂喜ecstasy的字源是「站出來」,不再受限於主客體的分裂關係,敏銳清澈地引發深層的知覺,我能直觀地融合外象與自我,不分彼此地共享一座身體,充滿力量地用我活成世界。
初秋,來到柏林。不說話的她頻繁現身了。每當我專注投入文字一陣子,我就關掉自己,傾聽她,放掉敘事的意圖、放掉自我命名和意義化,僅僅全神貫注地敞開感官,讓她不再擔負思想的意涵,純粹遊戲和流動。我是奔跑的她,我是摺衣服的她,我是在廚房水槽清洗瓜果和碗筷的她。
謝謝身體不說話,帶我懂得了魯米的詩──
注意看那些
在窗戶光線裡移動的塵屑
它們的舞蹈就是我們的舞蹈
-

吳俞萱
詩人。在日本學舞踏,在土耳其學蘇菲旋轉。目前就讀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
文章首圖插畫/Phoebe chen
關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閱讀與風格採買的書店誌,紙本刊物每月1日準時於全台誠品書店免費發刊。每期封面故事討論一個讀者關心的生活與消費的議題,推薦給讀者從中外文書籍、雜誌、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線上閱讀《提案on the desk》
☞《誠品書店eslite bookstore》粉絲專頁
Current Issue 完美身體求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