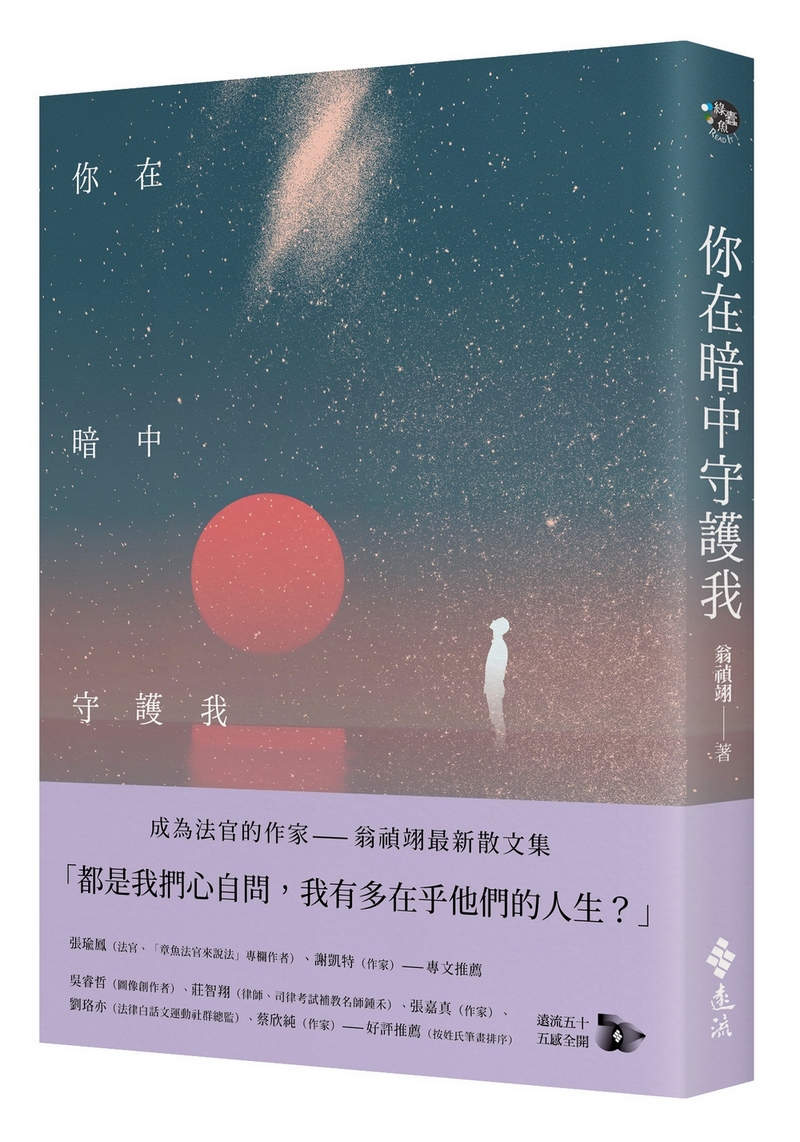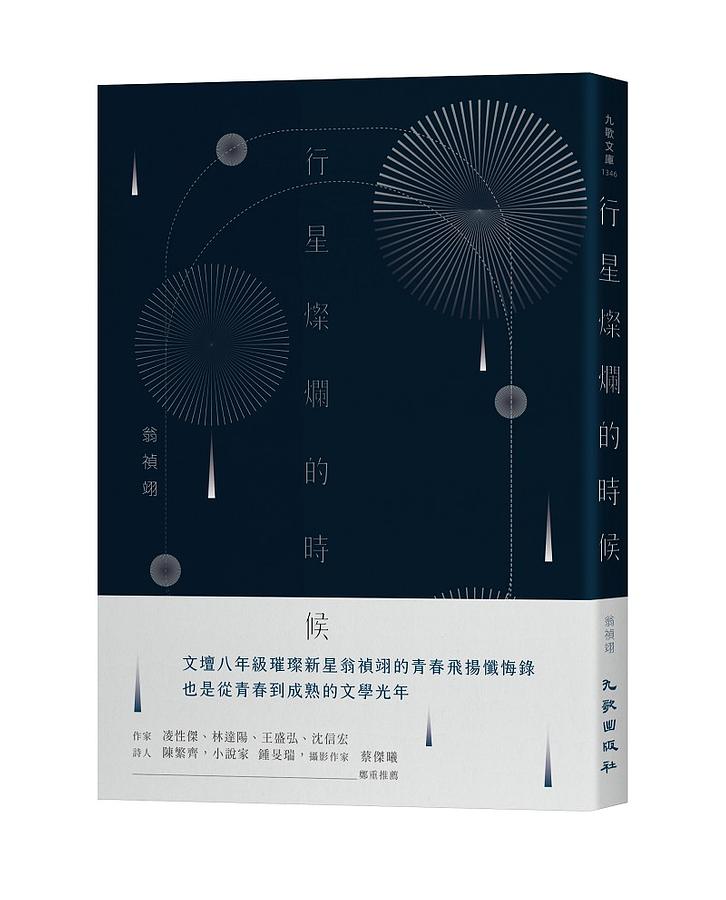「我不是最顶尖、最优秀的。」然而闪闪发亮的人生——专访作家翁祯翊
撰文 林于玄.攝影|KKlivehigh.場地協力|達文西咖啡不到 30 岁当上法官,台大法律系辅修日文系、台大法研所毕业,出版两本书,看似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人生胜利组」。然而谈起高中时,他却说:「建中很棒的地方,就是它让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不是最顶尖、最优秀的人。」
成为法官前,翁祯翊也曾想过念政大传院,学测分数却考得比历次模拟考还差,为了投稿文学奖不考指考而与父母激烈争执,最後选了台大政治系,念了一年再独自花三个月备考转到法律系。
——「如果成绩一直不起色怎麽办?」「我的兴趣和科系有未来吗?」「选错了还能回头吗?」与漫画、影剧里那些冷静睿智能言善辩的律师法官形象不同,翁祯翊书写的故事里,更多的是青春期的迷惘、怯懦、自卑,却也充满勇气、抉择和善良。
选系就像网购,我没办法跟高中生说「要勇敢追逐梦想」
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想选政大传播学院吗?我问翁祯翊。
「我现在完全不敢说服高中的我去念电影或传播学院。」他说。
「那就很像是网购,没有显示图片,没有使用者回馈,看着名称就要选下去,用个四、五年。我对那个科系不够了解,看到的甚至不及1%。现在快到30 岁这个年纪,我没办法回去跟高中生说『要勇敢追逐你的梦想』,因为有时那个想像跟那个科系毕业後实际在做的,距离其实很远。」
反而是当时离开的政治系,大一们同学间常开玩笑说「满水的」那些课程,在毕业後才发现「政治系要教你的,是建立自己的观点,精准、有条有理地讲给别人听。」翁祯翊说。
「很多政治系同学会开玩笑说,他们什麽都没有学到、不敢号称是政治系的,可是他们最大的能力就是,新接到一个专案,老板说这是前手做好的 PPT,给你20分钟,等一下客户来要跟他报告一小时。」
「这是很多法律系的同学,没办法想像或做到的。」
当老师说:「我知道自己不是来培养艺术家的。」
作为在全台求学竞争最激烈的台北市,考进第一志愿,穿上建中校服的学生之一,翁祯翊说自己曾经「自以为自己很厉害,是世界的中心」。
但在那之後,他讲了个让在场所有人屏气凝神的故事。
那学期,美术老师自掏腰包私下从国外支付高昂运费、起得很早到美术社抢货、拉下脸拜托老板,终於买来各种材料。「那时我们这些死小孩,就想说『我国中的时候也没有多听老师的话,还是可以考上。老师叫我不要丢黏土,那我就硬要丢、硬要弄水。』」毫不意外地,翁祯翊期末拿了62 分。
好死不死的,返校大扫除他被分配到了美术教室。美术老师找了他过去聊天,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为什麽成绩给你这麽低吗?」
後来,美术老师说了段让他铭记到今天的话。
「老师说,他从新竹女中跑来建中教书,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大部分不会去做艺术工作,可是一届1000人里面,可能会有5、600 个人成为有能力赞助艺术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在17、18 岁时,就感受到艺术很美好,甚至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你才会成为愿意主动花钱参与艺术活动的人,台湾的艺术环境才会有可能变得更好。」
「他知道自己不是来培养艺术家的,只是他想要让这些学生知道,艺术工作也是一份工作。『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大人时,希望你能看到别人,大部分的人看不到的付出。』」
翁祯翊说,「我就是在那个时间点,认知到我不应该当一个不可一世的人。」
一个月前,他终於重新得到老师的消息,老师分享了他写的〈恒星一样的大人〉。「他写了一句话——当年认识的小朋友,竟然也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我没有成为让老师失望的人。」
没考上律师,三十岁(还在)读研究所,也是让人敬佩的人生
律师国考的录取率约为 10 %,即使是录取率最高的台大法律系毕业生,每年也有约三分之一的人无法应届通过考试。甚至有不少法律系学生,在毕业後考了四、五年以上,仍然没有上岸。
「很多人考试压力很大,他们会想我的目标就是要考上,考不上就会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的话念法律系好像没什麽用......陷入无止境的循环跟挣扎。」翁祯翊坦言,自己很幸运早早做到目标。
真正让他佩服的,是他大学很要好的朋友。
「他大学毕业後从22 岁一直考,27 岁继续考......後来他就直接抛弃这段锁链,去香港做跟法律只有一点点关系的工作。」那後来呢?「他几次回台湾,我看到他就是开开心心的,对於自己的人生有新的掌握跟把握。」
「他才是真的克服了眼前困难,没有向任何人妥协而努力做自己的人。」翁祯翊说。
除此之外,还有他在台大「科际整合法律学研究所 」当助教时认识的人们。
「那时我22岁,他们都是比我大个5岁,甚至更多是30岁,工作5、6年,身兼着家庭、缴房贷、留职停薪的压力来念研究所,念个两三年,再花一两年准备国家考试。」
然而,翁祯翊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另一面——
「後来,他们很多人在法律这条路上,走得比大学生快乐或顺利。」
「因为那是决定承担这些风险,深思熟虑後做的决定。」
——也许会有那麽一刻,我们不再问自己「是不是最优秀的」、「是不是走错
了路」,我们会再次接受自己如青春期般的迷惘、怯懦、自卑,然後是勇气与抉择,
以及因此令人敬佩而闪闪发亮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