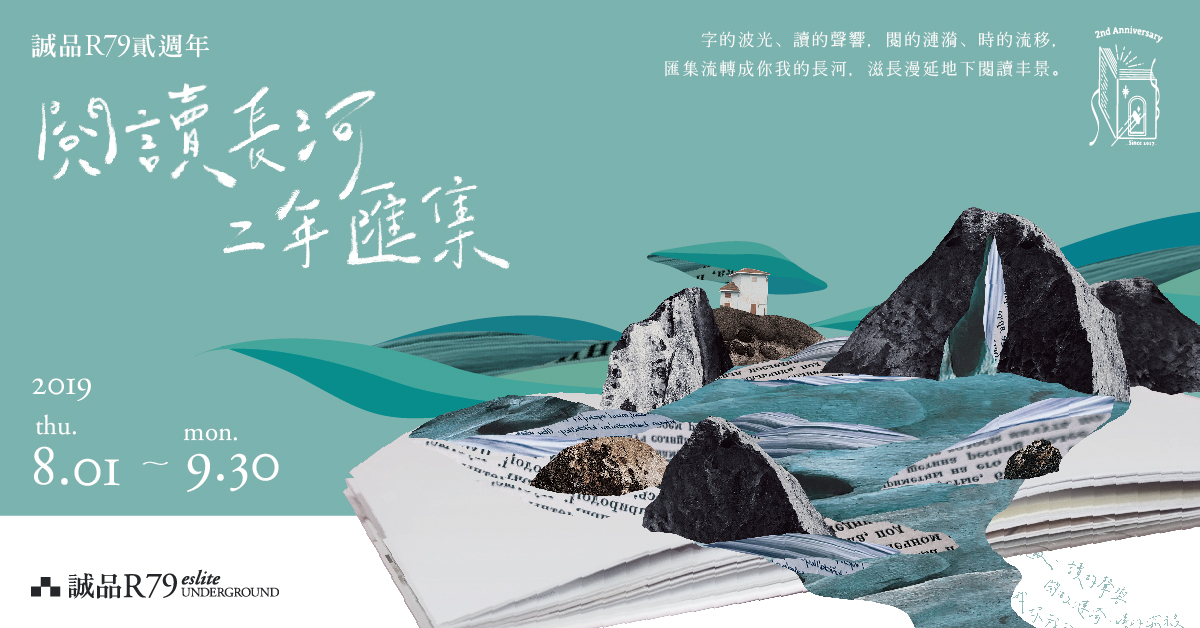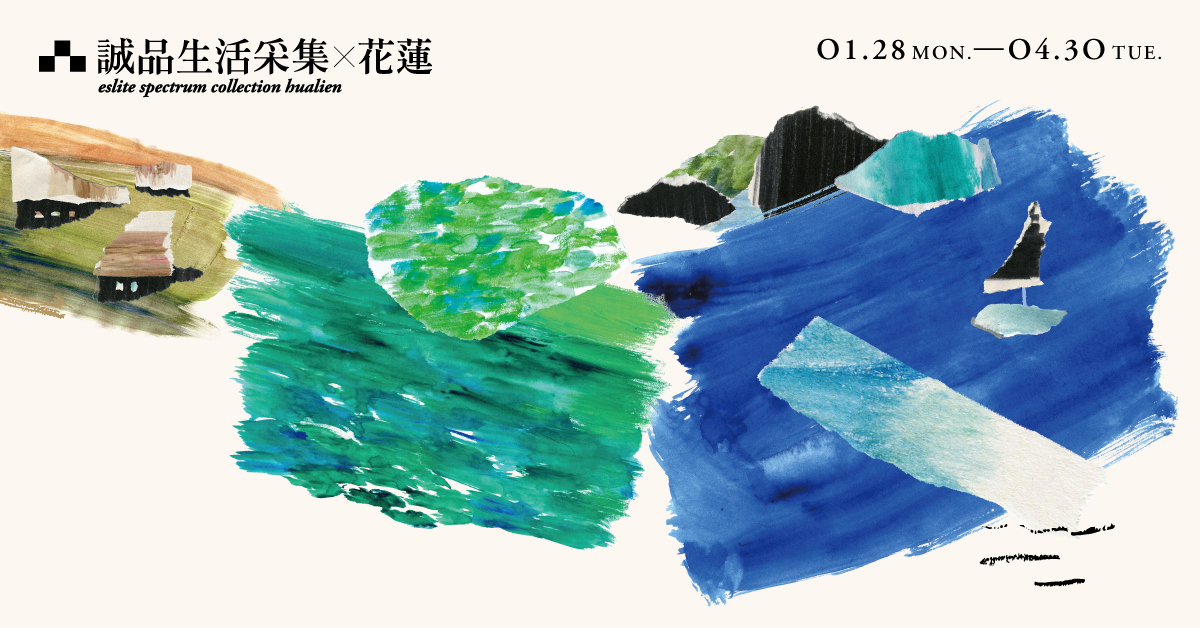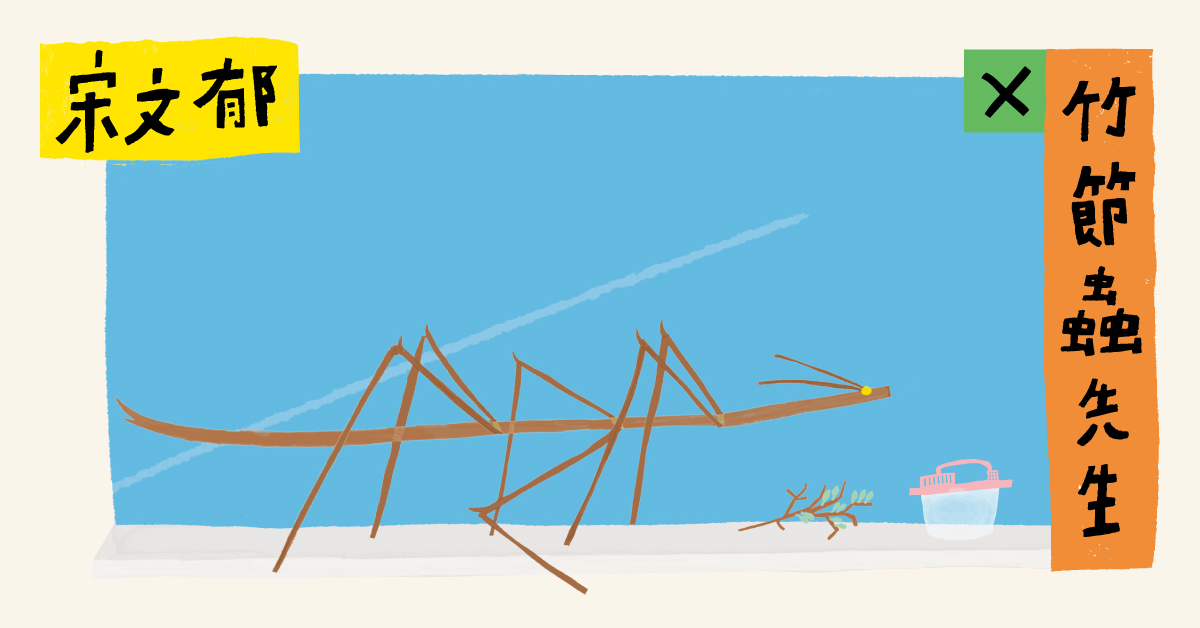只有喜欢是不够的, 聆听植物一如理解人心
撰文 鄒欣寧(文字工作者)
「用照料不会说话的植物的细腻心思,来揣摩对方的感受吧。」日本文化人松浦弥太郎在《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写下的清爽句子, 警钟一样撼动我。
那是一段为人际关系万分焦虑的时光。总是苦恼着对面那人究竟以何种心情与我来往,对我抱持怎样的态度,而我又该如何应对,如何平衡自己与人相处时貌似随性的粗神经和过分小心翼翼松浦提醒了我:一个人聆听、理解植物需求的能力,或许和他聆听、理解人心的能力成正比。
恍然大悟自己在这方面简直低能。回首我和植物的关系,在「栽种」这一章节里,基本上是由一连串的灾难伤亡构成。受难者形形色色,从潮流指标到公认难种死的全入了队:薄荷、薰衣草、迷迭香、黄金葛、仙人掌、石莲花、艾草、桂花、紫苏、常春藤、铁线蕨、兔脚蕨、波士顿蕨全都曾命丧我手至少一次。
到底怎麽成为植物连环杀手的?
我自己也百思不解。抱着一见锺情的兴奋感将它们从花市捧回家,也好好遵循老板的指示,室内景观植物和户外光照植物各安其位,每天早起就迫不及待往盆里浇水,无限爱怜的盼望它们蓬勃成长——为什麽这麽热切经营与植物关系的我,还是失败了?为什麽这麽努力想和喜爱的人们建立深厚关系的我,还是失败了?
原来,只有热切和喜欢是不够的,用一视同仁的态度应对,也是不够的。

植物不说话, 耐心倾听它们的需求
一位园艺老师听我说起身为「黑手指」的无奈和无力,微微一笑,「你在和植物相处前,有先做功课、对它们有基本理解吗?」他说,植物要的很简单,阳光、空气、水、土壤。虽然简单,每种植物需要的比例不一样,甚至即使同种植物,每一株的需求也有细微差异。
我想起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往需水量大的薄荷和耐旱的石莲花盆里倾倒一样多的水;把耐阴的山苏、白鹤芋、彩色网纹草放在来自热带的鸡蛋花旁边,一同接收从早到晚的强日曝晒;把根系在土里横向伸展的艾草塞在又小又窄的圆形花盆;任日日春野蛮生长到爆盆而不加修剪,再嫌弃它们徒长的侧枝丑陋杂乱。
植物不说话,却无时无刻表达它们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和它们晨昏相处的我,尽管依着某种常识和经验法则栽种浇灌,却不愿在惯习之外细腻观照它们各自的不同,用它们各自需要的方式温柔对待。於是我那每年春天显得繁茂光鲜的阳台植栽,犹如一场盛大举办的派对,在人群簇拥中享受社交女王的荣耀,可是每个人我都无法交心聆听、耐心相待,快则春末夏初,最晚不过秋冬交际,植物就会陆续凋零伤亡,留我懊悔又困惑:为什麽这段相处撑不过一个四季?
改变习性是漫长的试炼。逼自己慢下来,每天花更多时间在阳台晃荡,浇水不再行礼如仪乱浇一通,先用手轻触表土,确认乾燥程度才给水浇透。学着从叶片生长的色泽、趋向、饱和度判断要不要修剪、移盆、施肥,或是延续原本的对待方式。
与此同时,逐渐发现自己和人类往来,也从短时间的激越热切放慢脚步,学着不愠不火,偶尔抽身观照彼此在语言和行动之外的沉默,隐含着哪些讯息和感受。
树和人是不同的物种, 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
书架上挪出越来越多位置摆放植物和自然主题书。对於不具备理科脑的我来说,许多国外的植物学者从人类角度出发写成的植物科普书,无疑能引起更多共鸣,也降低阅读植物的门槛。德国树木学家彼得.渥雷本他用科学的语言写出树木和人类一样有记忆、会疼痛、能感知亲族关系,但也清楚点出了树和人是不同的物种,就算用类比、拟人的方式来拉近我们对树木植物的了解,并不表示人类中心、万物之灵的价值依然成立。
「动作缓慢的生物,就理所当然的要比行动敏捷的低等吗?有时候我不禁怀疑,如果说人们都同意说植物与动物间在许多方面其实很相似,那麽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与树木和其他蔬菜多一点尊重呢?」
——《树的秘密生命》
渥雷本提醒我,文学里惯用的拟人技法,某些时候只是一块入门砖,因为不可类比的差异才是我们相处中深切存在的真实。
「我不把植物拟人化,只是认定别的生物都在那里而已。」我锺爱的小说家吉本芭娜娜也透过书中角色这麽宣示。在她的四连作小说《王国》里,被大自然守护的女孩即使到城市生活,仍保有聆听和理解植物的能力,也把那样的能力转化成守护所爱之人的能量。我愿那是自己最终踏上的路径。
邹欣宁
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剧团经理、杂志采编、剧场编剧。闲时看书、看树、看舞。近期相关书作《种树的诗人》,为亲 自采访诗人吴晟编写而成。
关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阅读与风格采买的书店志,每个月1日准时於全台诚品书店免费发刊,全台发送量2万册。每期封面故事讨论一个读者关心的生活与消费的议题,并於全台书店展示议题的「延伸主题书展」,推荐给读者从中外文书籍、杂志、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新旧商品。除纸本刊物,另有线上版与《提案》粉丝专页,随时更新封面故事背後的最新动态!
线上阅读|http://issuu.com/onthedesk
粉丝专页|www.facebook.com/esliteonthede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