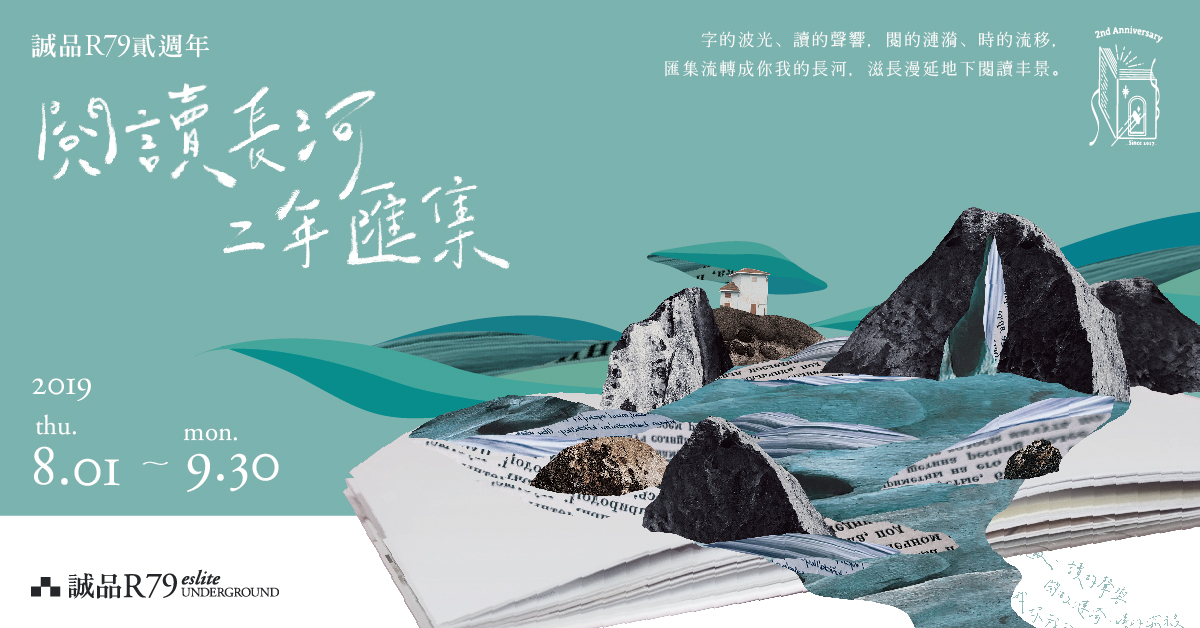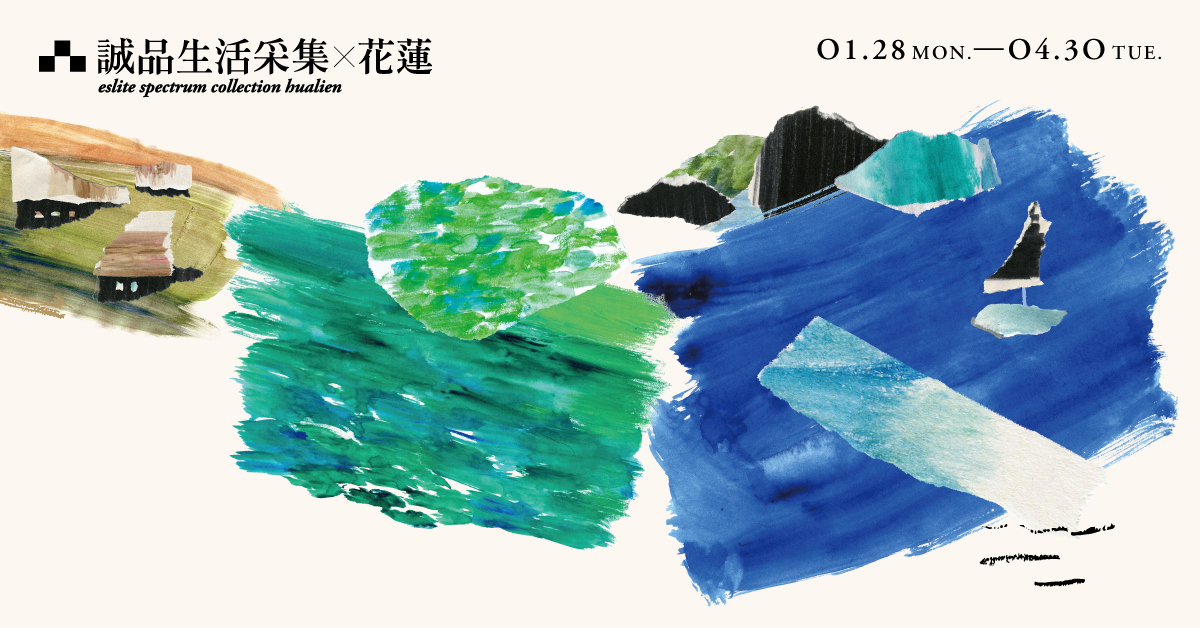只有喜歡是不夠的, 聆聽植物一如理解人心
撰文 鄒欣寧(文字工作者)
「用照料不會說話的植物的細膩心思,來揣摩對方的感受吧。」日本文化人松浦彌太郎在《今天也要用心過生活》寫下的清爽句子, 警鐘一樣撼動我。
那是一段為人際關係萬分焦慮的時光。總是苦惱著對面那人究竟以何種心情與我來往,對我抱持怎樣的態度,而我又該如何應對,如何平衡自己與人相處時貌似隨性的粗神經和過分小心翼翼⋯⋯松浦提醒了我:一個人聆聽、理解植物需求的能力,或許和他聆聽、理解人心的能力成正比。
恍然大悟自己在這方面簡直低能。回首我和植物的關係,在「栽種」這一章節裡,基本上是由一連串的災難傷亡構成。受難者形形色色,從潮流指標到公認難種死的全入了隊:薄荷、薰衣草、迷迭香、黃金葛、仙人掌、石蓮花、艾草、桂花、紫蘇、常春藤、鐵線蕨、兔腳蕨、波士頓蕨⋯⋯全都曾命喪我手至少一次。
到底怎麼成為植物連環殺手的?
我自己也百思不解。抱著一見鍾情的興奮感將它們從花市捧回家,也好好遵循老闆的指示,室內景觀植物和戶外光照植物各安其位,每天早起就迫不及待往盆裡澆水,無限愛憐的盼望它們蓬勃成長——為什麼這麼熱切經營與植物關係的我,還是失敗了?為什麼這麼努力想和喜愛的人們建立深厚關係的我,還是失敗了?
原來,只有熱切和喜歡是不夠的,用一視同仁的態度應對,也是不夠的。

植物不說話, 耐心傾聽它們的需求
一位園藝老師聽我說起身為「黑手指」的無奈和無力,微微一笑,「你在和植物相處前,有先做功課、對它們有基本理解嗎?」他說,植物要的很簡單,陽光、空氣、水、土壤。雖然簡單,每種植物需要的比例不一樣,甚至即使同種植物,每一株的需求也有細微差異。
我想起自己不分青紅皂白往需水量大的薄荷和耐旱的石蓮花盆裡傾倒一樣多的水;把耐陰的山蘇、白鶴芋、彩色網紋草放在來自熱帶的雞蛋花旁邊,一同接收從早到晚的強日曝曬;把根系在土裡橫向伸展的艾草塞在又小又窄的圓形花盆;任日日春野蠻生長到爆盆而不加修剪,再嫌棄它們徒長的側枝醜陋雜亂。
植物不說話,卻無時無刻表達它們對外來刺激的反應。和它們晨昏相處的我,儘管依著某種常識和經驗法則栽種澆灌,卻不願在慣習之外細膩觀照它們各自的不同,用它們各自需要的方式溫柔對待。於是我那每年春天顯得繁茂光鮮的陽台植栽,猶如一場盛大舉辦的派對,在人群簇擁中享受社交女王的榮耀,可是每個人我都無法交心聆聽、耐心相待,快則春末夏初,最晚不過秋冬交際,植物就會陸續凋零傷亡,留我懊悔又困惑:為什麼這段相處撐不過一個四季?
改變習性是漫長的試煉。逼自己慢下來,每天花更多時間在陽台晃盪,澆水不再行禮如儀亂澆一通,先用手輕觸表土,確認乾燥程度才給水澆透。學著從葉片生長的色澤、趨向、飽和度判斷要不要修剪、移盆、施肥,或是延續原本的對待方式。
與此同時,逐漸發現自己和人類往來,也從短時間的激越熱切放慢腳步,學著不慍不火,偶爾抽身觀照彼此在語言和行動之外的沉默,隱含著哪些訊息和感受。
樹和人是不同的物種, 理解並尊重彼此的差異
書架上挪出越來越多位置擺放植物和自然主題書。對於不具備理科腦的我來說,許多國外的植物學者從人類角度出發寫成的植物科普書,無疑能引起更多共鳴,也降低閱讀植物的門檻。德國樹木學家彼得.渥雷本他用科學的語言寫出樹木和人類一樣有記憶、會疼痛、能感知親族關係,但也清楚點出了樹和人是不同的物種,就算用類比、擬人的方式來拉近我們對樹木植物的了解,並不表示人類中心、萬物之靈的價值依然成立。
「動作緩慢的生物,就理所當然的要比行動敏捷的低等嗎?有時候我不禁懷疑,如果說人們都同意說植物與動物間在許多方面其實很相似,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給與樹木和其他蔬菜多一點尊重呢?」
——《樹的祕密生命》
渥雷本提醒我,文學裡慣用的擬人技法,某些時候只是一塊入門磚,因為不可類比的差異才是我們相處中深切存在的真實。
「我不把植物擬人化,只是認定別的生物都在那裡而已。」我鍾愛的小說家吉本芭娜娜也透過書中角色這麼宣示。在她的四連作小說《王國》裡,被大自然守護的女孩即使到城市生活,仍保有聆聽和理解植物的能力,也把那樣的能力轉化成守護所愛之人的能量。我願那是自己最終踏上的路徑。
鄒欣寧
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劇團經理、雜誌採編、劇場編劇。閒時看書、看樹、看舞。近期相關書作《種樹的詩人》,為親 自採訪詩人吳晟編寫而成。
關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閱讀與風格採買的書店誌,每個月1日準時於全台誠品書店免費發刊,全台發送量2萬冊。每期封面故事討論一個讀者關心的生活與消費的議題,並於全台書店展示議題的「延伸主題書展」,推薦給讀者從中外文書籍、雜誌、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新舊商品。除紙本刊物,另有線上版與《提案》粉絲專頁,隨時更新封面故事背後的最新動態!
線上閱讀|http://issuu.com/onthedesk
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esliteonthede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