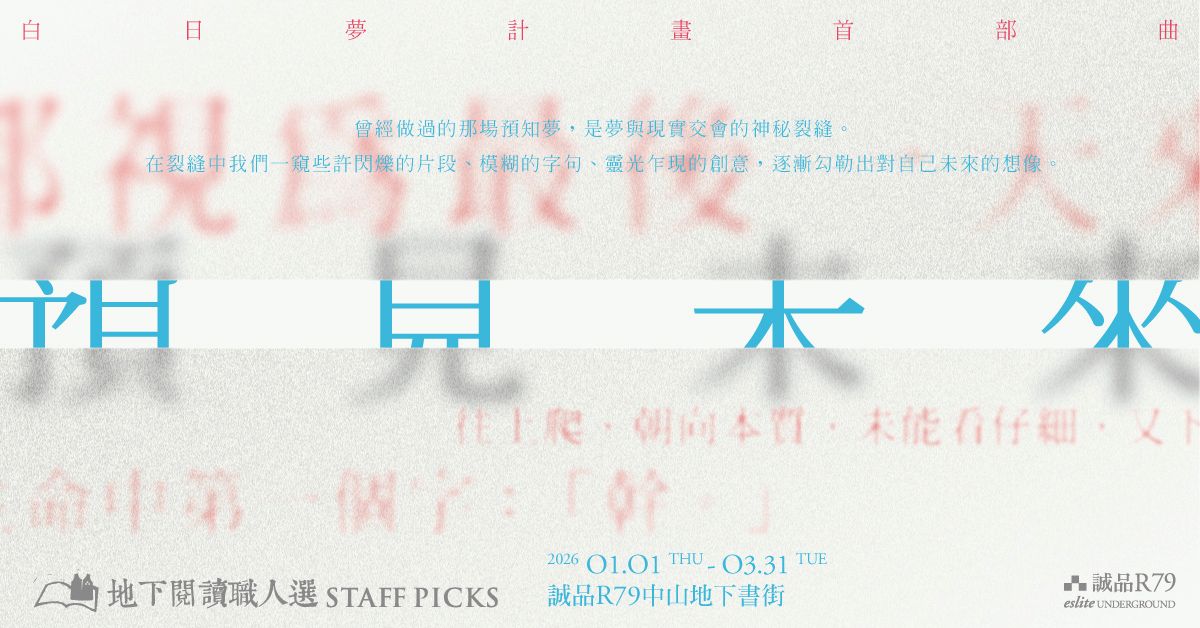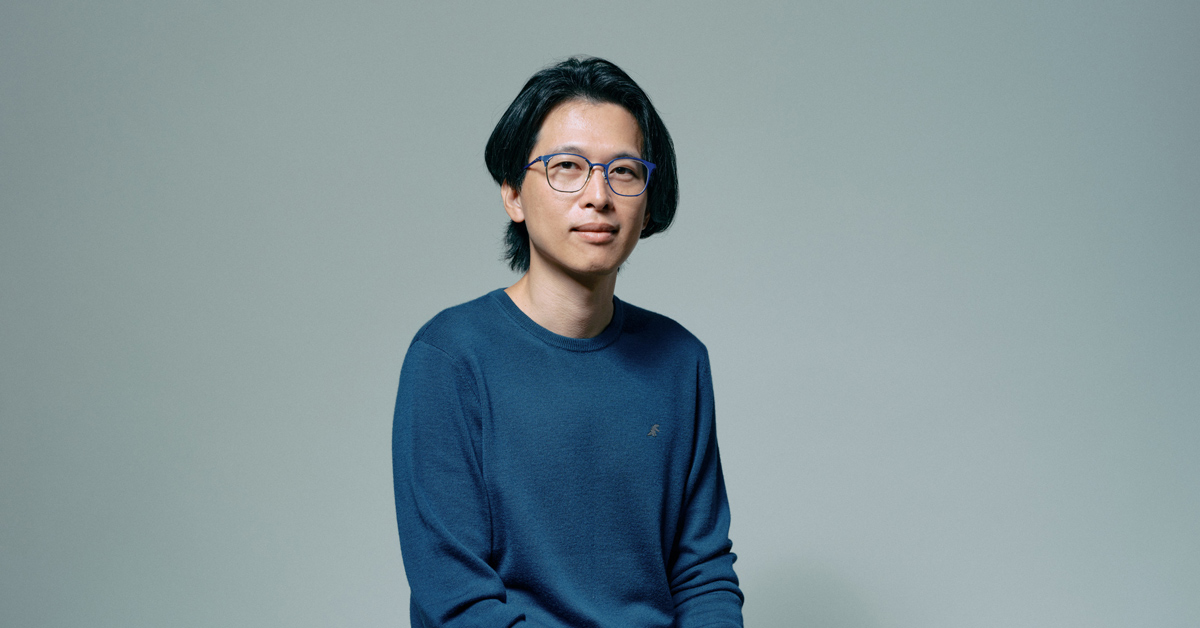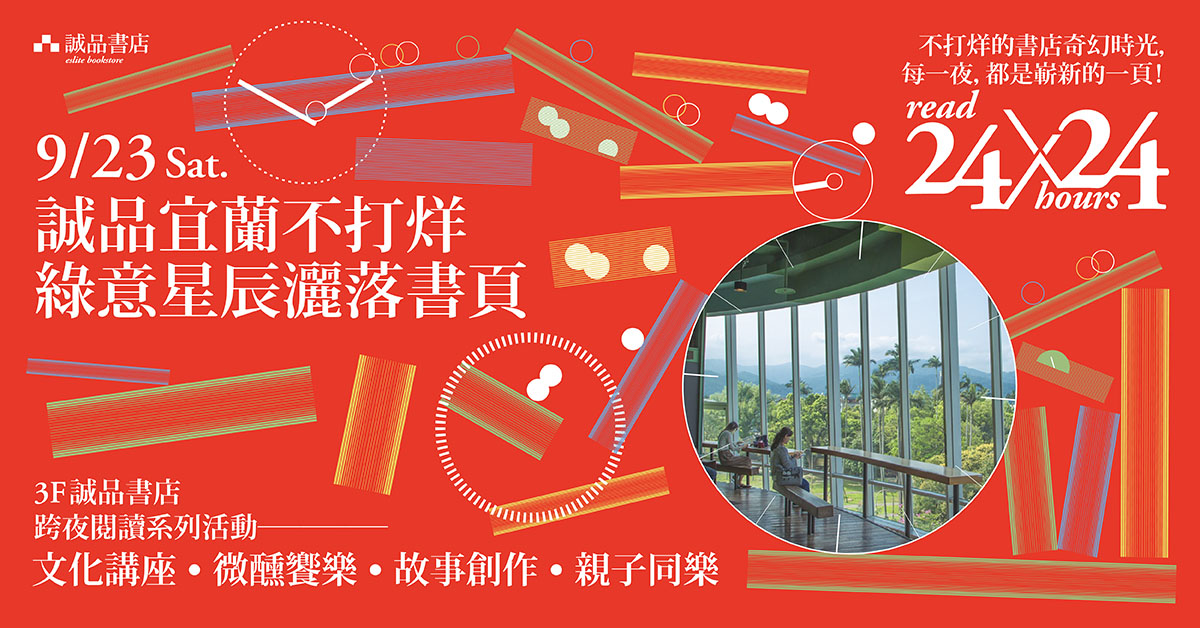随着韩国文化在台湾开花,接续影视与音乐,韩国文学也悄悄进入台湾人视角。近年来,许多韩国文学作家逐渐被读者阅读、认识,使韩国文学在台湾不再如过往冷门小众,作家韩江便是其中之一。
一九七○年出生於光州的韩江(),是亚洲首位获颁国际曼布克奖(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的作家,也是近代相当具有代表性的韩国作家,更多次名列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她的文字跨出韩国,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台湾文学圈也颇负盛名,拥有许多读者。
睽违五年,韩江在本书《永不告别》( )再度以「济州四三事件」国家暴力为主题,文中投射自我,虚实交错。即便描写炽热悲剧,充满哲思的文字始终冷冽、静谧,如带血的冰,却也因此让人看清血迹穿透扩散的痕迹。她笔下的角色常是柔弱的,像高墙旁微弱苍白的鸡蛋,但韩江总赋予这些人物坚不可摧的壳,并在黑暗中孕育良善与勇气。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漫游者文化,首图来源:The Korea Times}
▌不只遗留在过去的历史伤痛
历史看似遗留於过去,但事实上却深深牵动着我们彼此——
小说家庆荷受到摄影师好友仁善所托,帮忙前往济州岛照料她的小鸟,正因如此,庆荷意外发现仁善的家族史,看见济州四三事件带来的死亡与伤痛……
▊作者
韩江()
1970年生,韩国文坛新生代畅销女作家,是亚洲获得国际曼布克文学奖的第一人。
她毕业於延世大学国文系,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父亲也是小说家。
济州四三事件发生背景
 图片来源:《芝瑟:未尽的岁月2》_IMDb
图片来源:《芝瑟:未尽的岁月2》_IMDb
坐落南韩国境之南,现今被视作度假胜地的济州岛,曾经是独裁政治暴力下的禁地。相较一九八○年影响其後韩国民主化的光州事件,一九四○年代的济州四三事件对於台湾人而言可能较为陌生。起源於一九四七年的警民冲突误杀事件,济州民心激起反警情结,也为日後埋下未爆弹。一九四八年大韩民国(南韩)建立,隔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和彼端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对峙。
时任总统的李承晚颁布戒严令,以肃清共产份子为名对济州市民进行无差别血腥镇压。当时规定,凡在距离海岸线五公里外的山区被发现者,皆格杀勿论。如此焦土化的屠杀共持续超过七年,最终约有三万人死亡——该数字是当时济州人口的十分之一。
由一场警民冲突导火,失控引发至全岛屠杀,听来是否有些熟悉?济州四三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巧合般相像,那场发生在济州三月一日的误杀事件,即是同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後一天。同为孤悬在外的岛屿,台湾与济州岛在白色恐怖年代所经历的历史轨迹极其相似。
▌更多【漫游者文化】系列好书
女性视角揭露时代下的冲击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本书不只将读者带回那年济州岛之春,在阳刚挂帅的历史事件中,韩江用女性视角,为那些不被记录的女性刻画深度。《永不告别》以两位女性好友——庆荷与仁善为主角,从仁善一场突如其来的断指意外,连结至仁善母亲的家族伤痛,进而揭露一场屠杀,是如何重击那个年代下的人们。
韩江将巧思寄寓文字,充满各种解读可能,如「要医治断指,就须让缝合部位不能结痂,要继续出血」——呼应无法言说便难以治癒的政治创伤;抑或以「幻肢痛」隐喻失去至亲无法痊癒的伤痛;更用雪的意象象徵生死,如庆荷在济州经历的那场暴雪,宛如跨越生死边界,微妙镜射现实,种种抽象意念在文字中具体成形。
回望韩江历年着作,在探讨家庭中女性弱势角色的代表作《素食者》()後,韩江在《少年来了》( )以六位参与光州事件的平民,表面控诉独裁者的政治压迫与人性受创,实则探讨人性为何物。接着《白》()又如现代《道德经》般横空出世,在不同的「白」中思索生命本质。这些看来各异的主题,其实隐含相似内核,那便是韩江对生死的内省。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永不告别》则是一场跨过世代,穿越时间的对话。韩江有意识地选择叙事手法,不以当事人主观视角剖开过去,反而从政治暴力下一代的双眼间接切入,一一寻觅记忆碎片,循迹重构历史。一段家族回忆录,是政治悲剧的见证史,那些看似风和日丽的午後,远处竟下着暴雪;如今稳妥踩着的土地,数十年前曾是血染之处。
同以政治暴力事件为轴,若说多方陈述构建的《少年来了》是由各色颜料涂抹成画,《永不告别》则像小心翼翼拨开灰尘,找回画作已有些黯淡风化的当时面目。隔着距离,似带一层雾面,但不减暴戾,画面也渐渐鲜明。正如距今已遥远的济州四三,它提醒我们,有些历史不可遗忘,有些回忆必须永不告别。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希望这是一部关於极致之爱的小说」韩江在作者自述里这样说道。纵然叙说如何悲伤的过去,历史尚未翻页,烙痕仍旧渗血,但韩江的文字始终镶着残酷美感,如废墟里的花,在断壁残垣中兀自清丽。这是她给予读者的爱,阅读这些文字像一次次集体创伤治癒,坚定地告诉人们——不要别过头去。
因为当雪花落下时,我们或许能在一片颓唐中,找到那朵柔弱却坚韧的花。
《永不告别》节录——结晶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天空飘着稀疏的小雪。
我站立的原野尽头与低矮的山相连,从山脊到此处,栽种了数千棵黑色圆木。这些树木像是各个年龄层的人,高矮略有不同,粗细就像铁路枕木那样,但是不像枕木一样笔直,而是有些倾斜或弯曲,彷佛数千名男女和瘦弱的孩子蜷缩着肩膀淋着雪。
这里曾经存在过墓地吗?我想着。
这些树木都是墓碑吗?
雪花如盐的结晶,飘落在黑色树木每个断裂的树梢上,後方有着低斜的坟茔,我在其间行走。我之所以突然停下脚步,是因为从某一瞬间开始,我的运动鞋居然踩到滋滋作响的水,才觉得奇怪,水就涨到我的脚背上。我回头看了看,不敢相信。原以为是地平线的原野尽头竟然是大海,现在潮水正朝我涌来。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不自觉地发出声音问道:为什麽在这种地方建造坟墓?海水涌来的速度逐渐加快,每天都是如此潮起潮落吗?下方的坟墓是不是只剩下坟茔,骨头都被冲走了?
没有时间了,我只能放弃那些已经被水淹没的坟墓,但埋在上方的骨头一定得移走,在涌进更多海水之前,就是现在。但是怎麽办?没有其他人啊,我连铲子都没有。这麽多坟墓怎麽办?我不知如何是好,在黑色树木之间,我踏着不知不觉间已经涨到膝盖的水,开始跑起来。
眼睛一睁开,天还没亮。下着雪的原野、黑色树木、朝我涌来的海水都不存在,我望着黑暗房间的窗户,闭上眼睛。我意识到又做了关於那个城市的梦,然後用冰冷的手掌遮住双眼,躺下身来。
我开始做起那个梦,是在二○一四年的夏天,在我出版关於那个城市的居民曾经遭到屠杀的书将近两个月之後。在那之後的四年间,我从未怀疑这个梦的意义。去年夏天,我第一次想到,也许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城市而做起这样的梦,很快就凭直觉得出的那个结论,也许是我的误解,或者只是一种太过单纯的解释。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当时,热带夜现象持续了将近二十天,我总是躺在客厅故障的冷气机下睡觉。虽然已经洗过几次冷水澡,但汗湿的身体躺在地板上,我也未曾感到凉爽。直到凌晨五点左右,才感觉到气温有所下降,三十分钟後,太阳就会升起,这无疑是短暂的恩宠。
我当时觉得终於可以睡一会儿了,不,在几乎快睡着的时候,那片原野转眼间涌进我紧闭的双眼。飘散在数千棵黑色圆木上的雪花、在每株被切断的树梢上堆积如盐般的雪花,栩栩如生。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当时不知道为什麽身体会开始颤抖,虽然处於即将哭出来的那一瞬间,但眼泪之类的东西并没有流下来,也未曾凝结。这能称之为恐怖吗?那是不安、战栗、突然的痛苦吗?不,那是冰冷的觉醒,让人咬牙切齿。就像看不见的巨大刀刃—人力无法举起的沉重铁刃—悬空对准我的身体,我彷佛只能躺卧仰望着它。
当时,我第一次想到,为了卷走坟茔下方的骨头而涌来的那片蔚蓝大海,也许不一定是关於被屠杀的人和之後的时间。也许这只是关於我个人的预言,被海水淹没的坟墓和沉默的墓碑构成的那个地方,也许是提前告诉我,以後的生活会如何展开。
也就是现在。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从最初做那个梦的夜晚,到那个夏天清晨之间的四年间,我做了几场个人的告别。有些选择虽是出於我的意志,但有些则是未曾想过,即使是付出一切代价也想停下来的事情。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从最初做那个梦的夜晚,到那个夏天清晨之间的四年间,我做了几场个人的告别。有些选择虽是出於我的意志,但有些则是未曾想过,即使是付出一切代价也想停下来的事情。
如果像那些古老的信仰所说的,在天庭或阴间的某个地方,有巨大镜子之类的东西,察看人类的一举一动,并将其记录下来,那麽我过去的四年,就像从硬壳中掏出身体、在刀刃上前进的蜗牛一样。
想活下来的身体;被刺穿切割的身体;反覆被拥抱、甩开的身体;下跪的身体;哀求的身体;不停地流出不知是血、脓水还是眼泪的身体。
在所有的气力都用尽的暮春,我租下了首尔近郊的走道式公寓。再也没有必须照顾的家人和工作职场,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长久以来,在我工作维持生计的同时,还一直照顾家人。因为这两件事情是第一顺位,所以我减少睡眠时间写作,暗中希望未来能有尽情写作的时间,但那种渴望已经不复存在。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无心整理搬家公司随意置放的家具,直到七月来临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但几乎无法入睡。我没做菜,也没有走出大门,只是喝网购的水、吃少量米饭和白泡菜。
我一旦出现伴随胃痉挛症状的偏头痛,便会把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到马桶里。遗书在某个夜晚已经写好,在开头写着「请帮我做几件事情」的信里,虽然简略地写下哪个抽屉的盒子里有存摺、保险单和租房契约、剩下的多少钱用於何处、剩下的希望转达给哪些人等,但要委托的收件人名字却空着,因为我无法确定谁能够让我如此拜托。
我还补充了感谢和道歉的内容,说要给为我善後的人一些具体的谢礼,但最终还是没能写上收信人的名字。
我终於从一刻也无法入睡、但也无法爬起来的床上起身,正是出於对那个未知的收信人的责任感。虽然尚未决定在几位熟人中要拜托谁,但我想着需要整理好剩下的事情,於是开始收拾屋子。厨房里堆积如山的矿泉水空瓶、会变成麻烦的衣服和被子、我的日记和手册等纪录,我都得加以丢弃。我双手拿着第一捆垃圾,在时隔两个月之後,第一次穿上运动鞋、打开玄关门,彷佛是第一次看到的午後阳光,洒在西向的走道上。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乘坐电梯下楼,经过警卫室,穿越公寓的中庭,我感到自己正在目睹着什麽。那是人类生活的世界。当天的天气,空气中的湿度,以及重力的感觉。回家後,我没有把堆满客厅的东西绑成第二捆,而是进了浴室。我没有脱衣服,打开热水後坐在下方,用蜷缩的脚掌感受瓷砖的地面。逐渐让人窒息的水蒸气,湿透而黏在脊背的棉衬衫,顺着遮盖住眼睛的刘海一路流到下颚、胸前和腹部的热水,这些感觉让我记忆深刻。
我走出浴室,脱掉湿衣服,在尚未丢弃的衣服堆里找了件还能用的穿上。我把两张一万韩元的纸币摺了好多次後放进口袋,走出玄关。我走到附近地铁站後方的粥店,点了看起来最好消化的松子粥。在慢慢吃着烫得不得了的东西时,我看着从玻璃门外经过的所有人,肉体看起来都脆弱得快要碎掉,那时我确实感受到生命是多麽单薄的存在。那些肌肉、内脏、骨骼和生命,是多麽容易破碎和断裂,只要做出一次选择。
就这样,死亡放过了我。就像原以为会撞击到地球的小行星,因细微角度的误差避开一般。以不假思索、毫不迟疑的猛烈速度。
我虽然没有和人生和解,但终究还是要重新活下去。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意识到两个多月的隐居和饥饿,已经让我失去了不少肌肉。我因为偏头痛、胃痉挛而服用咖啡因含量过高的止痛剂,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我必须饮食规律并且活动身体。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意识到两个多月的隐居和饥饿,已经让我失去了不少肌肉。我因为偏头痛、胃痉挛而服用咖啡因含量过高的止痛剂,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我必须饮食规律并且活动身体。
但是在尚未正式努力之前,酷暑就开始了。当白天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人体的温度时,我曾试着开冷气,那是上个房客未及搬走的,但没有任何反应。好不容易才拨通冷气机修理业者的电话,对方表示由於气温异常,预约暴增,到八月下旬才能来修理。即使我想买一台新产品,情况也是一样。
不管是哪里,躲进有冷气的地方是最明智的抉择。但是我不想去人们聚集的咖啡厅、图书馆、银行等地方。我所能做的就只有躺在客厅地板上,尽可能降低体温;经常用冷水淋浴,以免毛孔堵塞而中暑;在街道热浪稍微冷却的晚上八点左右出门,喝了粥以後回家。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凉爽的粥店室内舒适得令人难以置信,由於室内外的温差和外面的湿度,像冬夜一样起雾的玻璃门外,拿着携带式电风扇回家的人络绎不绝,而我也马上要再次踏进这条似乎永远不会冷却的热带夜街道。
在某一个从粥店走回家的夜晚,我迎着从炙热的柏油车道刮来的热风,站在红绿灯前。我当时想,应该把信继续写下去,不,应该重新写过。用油性签字笔在信封上写下「遗书」二字,收信人始终没能确定的那封遗书,从头开始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如果想写,就得回忆。
不知从哪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开始破碎。
不知何时出现岔路。
不知哪个缝隙和节点才是临界点。
我们从经验当中知道,有些人离开时,会拿出自己最锋利的刀刃,砍削对方最柔软的部分,因为曾经靠得很近,所以才能知道要害。
我不想活得像个失败者,跟你一样。
为了想活下去才离开你。
因为想活得像活着一样。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二○一二年冬天,我为了写那本书而阅读资料,正是从那时开始做起噩梦。刚开始梦到的是直接的暴力。我为了躲避空降部队而逃跑时,肩膀被棍棒击打後跌倒在地,军人用脚猛踹我的肋下,我因此被踢得翻滚了几圈。现在我已经记不得那个军人的脸孔,只记得他双手握住上刺刀的枪,用力刺向我的胸部时,带给我的战栗。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二○一二年冬天,我为了写那本书而阅读资料,正是从那时开始做起噩梦。刚开始梦到的是直接的暴力。我为了躲避空降部队而逃跑时,肩膀被棍棒击打後跌倒在地,军人用脚猛踹我的肋下,我因此被踢得翻滚了几圈。现在我已经记不得那个军人的脸孔,只记得他双手握住上刺刀的枪,用力刺向我的胸部时,带给我的战栗。
为了不要给家人,尤其是女儿带来阴郁的影响,我在距离家里约十五分钟的地方租了一间工作室,原本打算只在工作室里写作,离开那里後,立刻回到日常的生活中。那是建於八○年代的红砖房二楼的一个房间,三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修缮过。
铁门满是刮痕,於是我买来白色水性油漆重新刷过,因太过老旧而出现裂缝的木头窗框则用图钉钉上围巾,以之代替窗帘。有课的时候,我在那里从早上九点待到中午,没有课的日子则直到下午五点为止,都在读资料、做笔记。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像往常一样,我早、晚都做饭和家人一起享用。我努力多和刚上初中、面临新环境的女儿聊天。但彷佛身体被分成两半一样,那本书的阴影隐约出现在我所有的生活当中。不只是打开瓦斯炉、等待锅里的水烧开的时候,甚至是将豆腐切片沾上蛋汁後放在平底锅上,等候两面都变得焦黄的短暂时间里。
前往工作室的道路位於河边,行走在茂密的树木之间,有一段向下倾斜後,突然豁然开朗的区间。在那段开放的道路上步行三百公尺左右,才能到达作为溜冰场使用的桥下空地。
我总觉得那段让我毫无防备、暴露我身体位置的道路太长。因为在单行道对面建筑的屋顶上,狙击手似乎正瞄准着人群。我当然知道这种不安非常不像话。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的睡眠品质越来越差,呼吸越来越短促。为什麽那样呼吸呢?孩子有一天向我抱怨—那是二○一三年的暮春。凌晨一点,我被噩梦惊醒,睡意全消,只得放弃再次入睡的念头。
我因为想买矿泉水而出门。街道上没有人车,我独自等待着毫无意义的红绿灯变成绿色。我望着公寓前车道对面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商店。突然回过神来时,我看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大约有三十名左右的男人正无声地排队行走。那些留着长发、身穿後备军人军服的男人,肩膀上背着步枪,以完全感受不到军纪的散漫姿势,就像跟随郊游队伍前行的疲惫孩子们一样缓慢走着。
如果长时间没能睡好觉、正处於分不清是噩梦或现实的人,碰到难以置信的场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自我怀疑。我真的看到了那个吗?这个瞬间是不是噩梦的一部分?我的感觉有多可靠?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们被寂静包围的背影,完全消失在黑暗的十字路口,彷佛有人按下静音按键。这不是梦境,我一点也不困,一滴酒都没喝。但在那一瞬间,我也无法相信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到他们也许是在後备军人训练场受训的人,就在牛眠山对面的内谷洞,此刻可能正在进行深夜行军。那麽他们应该越过漆黑的山,走十几公里的路程,直到凌晨一点。
我不知道後备军人是否有这种训练。第二天早上,原本想打电话询问身边服完兵役的人,但因为不希望我看起来像奇怪的人——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到现在为止,都没能向任何人开口。
我和一些不认识的女人一起拉着她们孩子的手,互相帮助,顺着水井内侧的墙壁爬下去。原以为下面会很安全,但突然有数十发子弹从井口倾泻而下。女人用力抱住孩子,藏在自己的怀里。原以为乾涸的井底,突然涌上如同融化橡胶一样的黏稠汁液,为了吞噬我们的血液和惨叫。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和记不清脸孔的一行人走在废弃的道路上。看到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时,有人说道,他坐在那里面。虽然没有说出名字,但大家都明白那句话的含义。当年春天下令进行屠杀的人就在那里。
就在我们停下来观望的时候,轿车出发、进入了附近巨大的石造建筑物里。我们中间有人说了,我们也走吧!我们朝那边走去。分明是几个人一起出发的,但在走进空旷的建筑物时,只剩下我和另一个人。
一个我记不清脸孔的人静默地跟在我身边,我能感觉到那是个男人,他因为不知道怎麽办才好,只能跟着我走。只有两个人,我们还能做什麽?昏暗大厅尽头的房间透出灯光,我们进入那里时,那个凶手背靠墙站着,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另外那人的手里也拿着火柴。只有在这根火柴点燃的时候才能说话,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是规则。那个凶手的火柴已经燃烧殆尽,大拇指快要接触到火苗了。我和同行那人的火柴还在燃烧,但正快速燃尽。凶手,我认为应该这麽说,我开口说道:
凶手。
没有发出声音。
凶手。
应该说得更大声一点。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那些被你杀掉的人,你要怎麽办?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突然想起要接续的话。现在就要杀了他吗?这对所有人来说是最後的机会吗?但是要怎麽杀他?我们怎麽可能杀得了他?我转头看向旁边,同伴的脸孔和呼吸声都极为模糊,微弱的火苗显露出橙色的火花後快要熄灭。我从那微光中清晰地感受到,那根火柴的主人非常幼小,只是个身高略高的少年。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在完成书稿的隔年一月,我去了一趟出版社,目的是为了拜托他们尽快出版。我当时愚蠢地认为,只要书出版,就不会再做噩梦了。编辑则说在五月出版的话,对销售更加有利。
图片来源:《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_IMDb
在完成书稿的隔年一月,我去了一趟出版社,目的是为了拜托他们尽快出版。我当时愚蠢地认为,只要书出版,就不会再做噩梦了。编辑则说在五月出版的话,对销售更加有利。
配合时间出版,多一个人读不是更好吗?
我被这句话说服了。在等待的期间,我又重新写了一章,後来反而是在编辑的催促下於四月交出了最终书稿。书几乎准时在五月中旬出版,但噩梦此後还是一直持续着。
现在我反而感到惊讶,我既然下定决心要写屠杀和拷问的内容,怎麽能盼望总有一天能摆脱痛苦,能与所有的痕迹轻易告别?我怎麽会那麽天真、那麽厚脸皮地盼望呢?
▌看更多小说推荐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