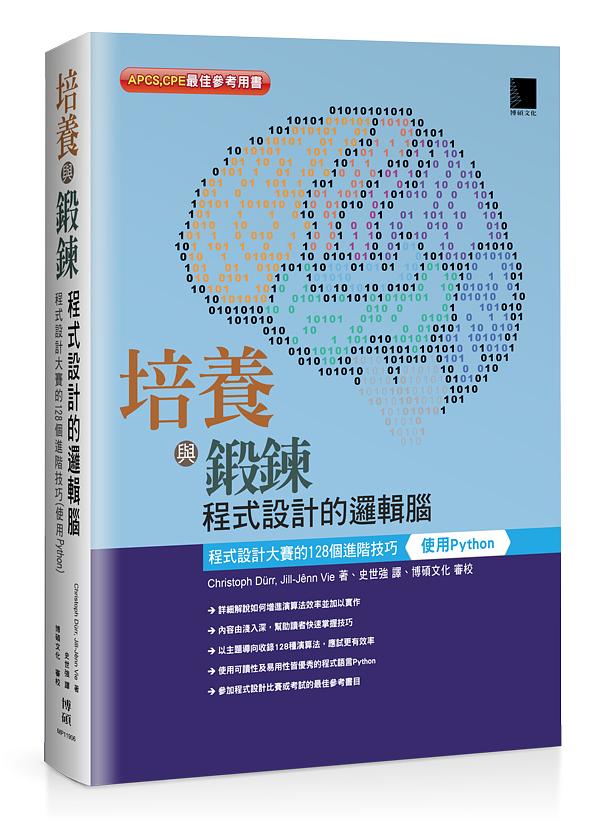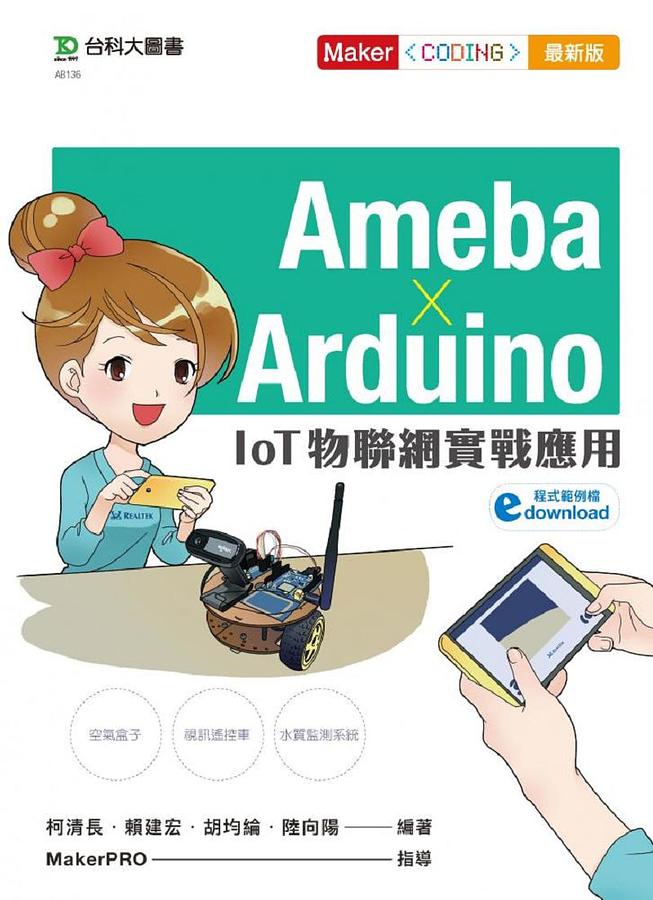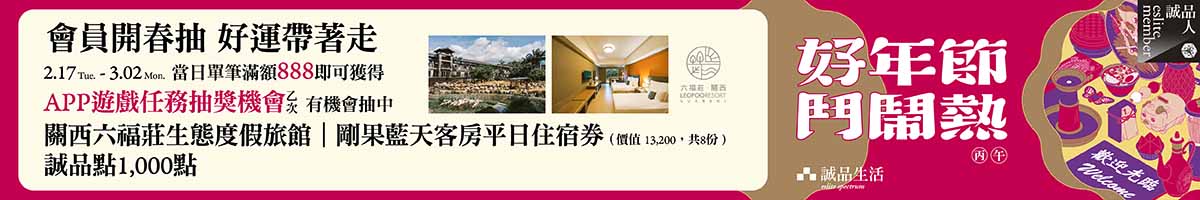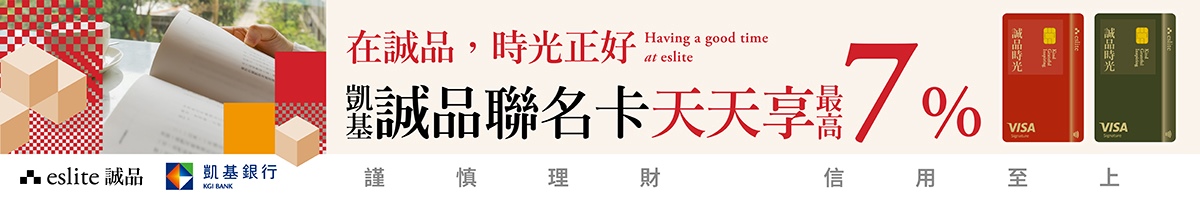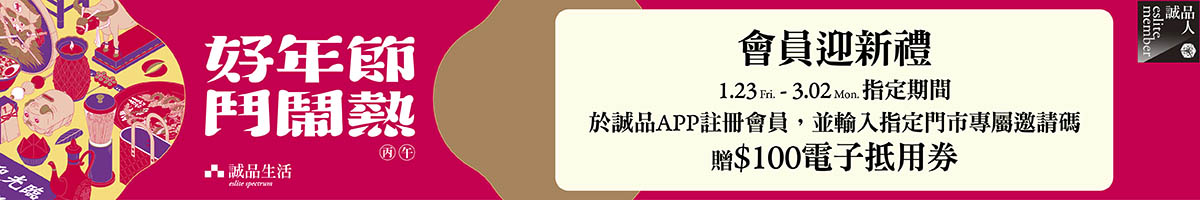李奕樵:斜杠不是两个赛道,而是你专属的新赛道——《提案》5月号「工作的理由」
撰文 李奕樵任何人的资源都有客观上限,但主观愿望却是无穷的。在这背景下,不管是否擅长数学,我们都会非自愿地变成一台以「过好人生」为目标的演算法解题机。
演算法有两个常见的策略:「摊销」与「分而治之」。摊销是用更少操作,同时达成更多目的。举例来说,工作跟梦想都很花时间,那麽把梦想变成工作,或是将工作当成梦想,是不是就能降低时间成本了呢?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摊销策略。
「分而治之」则相反,它会尝试将复杂的问题拆成多个更好解的子题。举例来说,我的数学天赋没有好到能让我当成人生的目标,而我也没有把握用文学创作付清房贷,就很适合采用分而治之的路线:靠程式来提供经济价值,然後靠文学在文化上贡献社会。
两者的心智状态的确不一样。软体工程师在工作的时候,会大量使用逻辑推理的能力,像是一场永不停止的解题游戏,难度适中;而小说则不然,小说同时会需要动员逻辑推理与非常多面向的感受能力,而且难度高得不合常理——人们不会同情你的对手是卡尔维诺、卡夫卡、金庸、还有一整座当代网路奇观。以战争场景比喻,工程师是在坦克中引擎部件运转的某个齿轮,而写小说像是顶着枪林弹雨推进的战地记者。
资讯科学、文学在新赛道擦出的火花
软体工程师的训练对小说创作有巨大帮助,带着各种被资本主义淬链过的演算法、系统理论知识、软体开发知识来参与文学,可以带来显着的局部优势。文学创作者的同质性其实很高,文学既有的理论、文本跟知识非常充沛,堪称是注意力陷阱。
研读这些文学既有知识带来创作品质提升的机率并不高,原因不是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不好,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曾经是有足够经济诱因跟社会影响力的领域,所以有大批天才涌入这个领域充分竞争。也正因为这个充分竞争,导致许多杰作的实践都是追求当下时空条件或特定美学偏好的区域最佳解(注一),不是适合当代新手参考的范例。适合作为策略参考的,反而是征服主流市场的大众文学跟足够抽象的跨领域知识。而资讯科学的各门知识,就非常适合作为策略的参考。
举例来说,可以把文本视为程式,运用演算法知识去优化我的文本成功机率;也可以使用软体公司的品管流程来拟定不同阶段的修改策略;又或者,可以将自由软体的文化移植到台湾的写作社群中,让数百位同世代创作者低成本帮助彼此的同时,我也顺便从中受益,得以写出更好的小说。结果是惊人的,资讯科学不只构成了我独特的创作者人格,更构成了台湾当代文学人口的一个独特族群。
反过来说,小说家身分对我的软体工程领域还没有贡献,但我对各种可能性保持敬畏,在永无止尽的解题过程中,还是会让我的小说家身分在脑中简短发言。
平衡的智慧,避开失速无力,享受这场竞赛!
目前为止的人生简直太快乐了。我能感觉到自己对各种情境的能动性。分而治之策略带来了资源配置的灵活性,能大幅度提高总体策略可行性,我可以选择在软体工作忙碌的时候减少文学产出,或刻意选择相对轻松的软体工作(为此忍痛婉拒台积电的面试邀约)来增加文学产出。这种弹性让我用非常长时间尺度去看待自己与文学跟软体的实际关系,我的文学路不靠频繁出书维持,也不会因为职场竞争付出全部身心。这样的安全感,是我能为文学社群长期付出的基石。
「想像朋友写作会」(注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文学创作者,但我们很少去讨论该如何分配这两者,多数时候,我们努力工作,剩余时间才用在文学艺术上。人不是生来作为工作机器或艺术创作者的,两件事都可能消耗太多。要能享受两者的关键很单纯,就是控制它们的难度与量。充满智慧地拆解它们,就有机会活在心流体验中。
注一:数学代数中,面对复杂问题求解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在一个求解方法找到的,可能是一个小范围内的最佳解,但是把范围拉到更大去观察的话,又常常能发现新的最佳解。
注二:自二〇一七年成立至今,以「创作技术的交流与分享」为核心理念,由各种职类与特殊专精的创作者组成,定期开放常态入会申请。

撰文|李奕樵
正职为软体工程师的业余小说创作者。想像朋友(IF)写作会成员。着有短篇小说集《游戏自黑暗》。
关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阅读与风格采买的书店志,纸本刊物每月1日准时於全台诚品书店免费发刊。每期封面故事讨论一个读者关心的生活与消费的议题,推荐给读者从中外文书籍、杂志、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线上阅读《提案on the desk》
云端下载《提案on the desk》
《诚品书店eslite bookstore》粉丝专页
Current Issue_工作的理由
Dear Job, What Are We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