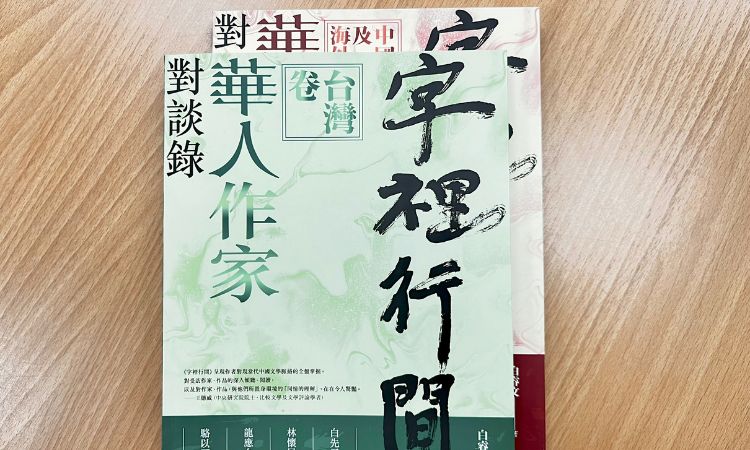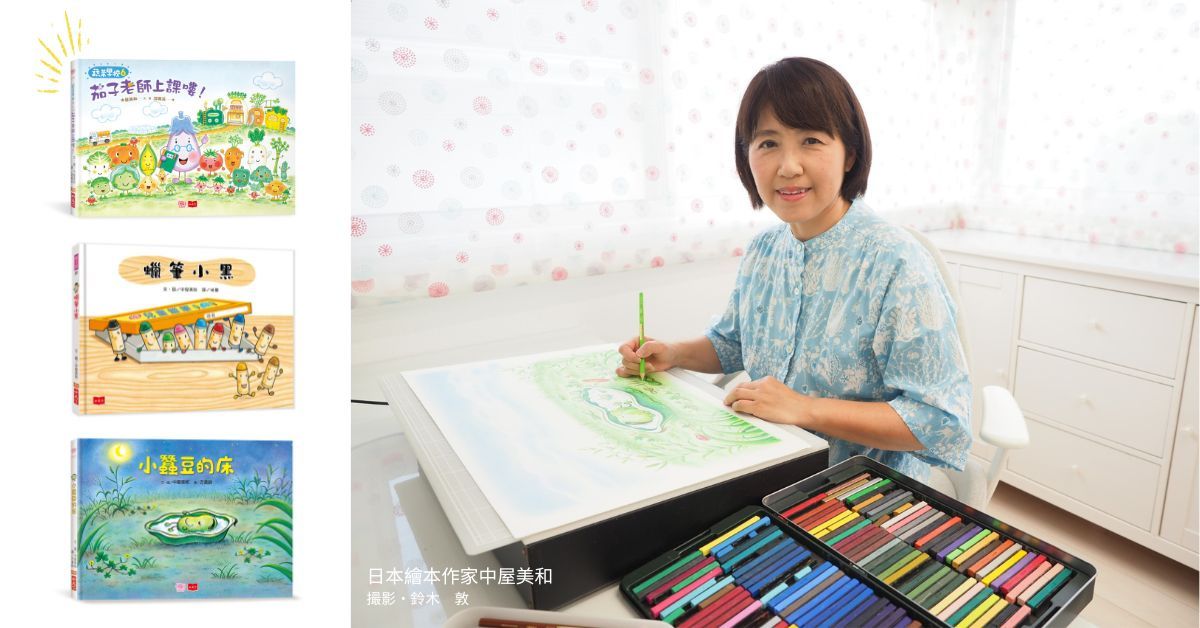華語電影研究學者白睿文從 2000 年代初期便陸陸續續展開一系列的專訪,採訪的對象涵蓋範圍極大,包含文學作家、導演、音樂家、藝術家等等,每場訪談以細膩卻精闢的對談,挖掘不同領域創作者的想法與脈絡。
而《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台灣卷》中集結八位文學界廣為人知的著名作家,包含白先勇、林懷民、龍應台、駱以軍、吳明益、舞鶴、陳栢青、陳思宏,透過深入訪談,探索這些創作者的靈感來源,感受不同作家書寫題材的差異,呈現台灣文學圈多元且豐富的創作風貌。
以下為小說家陳栢青的訪談,在他的創作歷程中,曾出版小說《尖叫連線》、《髒東西》,作品以癲狂的敘述角度,跳脫常理範圍,甚至與鬼片產生特殊的連結,不過這些元素為何頻頻出現在他的創作中?而他成為作家的契機又是什麼?透過專訪,得以更了解陳栢青的創作故事。
▌知名作家的訪談精華
白睿文採訪過許多不同領域的創作者,透過深入採訪,得以知曉這些作家的創作歷程,以及靈感來源。
本書收入八位台灣文學作家的訪談,探索台灣文學的豐富與多元。
▊作者
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年於美國芝加哥出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
現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亞洲語言文化教授兼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華語文學、電影、流行文化和翻譯學。
作家陳栢青成為小說家的契機
Q1:除了閱讀,寫作也需要經驗和想像力。您個人的經歷,比如當兵或跳舞——我聽說您跳了八年的《洛基恐怖秀》,是否對您的寫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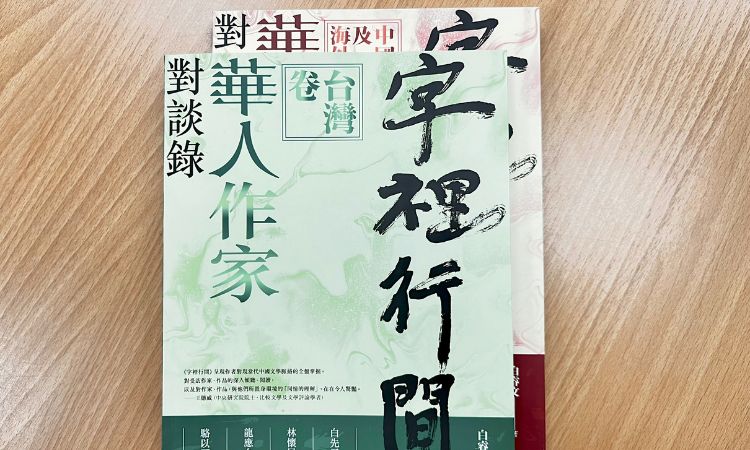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一開始,我並沒有想過要成為作家,只是個物質慾望很強的傻小孩(笑)。我的前半生都想活在舒適圈裡,想被父母保護,想被朋友圍繞。三十歲之前,我的目標就是逃避兵役。因為台灣每個男生都得當兵,我決定這一生都不要當兵,於是我選擇了逃兵。
逃兵的方法是什麼?在台灣,就是成為殘廢。但如果我殘廢了,我在同志市場的吸引力會大打折扣,所以我不能殘廢(笑)。於是我只能選擇過胖或過瘦,但這樣也會減少吸引力。所以,為了保持競爭力,我只能一直念書。高中後上大學,大學念了七年,為了逃避兵役;研究所又念了七年。所以,三十歲前我全部的時間都在學校,從未走出過學校的圍牆。
碩士畢業後,政府還是要我去當兵。我決定去一個我從未去過的地方。當時政府推出了替代役,於是我選擇了海外服役,我去了菲律賓。在菲律賓的經歷,真的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那時剛好遇到廣大興漁船事件,菲律賓軍艦掃射台灣漁船,台菲關係異常緊張。同年,軍中還爆發了受虐事件。我想,在這個風口浪尖,讓我去菲律賓,我要不是被自己人殺死在軍中,就是在異國為外鄉人憤怒的獻祭。
等我抵達駐地。那是我待過最破落的飯店。史蒂芬.金的「鬼店」跟它一比,真的像是皇宮一樣。我抵達那一晚,菲律賓被那年亞洲最大的颱風暴風圈所籠罩。我哪裡也去不了,只能困在房間裡。這就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出國。離開舒適圈的第一晚。窗外暴風像是某種人生的預言。我上了床。我以為我睡著了。至少睡了有一會兒吧。某一刻,忽然醒來,發現四周一片漆黑,按床頭燈,燈沒亮,發生什麼事了?停電了。還好對一個台灣長大的小孩來說,停電是常有的事情。我安慰自己,不怕不怕。我在台灣受的訓練就是為了這一刻。
黑暗中,雖然眼睛看不見,但在我的內心,在潛意識裡有個聲音低低地對我說:「可是,栢青,你不覺得房子裡有哪裡怪怪的嗎?」真的是什麼都看不見啊。我只能安慰自己:「陳栢青,你不要亂想,你是個瘋子。」我用盡氣力安撫自己。就在心跳趨緩,就要重新入睡的那一刻,忽然,一道雷打下來,雷光非常亮,我想那雷就打在窗戶旁邊,一瞬間,整個房間都在發光。
耳邊嗡嗡作響,在那轉瞬而滅的雷光中,我忽然知道,房間裡哪裡怪怪的了。因為剛才的雷光,我清楚地看見,原本應該散落在房間的三張椅子,不知何時正有序地排列著,以我的床為中心。像開圓桌會議般圍繞著我。
黑暗中,我被三張椅子圍繞著。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認清這件事的第一時間,我只冒出一個念頭:「所以,剛剛,在那樣的黑暗中,有什麼東西在椅子上看著我?」那時候我真以為自己就要掛掉了,要被黑暗吞噬在這間旅館裡。但跟著,我又想起來,畢竟我是看著港片長大的孩子,眾多港產恐怖片告訴我一個奇怪的知識是:鬼最怕的,是軍人和警察。
當下我想,哎喲,這麼巧,我可不就是中華民國軍人嗎?於是,我立刻展示我在軍中受到的優良訓練,三十秒時間掀開棉被,四十秒時間翻身滾下床,六十秒快速著裝,然後踢著正步走回床前。我用軍中教我的坐姿端正地坐在床沿,我想,「鬼」既然看著我,那我也要看著它們!於是,我瞪大眼睛,一直盯著那三張椅子,一直瞪到天亮第一縷陽光射進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在海外的經歷。
雖然已經超過十年了,但每次回想這段經歷,我總感覺又回到那個房間。我仍然記得那三張椅子。但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想起那三張椅子,一邊害怕,我也會想像,如果當時我踢著正步,走到椅子旁邊,卻就著椅子坐下來,那會發生什麼事?如果當時,我踢著正步,卻直直穿過那三張椅子,走向椅子後面的黑暗,會發生什麼?
黑暗是那樣恐怖,卻又甜美,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寫作是什麼,我會跟人說,寫作,就是去那三張椅子後面的黑暗看看,並從那後頭帶回來什麼。
從那一晚之後,我嘗試從黑暗裡帶回去什麼。我成為了一名作家。
▌更多作家陳栢青談文學
作家陳栢青從恐怖電影獲得書寫題材與靈感
Q2:謝謝您分享這麼精彩的鬼故事。說到鬼故事,其實您的小說《尖叫連線》好像跟日本恐怖電影《七夜怪談》有種特殊的關係?可以講講這部小說與恐怖電影的特殊緣分嗎?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白老師剛介紹我時,提到了我每年都會去電影院參與《洛基恐怖秀》的演出,這是台灣金馬影展舉辦的活動,會有表演者扮裝在電影院裡隨著電影劇情一起演出,和觀眾直接互動。我記得第一次受邀演出時,驚訝地發現,在這個世界上,一個男孩可以被允許穿女裝、化妝,而沒有人會討厭你,甚至所有人都為你鼓掌。與其說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是「自由」,不如說,是讓我感受到,什麼是「無限」。
有一年表演完我妝還沒卸,就直接從演出的戲院走出來,想直接回飯店去。剛進飯店門口,管裡櫃檯的大媽正低頭在吃東西,她一個抬頭看到我,臉色忽然大變,我和她同時聽到筷子掉在地上的聲音。從大媽身後掛的鏡子,我立刻知道她看到什麼─鏡中的我經過一整天的表演,現在是最醜的模樣。頭髮已經歪了一邊,裡面的髮網都露了出來,高跟鞋也有點歪了,衣衫不整,臉上妝容多半也脫落了。一下巴新鮮的鬍渣。
怪物。不男不女。醜八怪。死人妖……大媽其實沒有說出這些詞彙來。但看著她的表情,以及她身後鏡子中的我,我耳邊像有無數人正張開口,那是從過去到現在曾經傳入我耳邊的聲音。我以為它們已經消失了,但其實沒有,它們隨時會冒出來……
只要一個夜晚、一張鏡子,一切就會重現。一切就會回來。「我走錯了飯店了,對不起。」我正準備轉身要逃跑。突然間,大媽叫住了我。她低頭窸窸窣窣不知道在翻找什麼,接著,遞出一根吸管,對我說:「用這個喝,口紅才不會掉。」我忽然明白,大媽並沒有嘲笑我,她反而關心我的口紅有沒有掉。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就算你是怪物,你也會被某人寵愛,被人喜歡。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那時候我就想我要寫一個怪物的故事,所以我有了第二本書《尖叫連線》。《尖叫連線》是本長篇小說,故事講述台灣發生了一種恐怖的傳染疾病,叫HLV,只要感染三天後,感染者就會變成喪屍,然後死掉,所以台灣正面臨滅島、滅國的危機。
可是我們的女總統想到一個方法,她小時候看過一部恐怖電影叫《七夜怪談》。《七夜怪談》這部電影大綱是,只要你看了被詛咒的錄影帶,七天之後貞子就會爬出來殺死你。女總統就想,按照這部電影的邏輯,只要我讓全台灣的人都看了《七夜怪談》,那大家就會被貞子詛咒,感染者就不會死在三天後,而是會死在七天後。
於是,總統派出了一個小隊去尋找這卷被詛咒的錄影帶。《尖叫連線》描述的是這個小隊的故事,我設計小隊裡全都是好萊塢恐怖電影裡最早死掉的那些失敗者,比如《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裡第一個被殺的啦啦隊隊長,比如《半夜鬼上床》(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裡只愛看書考試的眼鏡妹……我想把所有恐怖片裡一看就知道他會死掉的人集合起來,例如那些愛亂講話娘娘腔的 gay,有色人種,亂搞的辣妹,只有身材沒大腦的體育生……我想讓這些人來拯救台灣。對我而言,我相信,能夠拯救世界的,是這些受過苦,是這些被遺棄的人們。
就像我在跳《洛基恐怖秀》時遇到的旅館大媽。我想把詛咒變成一種祝福。
Q3:那從《小城市》到《尖叫連線》,是否有一些在寫《小城市》的過程學到的寫長篇的技巧,直接用到第二本呢?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圖片來源:秀威資訊提供
我學到某種技術,不如說,從《小城市》的紅衣小女孩,到《尖叫連線》的諧仿、搞鬼,我真正感受到的是,我越來越逼近某個自己在意的核心。你會發現,我很喜歡寫鬼,不如說,我真正想要它現形的,並不是電影中的鬼,而是真實人生的。那麼,在真實世界中,什麼東西是「看得見,又好像看不見」的呢?對台灣社會而言,就是同志。
我的第三本書《髒東西》就想寫台灣男同志史。不是透過電影的鬼來象徵,我要寫台灣社會中的鬼。台灣歷史中的鬼。社會禁忌中的鬼。我要讓他們從歷史中現形,如果他們消失了,我就替他們招魂,如果他們不存在,我就要讓他們附身,我要讓男同志的幽魂遊蕩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也就是說,我不但想替台灣男同志寫史,我還想在台灣史中創造男同志。
✦
▌更多台灣作品推薦書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