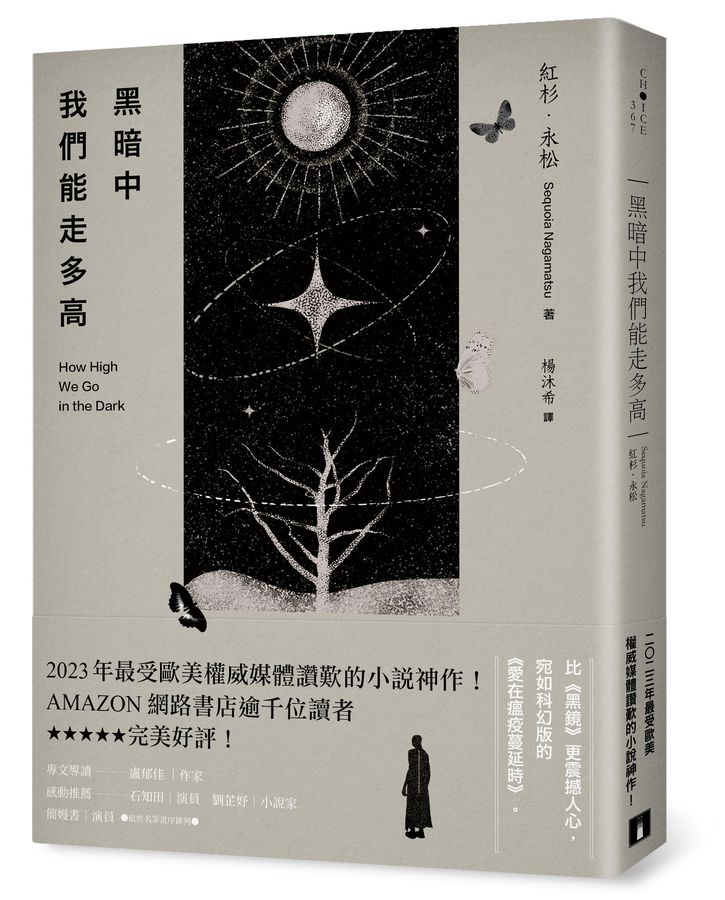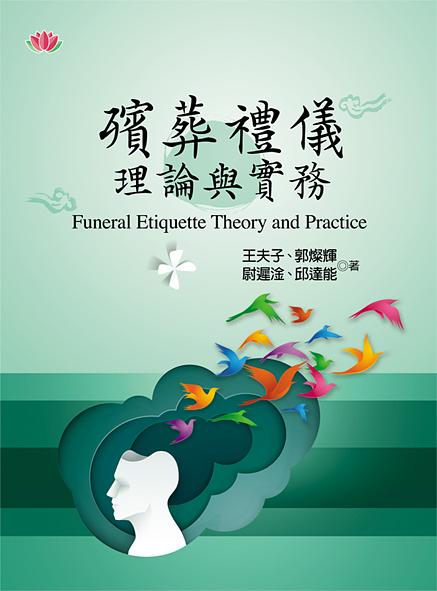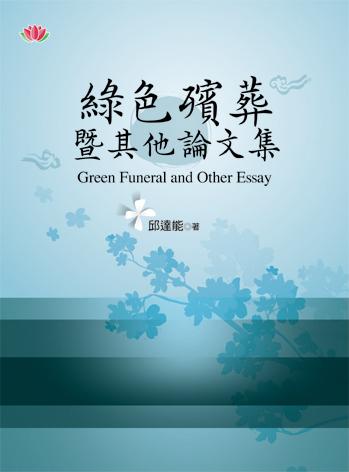专访作家红杉.永松:黑暗有时能够让我们脱离每天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是谁,想要成为什麽样的人。
撰文 紅杉.永松.採訪|皇冠文化Q:本书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透过人类遭逢生存环境上的钜变,刻画人与人关系间细腻动人的情感。请问您是如何发想这个故事的起源呢?
A:一开始,这本书只是想探索哀伤与不同以往的殡葬仪式。当「一般」的道别方式已经行不通,或是不够的时候,生者该如何向死者道别?这本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都没有疫情的元素,一直到2014年写到一半时,我才加入传染病,作为包含且连结所有篇章的关键。所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诉说背景设定在未来的疫情故事,以及这样的背景对每个人及群体有什麽样的影响。这只是这麽多年後,这本书自己发展出来的样貌。
Q:承上题,虽然故事背景是在「未来」,但在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代来看,却非常有既视感。请问作者想透过这个故事给现在的我们什麽启示或预言吗?
A:如同上述所言,我并没有设定要写一本传染病小说,但我想重点在於本书是在Covid之前完书的。因此本书反而聚焦在群体、连结、宽恕、在至暗时刻掌握微小希望等主题上。这些启示理当可以运用在大疫时分,但我觉得这本书的视野远超过传染病,也请读者稍微停下来,不要一直去想自己的生活与现在的世界,反而展望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具社会性的未来,每个人都能更关怀彼此。
Q:本书书名《黑暗中我们能走多高》,您指称故事中的背景是处於「黑暗」时刻。请问您觉得在这个「黑暗」的时期中,人类应该如何共处呢?在这个过程中,有什麽能指引我们走向光明吗?
A:故事中当然有黑暗,某几则特别黑暗。光明与黑暗两者都存在於生命之中,不可能只要其一,不要其二。在小说中,起点可能就是黑暗的。我觉得黑暗有时能够让我们脱离每天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是谁,想要成为什麽样的人。这个世界喧嚣繁忙,我们少有机会扪心自问这些简单的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跟朋友、家人失联,我们容易说服自己,科技可以产生连结,但这种连结通常只是假象。当我们谈到解决世界问题时,大多聚焦在科技、国家或全球政治议题上。不过,我认为希望存在於渺小的行动及细微的连结之中。在邻居与家族间都无法学习拥抱同理心时,我们实在无法指望一个个国家能够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Q:本书共有14篇故事,每段故事都叙述了一段真挚深刻的关系互动。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曾经出场过的主角出现在其他篇章中「客串」,让读者在阅读体验上,有种获得彩蛋的惊喜感。请问您在撰写前,是否会先布局全部的角色人物呢?在创作的过程中,您又是如何与这些角色互动呢?
A:我并没有刻意安排这些关联。一开始,其中几则早期构思的故事就只是独立的短篇故事。不过,在几年的岁月里,我渴望再度拜访某几位角色。在《黑暗中我们能走多高》最後几年的写作历程中,我加深了这些关联,创造出新的连结,增强整本书的连续性与时间线。
Q:您是一位日裔美籍的作家,在本书中也看见不少日本文化的痕迹,例如〈在东京虚拟咖啡厅度过的忧愁夜晚〉、〈但愿死在一起〉,正是以日本东京、新泻作为故事背景。请问东西文化身分的重叠,在您的写作上提供什麽样的养分与灵感呢?
A:偶尔但绝非必然。早期有几篇故事是我住在日本时期写的,我当然对探索日裔美国人及日本世世代代的文化产生兴趣。不过,我不希望《黑暗中我们能走多高》会被视为亚裔或亚裔美国人的小说,因为自古以来,美国人就只认为亚裔或亚裔美国人小说不是跟移民有关,就是在写战争。修改时,我希望强调的是就算长着亚洲脸孔,背景可能还是很多元,特别是在这个全球亚洲人会遭受种族歧视或暴力的时刻,因为有人会认为Covid是亚洲人的错。我希望书里的角色首先是个人吧跟其他人一样会遭逢苦难的人。
Q:本书的14篇故事中,有许多是描写母子(女)间的互动,包括〈悼词下的三万年〉里的克莱拉与由美、〈欢乐之城〉里的朵莉与菲奇、〈但愿死在一起〉里的妈妈与梨奈等。请问您为何会对母子(女)间的情感多有着墨呢?是否与您个人的生命经验有关?
A:某种程度算吧,我喜欢写压力下的家庭关系。我通常会写家人间想要连结的努力与挣扎。这部分来自我与自己家人的关系,所以我想身为作家,我利用艺术表达这些观察与感觉。不算是治疗的过程,而是因为那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希望读者也许能够喜欢且同理我所创造出的不完美角色。
Q:本书背景因为在「极地病毒」的肆虐下,不少人类染疫而亡。故事中也发展了许多与「死亡」相关的行业,例如〈欢笑之城〉里的「安乐死园区」、〈在你融化进大海之前〉里的「冰冻伊甸园」、〈挽歌大酒店〉里的火化套房等等。当「死亡」变成日常,许多社会机制皆绕着它转时,您觉得「死亡」之於我们的意义是什麽?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呢?
A:我想要展望的是企业也许会为了回应大量人口死亡而采取相应的经营方式,在我们经历过疫情之後,这种规模的死亡也许会看起来不太真实。政府、企业,负责界定人类文明的一切该如何被迫回应?我想展示的是资本主义、贪婪、金钱会永远纠缠我们。当然啦,在我笔下的极地瘟疫中,肯定有人会藉此发财。不过,其中许多服务不可或缺,这种新型态的殡葬仪式能够带来慰藉。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不会因为全球悲剧就停摆,股市、房市还是会继续交易。只不过一切会如何推陈出新?在这一切背後,我想预言的是在Covid这种事件後,接下来几十年间,人类的社交行为会如何展开。在我的小说里,好比说〈但愿死在一起〉,就有整个街坊因为极地疫情与气候变迁而凝聚在一起。我不确定真实世界中有没有这种事,但持续观察两、三年间没有社交生活的年轻世代应该满有意思的,这种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交生活。
Q:在最後一篇〈机率之镜〉中,您以一位「创世神」的角色横贯整个地球历史。这个角色既投入又抽离於人类的世界,像是参与,又像是俯瞰我们的生活。请问您设计这一篇故事的用意为何?它作为本书的最後一篇,是否也有特殊的意义在其中?
A:我想过用其他方式建构整部小说、连结其他故事。〈机率之镜〉取材自我研究所时期放弃的小说草稿,但我始终喜爱其中的角色与那个世界。到了《黑暗中我们能走多高》,〈机率之镜〉的主角过上不同身分的各种生活。某种程度来说,在众多角色里,这个外星人是最具人性的角色,因为她思念女儿长达十亿年的光阴,几万年来,她都在哀悼、寻爱,一再厘清她自己的身分与认同。虽然有战争、暴力与仇恨,但她最终会找到希望。她还记得自己的女儿。我希望最後一章能够带有串连起每个角色的宇宙色彩。
Q:请问本书的14篇故事中,您最喜欢哪篇呢?为什麽?
A:我想我最喜欢的是〈挽歌大酒店〉,因为主角丹尼斯宛如年轻时的我。这一则故事带领我走出家父在疫情中因癌过世的痛苦时期。我与父亲多年没有交谈,因此编纂出一个无法跟家里联络的角色,这样的过程协助我做出我认为正确的选择,与家父道别。
Q:请问您接下来还有什麽写作计画?对什麽题材感到兴趣?
A:我手边有两本书正在进行。一本是一对夫妻用变形人替代死去女儿的故事,另一则的主角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虚构艺术家,内容讲述用塔罗牌与古神交流之类的。
Q:本次是您的作品第一次与台湾的读者见面,请问您想跟读者们说什麽呢?
A:我希望读者能在这本书里看到部分的自己,他们能够在阅读(特别是头两章)的过程中关照好自己。我同时也期待因为我的书结合了不同的类型与风格,读者能够重新审视所谓文学与科幻小说的刻板印象。
作家|红杉.永松 Sequoia Nagamatsu
日裔美籍作家,创新文字网路季刊《灵魂向导》主笔。於夏威夷及旧金山湾区成长,拥有南伊利诺大学创意写作艺术创作硕士及格林内尔学院人类学学士。他的作品刊登於《联合》文艺期刊、《南方评论》文学季刊、《象鼻虫》杂志、《童话评论》及《锡屋》杂志。着有得奖短篇故事集《我们不在之後去了哪里》,於圣奥拉夫学院教授创意写作课,指导雷尼尔写作工作坊远距艺术创作课程。现与妻子、猫咪及名为卡尔维诺的机械狗一起住在明尼苏达州。
关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阅读与风格采买的书店志,纸本刊物每月1日准时於全台诚品书店免费发刊。每期封面故事讨论一个读者关心的生活与消费的议题,推荐给读者从中外文书籍、杂志、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线上阅读《提案on the desk》
《诚品书店eslite bookstore》粉丝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