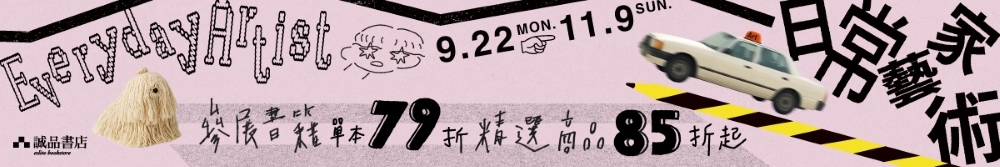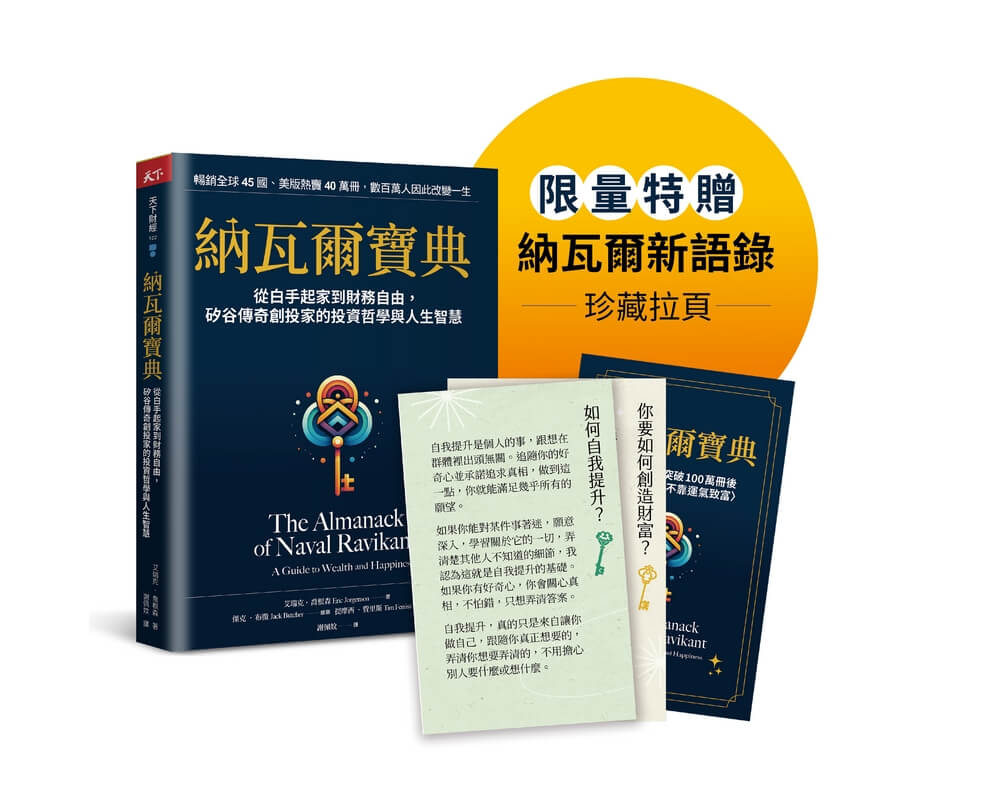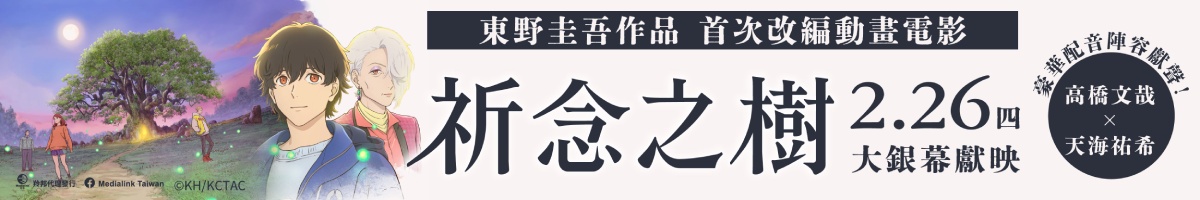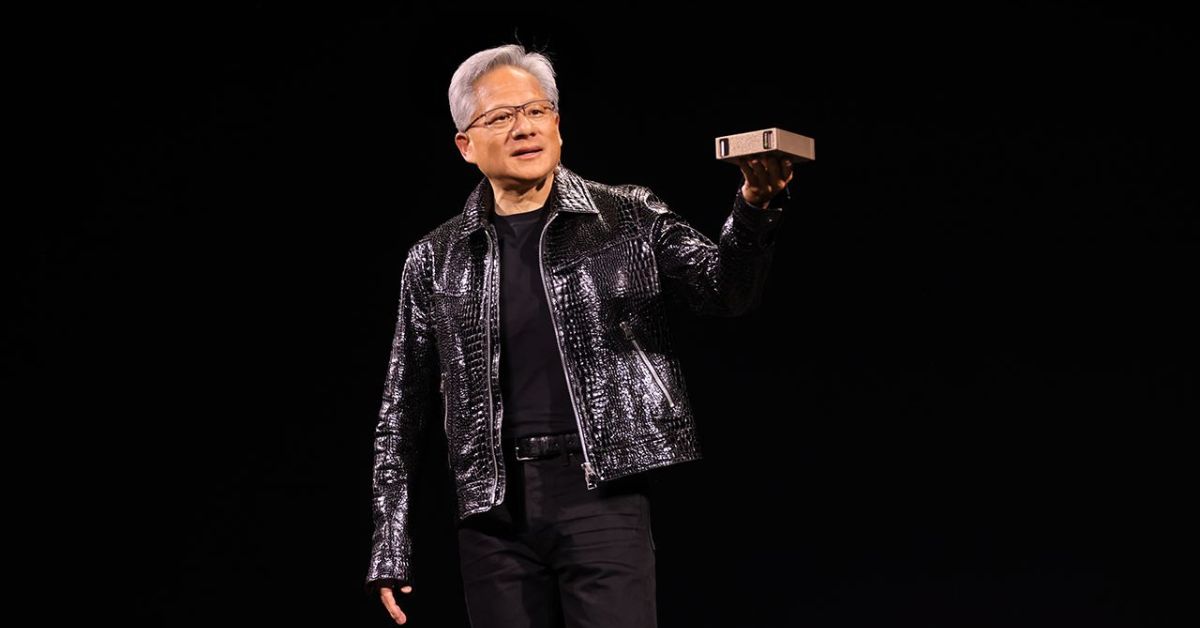若喜欢歌仔戏,对於着名剧团——明华园必然是耳熟能详,而更是对於其中的当家台柱孙翠凤有着深刻的印象。孙翠凤除了能够扮演温柔似水的小旦,更是能够扮演帅气威武的小生,惊艳四方,成为台上引人注目的焦点。
歌仔戏对孙翠凤有着深厚的情谊,也是在谷底拯救并拉起她的稻草。出生於嘉义的她,儿时举家迁入台北;由於父母不愿意让她踏入歌仔戏的行列,因此她直到26岁才开始学戏、勤勤恳恳练习台语,渴望以此回报照顾她的明华园大家庭。
孙翠凤在意外之下挖掘了担任小生角色的天赋,於是她花费多年揣摩每个男性角色,在她精彩的演绎下,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面相,使她成为无敌小生。戏里戏外,每个角色都是她的悲喜,她的痴迷。人生淬链出她的刚柔并济——她是无敌小生,更是逆风前行的勇敢查某子。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皇冠文化集团,首图由明华园提供}
▌无敌小生的半生淬链
有着无敌小生、明华园台柱之称的歌仔戏国宝孙翠凤,凭藉高超的技巧,出演许多威震四方的角色。
除了这层身分外,她同样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兜兜转转於不同角色间,在人生中演出最精采的一道光。
▊作者
孙翠凤
人生如戏,所有角色她都演,台上台下,全是她自己。她登过颠峰,也行过低谷。她以苦练换得掌声,用青春累积智慧,凝链成柔韧丰厚的底蕴。
如今她想要走得更远,抵达更多人心里;也走得更广,将歌仔戏的生命力不断传承下去。她是不畏逆风的查某子孙翠凤——戏里的无敌小生,戏外的无敌女人。
被明华园接住的瞬间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我的人生,曾经跌落到最幽深的谷底。而张开双手将我稳稳接起来的,不是别人,是明华园。
约莫是二十六岁的事了,所有的坏事都发生在那一年,孩子骤逝、事业失败;公司收了、房子卖了,我和胜福夫妻俩穷途末路,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什麽都不剩了。几个月前明明还是百花齐放的春天,怎地一夕遁入了无生息的严冬?
这些厄运来得太急,我们不敢让远在屏东的公公婆婆担心,但他们早听说我们的处境,婆婆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说:「家里不缺碗筷,你们回来,别留在台北被人糟蹋。」胜福很有责任心,他不甘在落魄的时候回家,更不愿抛下债务一走了之,於是他劝我先回去,他说:「回到明华园,至少还有公婆照顾你。」
位於屏东潮州的明华园是个家族剧团,一家三代都在演歌仔戏,在公公陈明吉与婆婆陈水凉的当家之下,数十口人依着一口灶、一辆卡车,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我不会唱戏,回家就成了没有用的人。」我哭着跟胜福抱怨,明华园的媳妇们个个站上戏台能文能武,众人排开就像杨门女将一样,就只有我这第三房的媳妇在台北坐办公室,别说唱戏,连台语都说不标准。胜福要我别伤心,他像哄小孩一样劝我:「没关系,没有人会强迫你唱戏,我爸妈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一九八四年,在公婆的频频呼唤下,我抛下台北的失意与落魄,带着简便行囊回明华园,当时没有想到,我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会在这个暖洋洋的大家族里蓄积能量。
彼时的明华园已是戏剧比赛的常胜军,一九八三年获邀到国父纪念馆演出後,更被赋予文化责任,许多庙宇酬神都喜欢找明华园搭台演出。而我是戏班里唯一不会唱戏的「台北媳妇」,连台语都说得零零落落,心中难免隔阂。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好在公婆的疼惜,回到屏东的日子,我每天跟着戏班出门,他们忙着演戏我乐得看戏,众人们更是左一句「三嫂」,右一句「三婶」,喊得我心里温暖,几乎忘记不久前还紧箍着我的阴霾与悲伤。
公婆的包容与疼惜,陪我走过生命中的暗潮,他们愿意娶不会唱戏的媳妇进门,即使缺人手也不曾逼我上台,在我们经济压力最大的时候,偷偷帮我度过难关,家族成为胜福的靠山,也是我的避风港,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让我下定决心为家族付出,即使这不是我能胜任的环境,我也不会退缩,哪怕我只能在剧团里跑个龙套,我也决心将自己奉献给明华园。
婆婆引我来到案前,案上供奉着戏班的祖师爷「田都元帅」,我点起三炷香再伏首膜拜,犹记得那天屋内香烟袅袅,阳光斜斜地照在我身上,我凝视着祂,嗅着鼻间隐隐约约的檀香,慌乱的心渐渐定了锚,我原以为自己此行是离家,那一刻才明白,原来这里就是我的家。
▌回味传统技艺的美好
坐卡车跑码头的辛酸与欢笑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在一九八○年代,即使明华园已从野台戏被邀请到国父纪念馆的大舞台演出,但在主流艺术领域中,它依然像是流落乡间的孤儿,只能克难、坚忍地在民间薪火相传。
当时的明华园已经被赋予文化传承的使命,所以我们常常跑遍全台乡镇进行户外大型公演,但无论到哪个乡镇,就是一部老卡车把大家载到现场,到了晚上不是睡货车就是睡戏台,我们省住宿费、省交通费,不怕吃苦,齐心协力地把微薄的演出费用一分一毫攒下来。
刚回到明华园,我肚子里已经怀了昭婷,公公婆婆对我很是包容与疼惜,他们交代各房媳妇要好好照顾我。有一天,剧团要远赴小琉球演戏,这一趟出门预计十来天跑不掉,我抱着远足的心情跟他们一起出去「跑码头」。
兴匆匆来到门口,没想到交通工具就是一部老卡车,车斗堆满道具与布景。「游览车呢?」只见我的妯娌把行囊扔上去,三步并两步爬上车斗,我心想这是什麽功夫?上头的人就喊了:「三嫂,赶紧上来!」
我怀孕带球走路、背着背包、攀着车身,远远看过去像只笨拙的大乌龟,我夸张地喊着「来人,搬梯子」,他们简直笑翻了,赶紧提点我:「右脚踏铁板、右手攀车斗、左脚踩铁栓……」一群人又拉又推总算把我挤上卡车。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俗话说:「各人有各人的风水。」只见车斗虽然被布景和戏箱塞满,但众人熟练地钻入其中,或倚或靠,都有一处安适的地方。他们帮我找了一个孕妈咪的「博爱座」,是众多杂物之间最不容易颠簸的地方。
我靠着卡车的帆布和铁架摇摇晃晃抵达目的地,别说休息,遇到路面不平还得小心别摔下去,这段交通过程,让我这个道地的「台北俗」很不能适应。
後来我渐渐发现,坐卡车是我最痛苦的事,白天一夥人嘻嘻笑笑就度过了,但有时若接到早戏,需要在两地之间连夜「过位」,那段坐在车斗的时光,只能听着风声呼啸耳畔、长夜无眠,每每望着天上星斗,那股从内心深处不断滋长的孤寂感最为难受。
我的睡眠品质向来不好,每当需要过位时都忍不住头皮发麻,上了车,我左看右看,大家彷佛睡仙上身,任凭路途颠簸依旧睡得香甜,在鼾声与风声夹杂之中,我总心想:「你们真的是天生吃这行饭呢!」
白天前台演戏、後台着装,入夜後草蓆一铺就成了床。前台是男性工作人员的地盘,後台则是单身女性与夫妻档的位子。大家拿出各自的行囊,里头装了草蓆、棉被、枕头,在戏班长大的人,自小练就一躺入眠的能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其中,夫妻档在外演出,若想睡得隐密一点,还能拥有自己的「高级套房」,那是把舞台上约莫半身高的木制布景拉来隔间,我第一次看到时忍不住惊呼,「这是开放式的套房吧!」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很有默契地不会窥探隐私,说起来也很温馨,我们剧团里很多小孩,都是在这样的高级套房里诞生的。
我腰椎受过伤,即使已经备妥两件厚被,睡在木板或戏箱上,左翻右翻依旧疼得睡不着,且戏台由长条木板搭建,好不容易即将入眠时,只要有人起身,总是踩得木板嘎嘎作响,等到我再次酝酿好睡意时,天空已泛起鱼肚白,大夥又要起身工作了。
那段失眠的日子,我总是数着星星、看着月亮,听着野外虫鸣此起彼落,夜里冷冷清清的戏台,让人格外寂寥。偶尔眼角瞥见那处小套房,更加思念远在台北的丈夫,和与自己无缘的大儿子。
这样的野台生活,我真的撑得下去吗?胜福知道我孤单无助吗?他自己又过得好吗?我的大儿子有到佛祖身边了吗?祂会到梦中找我吗?每思及此,多愁善感的我总是止不住情绪,後来我学会无声哭泣,总是在其他人发现之前,偷偷把眼泪擦乾净。
下定决心学唱戏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二十六岁那年,走过这段跟着剧团南征北讨的日子,我体会了做戏人的甘苦,看见大家族同心协力为了歌仔戏努力,彼此间没有一句抱怨,那样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是我这个都会女性从未感受到的情感,加上公婆的体贴与包容,使我暗暗下定决心:「好!我要加入你们!」
其中,我效法的对象就是家族里那些身怀绝技的戏班媳妇们,台下轮值张罗大家族的餐食,上了台个个都是足以撑起一片天的名角,而我身为唯一的「台北媳妇」,别说唱戏,连台语都说得怪腔怪调,有时我也难免焦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家中的一分子。
但我的成长过程,也非与戏班绝缘。事实上,我的父母亲早年曾随着戏班漂泊,他们不愿儿女踏上这条艰苦的路,因此举家搬迁台北,并供我读书,让我远离戏班生活。
记得公婆当年提亲时,母亲什麽聘礼都不收,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让我回去演戏。胜福听了在旁打包票:「她那口外省台语也没人听得懂啦!」而我公婆确实信守承诺,即便家族再缺人,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色,他们也不曾要我上台演戏。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其实胜福说得没错,我的父亲是河北人,他说的台语有很重的乡音,到了学校说国语,出社会後当起办公室OL,更没有机会说台语,日子一久跟母语都生疏了。但回到明华园,听不到任何一句国语,就连牙牙学语的孩子,学的第一句话也是台语。
记得胜福有时回到屏东探班,我们总习惯用国语交谈,我的妯娌有天私下告诉我:「三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在家讲『北京话』?公婆听不懂,他们以为你们有什麽烦恼不好说,老人家在旁看了很担心。」
原来让老人家误会了!我於是决定昭告家族成员:「你们以後都用台语和我对话,若我下意识用国语回答,大家就装没听见吧!」开始苦练台语後,我觉得自己跟家族愈靠愈近了,渐渐地也想为家族尽一份心力,眼看戏班常常缺人手,有时连司机也得跑个龙套,我便决定毛遂自荐,我想更融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图片来源:明华园提供
其实早在一九八三年明华园北上国父纪念馆演出时,我已经在剧团里跑过龙套,扮演一个没有台词的丫鬟,剧团里上上下下看我扮相漂亮、台风稳健,他们很看好我,便邀请我只要回屏东,就当作来戏班玩,没压力地跑个龙套。
玩票性质与正式学戏的心态自然不同,不同於传统戏班,都是以「听戏」、「口耳相传」的方式学戏,我决定学戏後,便备妥录音机和笔记本,看戏之余勤奋地记录对白,若是漏了两句,下台後便缠着小生、小旦,要他们再唱一次。
▌更多【皇冠文化】系列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