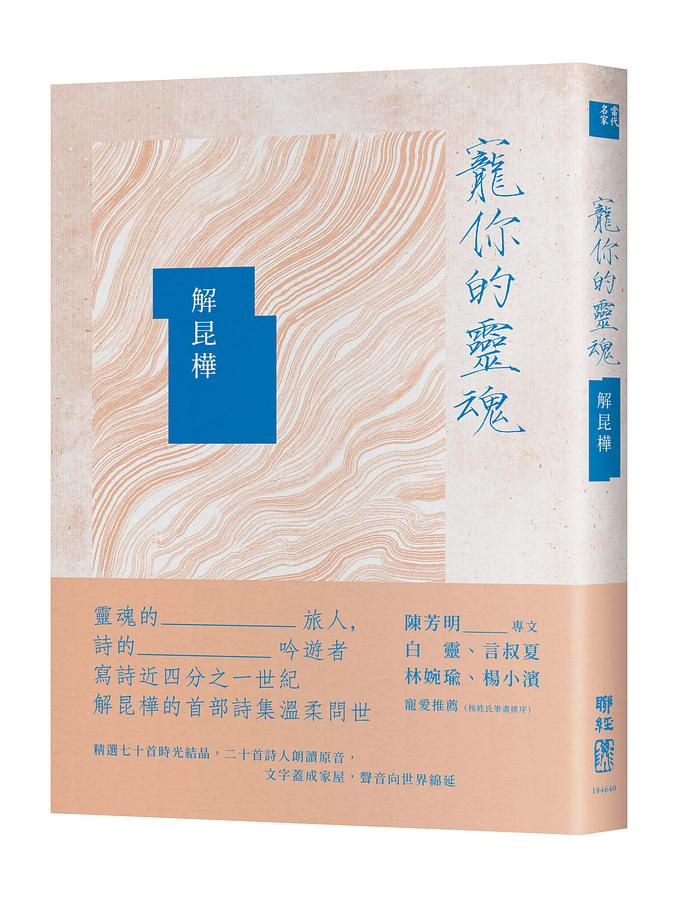专访|在角色里学习内敛、在人生中凝视自己,郑秀文《流水落花》看见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
撰文 女人迷(女人迷原創製作所)你可能不知道,这是郑秀文第 7 次角逐金像奖影后,也是第一次获奖,在这之前还历经忧郁症低潮。跟着女人迷的专访一起,看郑秀文如何从角色找回真实的自己!
郑秀文最新演出作品《流水落花》以寄养家庭议题为核心,注目死亡、别离与爱的本质。
她说,寄养家庭是冷门议题,但剧本使她动容,说什麽都要接下演出。片中,她接下寄宿家庭「天美姨姨」一角,对表演有更深一层体悟,也诚实走进自己的内里。

图片|《流水落花》剧照
《流水落花》(Lost Love)的片名,暗示别离,也谈离别後的延续与祝福。
此片为香港新晋导演贾胜枫首部长篇作品,故事讲述一对丧子的夫妻与七位寄养孩子间的生命故事。电影剪接手法乾净,对故事中孩子流离失所的局促、不舍,轻轻地点到为止。
那种轻,像悄然而至的人生无常:故事已来到下个篇章,观者却仍对句号之间,留有念想。 郑秀文在剧中饰演寄养家庭的「天美姨姨」,一场死後与寄养孩子们重遇的戏,让她懂得回望。
「那场戏情绪很复杂,有笑有泪。年老的天美姨姨逐一注视孩子们的脸,那一刻,她在看似无意义的生命过程里,找到了意义。」
原来离别也是一种延续,祝福生命去往更好的地方。
角色感触也让作为演员的郑秀文有所思考,「跟人生一样。当你回头看,才明白当中的意义,明白有些错误、有些经历没有白费。不过这些都得回望咯,才看得见。」

图片|甲上娱乐(服饰提供:Glasses:溥仪眼镜- Maison Margiela)
50 岁是什麽就呈现出来,我有这种坦然
回望三十年演艺生涯,起伏有时,如今郑秀文拥有一双眼睛,坦然无惧地凝视自己。
「以前每部戏我都很想突破,想有不一样的演出。觉得要演到大家都认不出那个真正的郑秀文,才叫演戏。」
如今她却觉得,角色有着郑秀文的影子是很好的一件事,「现阶段对我来说,演员去到片场并不是要突破,而是要『完整』角色。那得先对自己诚实。」
拍摄《流水落花》时,因剧中角色年龄跨度大,有几场戏郑秀文得素颜上阵。对此她曾分享「作为一位演员不应只在镜头前看见外貌,而看不见最内里的自己」,这与完整角色前须对自己诚实,是同样的道理。
「演员会为服务一个角色做体型、容貌上的调整,对我们这种来到 50 岁的女演员而言,更要坦然地接受自己容貌上的变化。」
「很多时候通过一个角色会碰触到我们的内在,有快乐、明亮的部分,当然也会勾起过去的疼痛与伤疤,人性黑暗的一面,我们也必须诚实地展现出来。基於这样的坦白、诚实,观众才能更靠近角色。」

图片|甲上娱乐(服饰提供:Celine)
在忧郁症之後懂得谦卑
2005 年,郑秀文拍摄《长恨歌》时患得忧郁症,此後三年时间她陷入找不到希望的低潮。
她说自己从来不是争胜的人,但害怕输,「那场忧郁症确实把我的人生天翻地覆地改变,我以前的脾气很烂,忧郁症後我更懂得谦卑。」
「从前我没看过世界其实很大,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大,但现在我的心态、眼光改变了。当我拥有了谦卑,我就拥有更多学习的心,学习如何做一个人、如何跟其他的人好好合作。」
当年 16 岁的郑秀文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进入演艺界,粉末登台 30 几个年头,回望一路跌宕,明白众人耳语皆不重要,生命必须忠於自己。
她发现人生好似还原法,活得越久越还原真正的自己,「我现在很坦然了,我是什麽我就呈现出来。」

图片|《流水落花》剧照
做演员,是发现自己的过程
郑秀文坦言,经历过千禧年因《百分百感觉》、《孤男寡女》而爆红的演员时期,她曾试图脱离喜剧,寻找突破,直到现在明白,做演员最重要的是服务角色。
从追求个人突破,到专注成就角色,是她反覆试错而得的领受。
「自从我比较少演喜剧後,我尝试不一样的电影,比如《花椒之味》、《圣荷西谋杀案》,但在尝试的过程,我看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与可能性。以前演戏会想,如果不把情绪表现出来,观众会感受不到,但後来我在表演中慢慢调整、感受,有时伤痛的情感,它是深沉、内敛的。」
2019 年,《花椒之味》里的夏如树终於找到离世父亲的火锅秘方,她闭眼品嚐,在呛辣的花椒之味里明白家的滋味。
那颗特写镜头,微微发颤的手指、似哭似笑的面部神情,郑秀文闷闷地演,像屏息以待体内深处的什麽,无声地爆发。
2023 年,郑秀文饰演《流水落花》里的陈天美时,也有一颗内敛的镜头,「尝试领养小花无果後,我跟小花有一场很短的戏。她睡地板,我在她身边躺下,没有对白,我只是闭着双眼,缓缓地张开眼睛,从眼角落下一滴泪。」没有煽情的告别,泪落下的瞬间,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种饱满、很深很深的情绪我觉得就是内敛。有时看似内敛的表达,观众却能在表演里感受到力度。」
郑秀文说,作演员是不断发现自己的过程,她在角色里学习内敛,也终於在人生中凝视自己,看见在自我突破之外,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女人迷专访金像奖影后郑秀文|走过忧郁症低潮,《流水落花》让她找回自己}
▊延伸阅读
不是演戏成魔,便是嫁为人妇,《女二》做为女演员的结局,还能是什麽?——专访第二十三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得主邓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