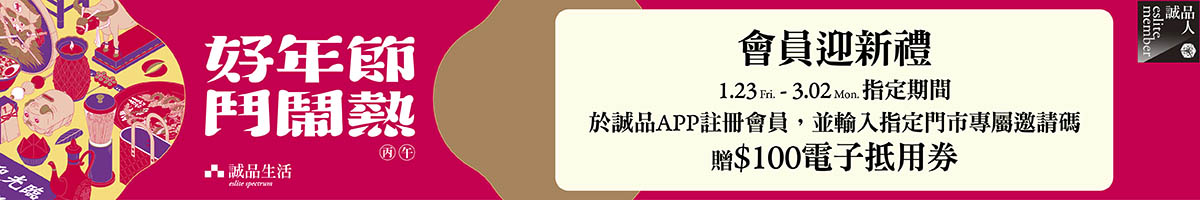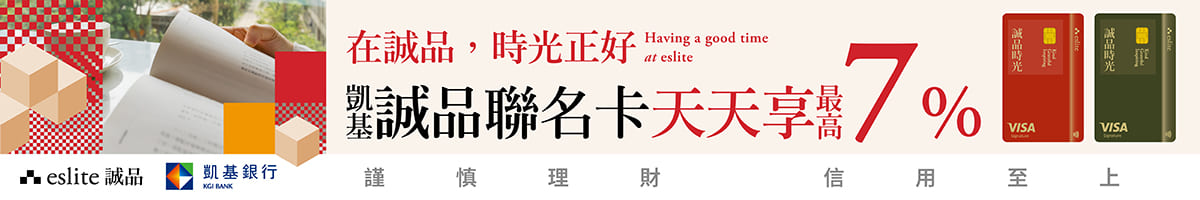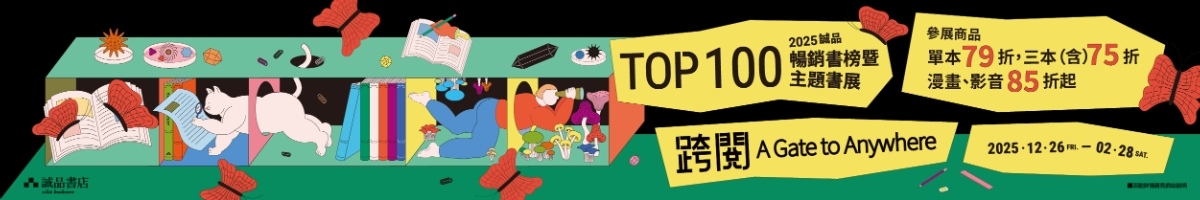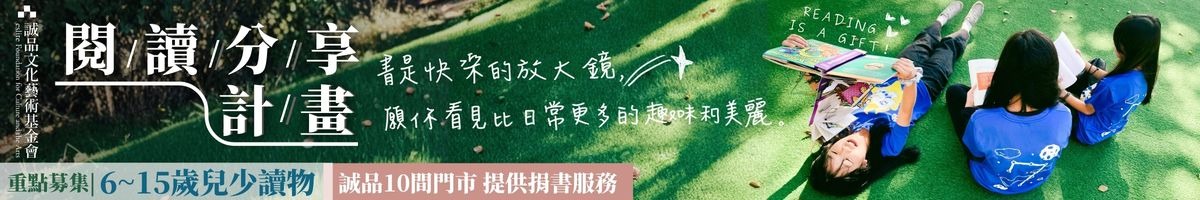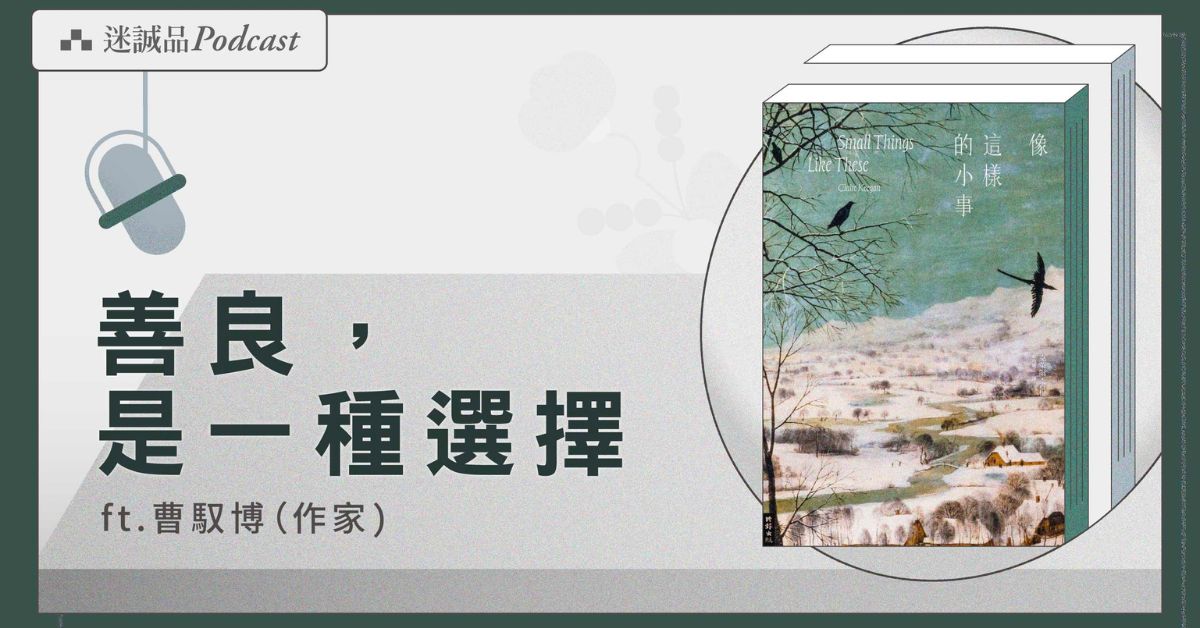大家第一次听到「婴灵」是什麽时候?那你知道这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习俗吗?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是台湾第一本以人工流产为主题的文集,透过小说、诗歌、剧本、访谈、论文等形式,描绘女性在面临生育选择时,自身的思索与感受,让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经验得以诉说,也重新思考女性的生育自主权议题。
本集由《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的主编吴晓乐担任客座主持与徐佩芬对谈,透过收听迷诚品 Podcast 或是阅读此篇文章,我们将聊到本书诞生之前的种种、佩芬在书写时所遭遇的身体变化,还有人工流产为什麽被视为禁忌?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内容皆为撰文者观点,非代表诚品立场}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的诞生与顾虑
 图片来源:Canva
图片来源:Canva
张爱玲曾在多篇文章中探究自己对於「母爱」的看法,其中於散文集《流言》的一篇文章中〈谈跳舞〉这样写到:「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
关於母爱、母性,是众多贴在一位母亲身上的标签,然而这些社会大众对於一位母职怀有的想像与冀望,却在某些时刻转化为质疑的声浪;长期以来,女性生育权一直是值得深思的课题,文学、影视作品也广泛探讨该层面的议题,然而,人工流产反而是较少人会选触及的领域,一方面该课题的讨论面相时常处於灰色地带,另一层面则是更多接踵而至的污名化标签与谩骂。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一书则是作为抛砖引玉的角色正视人工流产的议题,成为台湾第一本人工流产的文集。本书集结不同领域的作家、学者,透过不同面向进行相关议题的抒发与研究,除了文学类别的新诗、小说,也有针对人工流产於历史的流变、法律的探讨,以及十三位女性真实经历的访谈,欲从不同面相引领读者了解这些决定背後的挣扎与故事。
身为主编的吴晓乐,在考虑邀请各界学者、作家进行文集编撰时有许多的顾虑与担忧:「人工流产这个题目,其实非常敏感,我很害怕问了以後,他们其实本身不想就这个主题表态,或是不想就这个主题创作,但又不晓得怎麽拒绝我。」所以决定人选时,她花费许多时间以更「後面」的角度去观察有哪些作家可能有打算於未来的写作中碰触相关议题,或是能够直白拒绝自己的对象作为邀请的考量,因此,本书集结的文类、学术性文章皆是透过团队仔细的考量与思索编排而成。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封面设计的巧思
「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让美术很痛苦,」吴晓乐苦笑:「我们跟他说,有没有办法呈现一种概念是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的封面并非以很直观的方式呈现,反之若没有特别去了解、阅读内容,其实不会与人工流产相关议题产生连结。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的封面以五彩斑斓的细线、色块构成。吴晓乐解释,这些色块就像是每个人对於一个议题抱持相异概念的板块,拥有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但这些立场却不是全然对立,而是有一些细线正联系着彼此:「我们想要去表达的,是一开始人想要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那个意愿不可能是非常强健的,一定是小心翼翼、非常脆弱,然後过程之中可能随时随地就会断裂。」
「怎样的人可以去说人工流产的故事?我觉得大家依照现在讨论事情的方法,最最最简单,也最最最懒惰的方式,其实就是让有做过这场手术的人出来说自己的故事。」吴晓乐在书中高度匿名采访十三位曾接受过手术的女性,访谈过程中,她不断去思索,为何每个人总是这麽依赖实际的经验?而到底要怎样的人可以去传递这个议题?
吴晓乐提到,采访过程中,她不断想起她的母亲,同时也思考这些采访者选择不生的理由以及背後的考量,这带给她很多冲击,同时她也坦承,大多人不会因为阅读一本书後,就马上对於产生想法上的剧烈转变,但可能光是多说一个字、一句话,很多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差异,就像是封面上连结的细线般,搭建着双方的理解与困惑,并尝试在板块交接处理解彼此的难处与主张:「我现在就好期待2035年之後这本书又会被放在怎样的定位里?」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诗人徐佩芬创作的心路历程
 图片来源:Canva
图片来源:Canva
「我是一个不婚不生,到现在今年38岁了,这个念头完全没有动过。」诗人徐佩芬参与《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文集的计画,她於其中创作了一组诗作〈搁浅〉,当中除了同名诗作,还包含〈陌生人〉、〈无知〉、〈宝盒〉、〈魔术〉,共五首诗。但完成作品後,徐佩芬被确诊罹患罕见的急性乳腺炎,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结婚与生育念头的她,产生了过往从没产生的念头:「我们直接讲终点就是死亡,意料之外提早来到的死亡,我究竟会比较释怀呢?还是觉得遗憾呢?比较释怀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至少我留下了一个孩子。最多人的理解的方式就是我留下了一个传承,因为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们觉得小孩子很多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你来过这个世界的证明。」
一个孩子究竟意味着什麽呢?寻常概念下,通常父母会比孩子还要早离世,若有一位孩子留在世上,彷佛就多一个人记得自己。这让人联想到迪士尼动画《可可夜总会》(Coco)当中描绘,若人世间没有记得你的人,那麽身在亡灵世界的人将会面临消逝的问题。
这也让人不禁思索,在人世间遗留下自己存在过的痕迹,似乎是许多人内心潜藏的一种渴望与忧虑。身为创作者的吴晓乐与徐佩芬则认为,反而很多作家直到人生尽头没有生孩子,似乎也是因为他们早已透过作品、创作解除这份焦虑。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徐佩芬仍在某个瞬间思索有关生子的问题:「我不希望这世界上再一个本来可以与我没有牵扯的人,要为了我伤心,但这真的是我这麽多年以来第一次脑中浮现了,如果我有过一个小孩的想法。」
徐佩芬创作〈搁浅〉的时候,不断回想起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她坦言:「我不知道为什麽,因为我母亲很害羞,害羞到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直视她的眼睛。她回避所有人的眼神,以至於我也不知道如何跟她对谈,我们是没有办法吵架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说话。」从这层有些距离,却又漠然的相处方式,在徐佩芬的诗作展露一角,这层疏离,却又连结血脉相连的关系。
▌更多女性成长的思考与反思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从历史角度剖析婴灵的起源
 图片来源:Canva
图片来源:Canva
无论是民间乡野传说林投姐,还有後续改编成漫画《守娘》的陈守娘,或是许多惊悚片都以婴灵为核心主题,下意识会认为「婴灵」的概念可能很早便流传於民间。不过透过《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一书中所收入的学术研究文章〈无差别格斗派的爱情:吴燕秋与台湾妇女堕胎百年史〉,从不同阶段了解人工流产的产生与变化,当中便提及,婴灵概念的产生比想像中还更为近代,大约是在1980年代於各大报纸上出现「婴灵供养」的耸动标题。
不过,会产生婴灵供养的概念,依据台湾民俗学学者刘枝万的科普,这是源自於日本「水子供养」的习俗,同时这样的概念从日本移植至台湾,可能是基於宗教商业化的操作模式,同时也是历经人工流产伴随而来的罪恶感与恐慌下的结果。
吴晓乐提到,她在采访的过程中,听过采访者提及以前曾在电话亭中发现一本小小、不显眼的本子,内容则是说明婴灵究竟是什麽,间接佐证了吴燕秋的研究结果:「如果我们现在拿婴灵的概念去问我们的阿嬷,可能七、八十岁的阿嬷,其实是没有什麽概念的,因为这个东西引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已经四十岁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印象会更後面。」
吴晓乐与徐佩芬大约都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接触婴灵的说法,这个概念以及受访人所提供的资讯,让她们知晓,其实有许多女孩在求学过程中曾经被召集起来,观看人工流产的影片。不过播放人工流产的影片所代表的意义是什麽?若只是以极端的方式,并无加上任何说明与配套,似乎只有达到恐吓的效果。若要传递正确的卫教知识与概念,应该是不同性别的人都应该了解,比起恐惧,认知正确的概念才能真正除去不安的想法与莫须有的污名化罪名。
《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正视曾被忽略的声音
 图片来源:Canva
图片来源:Canva
「我们这个社会不要讲全部的男性,但可能有一半的男性,无法讲这个题目,他无法在这个话题多讲几句。」《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是讲述人工流产议题的文集,然而这在另一层面更彰显男性区更需要阅读这本书:「因为你是一个男生。正因为我觉得男性比女性更需要读这本书,因为当身边的女性朋友进行人工流产,你得要表达你关心的时候,你从头到尾说你那个後来好了吗?最近有没有好一点?你还在在意吗?」这样表达方式,反而原本准备放下的女性会产生一种需要继续在意这件事情的压力。
同时,书中藉由真实故事的采访,可以从中看出当中女性决定过程中所遭受的煎熬与考量,但是若不了解的人,可能在听到人工流产手术时,下意识会浮现在脑中的,不外乎是社会结构下强压在一位母亲、一位女性身上的标签,并对此做出伤害性的批判与责骂。
吴晓乐在《以为无人倾听的她们》访谈文章的後记最後一段话便是:「你的人生也很重要。」拥有孩子的人生、没有孩子的人生,最终下定这个艰难决定的自己,请将自己也纳入这份考量之中,因为身为一名女性,同时也拥有属於自己的人生,如同张爱玲於〈造人〉所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
▌台湾首部人工流产文集
每位女性在选择人工流产时,究竟遭遇怎样的困扰与挣扎,然而这些决定却遭受到污名化的看待。
从不同面相看待人工流产的历史、文学展现,如何阐述这个课题。
▌女性生育的自由意识
现在能够延迟生育的方式便是冻卵,然而这场冻卵行动背後又意味着什麽?
本书藉由冻卵的角度看待生育议题,决定生与不生并非回应社会答案,而是基於个人自由意识下的选择。
▌更多女性身分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