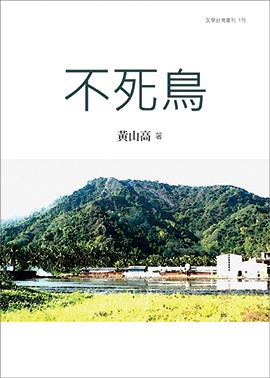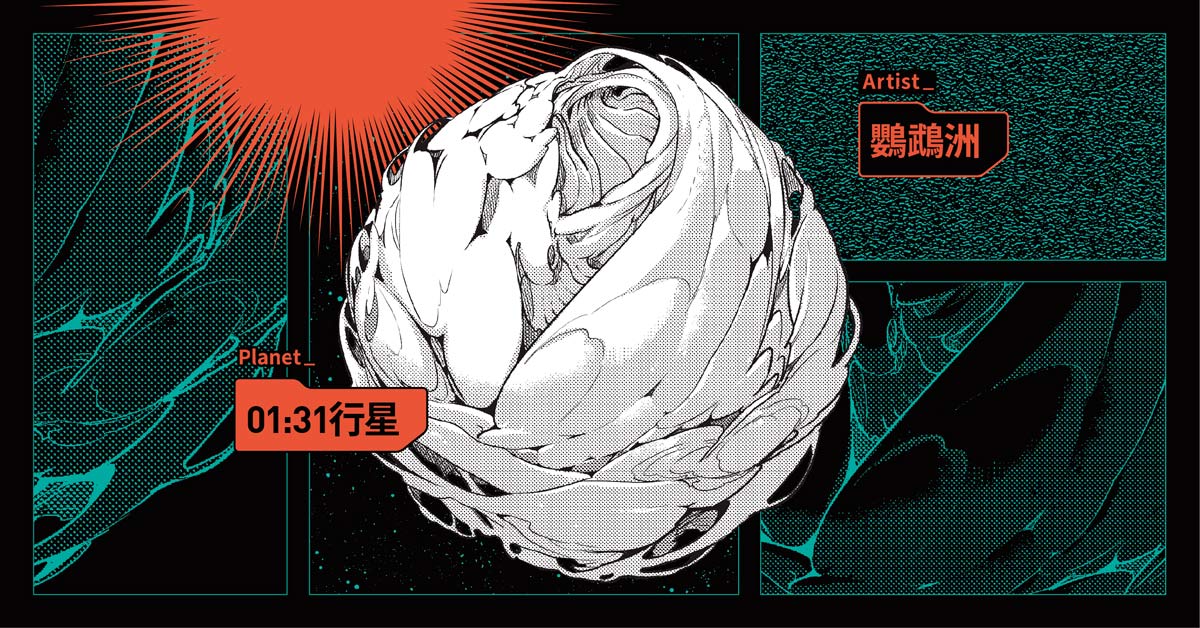虚构的真实,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秘而不宣的谎言契约|访《不死鸟》作者薛西斯(下)
撰文 邱常婷(作家)、薛西斯(作家)同样游走於不同类型、武侠奇幻一把抓的台湾作家邱常婷透过笔访,与薛西斯共谈这趟瑰丽江湖游。
阅读|侠是愿意为了他人而使用你的特权,不论那是多麽微小|访《不死鸟》作者薛西斯(上)
{本文内容由独步文化提供,非经授权请勿转载}
上篇的问题提到了一些女性角色的名字,我想更进一步请问,薛西斯如何创造《不死鸟》角色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些角色的名字都非常美,而且不会太浪漫或华丽使人出戏,只是无比雅致与合适,甚至连蛊虫和门派的名字也都好好听。
【薛西斯】:
有些名字是为了提示或辉映人物命运而设计,比如「承平安乐」之世,就是注定与「悲麟叹凤」之世背道而驰的。
其他的话,原则有点像写诗吧,不可太俗,也不可太雅太险。
在读完《不死鸟》後,我其实感觉整个故事的背景和世界观相当庞大,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看见薛西斯为了在故事中开辟出清晰的道路所做的牺牲。不知道在所有的故事线中,有没有哪一条线是你觉得还有未竟之处,或者虽然已经写完了,但私心仍有一些想像留在脑海中呢?
【薛西斯】:
前面也提到,我心中武侠小说的最大魅力在武林,就以这一点来说,武林写得不够丰富是最大的遗憾吧,但单集的篇幅很难写出一个更完整的武林了。
如果单纯就故事几条主线的话,旧版缺陷是比较明确,我和编辑有针对这些问题讨论过,其实我们的观点颇一致,就是丹阳谷的鸿麟三人组和栖霞派必须收尾。
前者当年我自己就很清楚有问题了,而且我不知道怎麽处理,对不起,只好摆烂。这回倒也不是说大展鸿图,至少做了一个情感上较完整的收结。
後者我与编辑看法就比较分歧,这回我仍不愿收尾,只是结得乾净一点,提醒大家,山上当然会有一个结局,只是我没说。
而那具体是什麽?对我来说,栖霞派的结局,就如同薛丁格的箱子里一头已死透的猫。唯一让猫活下去的方式,就是永远也不打开箱子。不过我将一些对栖霞的意见留在番外篇了,也算提供读者一些想像的可能性。
再来想请问薛西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自己被《不死鸟》的故事勾住的时刻,就是我读到石棺中的女孩失踪(为了避免剧透,我就不说明得太清楚了)。虽然你很快便解决了这个悬念,但总是有新的剧情和新的悬念紧接而来,这让我想要继续读下去,迫切地渴望知晓结局。我十分好奇薛西斯在设计剧情或伏笔的时候知道你的设计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效果吗?如果是的话,你如何有技巧地编排这些层层叠叠互有关连的剧情呢?
【薛西斯】:
是,写作时我会意识自己做的每件事带来的效果。
要说编排技巧,我觉得只能根据故事临场见招拆招,但通用的大原则是,时时刻刻将读者放在心上。我会一直在脑中想像读者,模拟他们此刻在想什麽,作家的控制欲可能都很强。
我经常一边写作一边听到读者的声音,那有时也颇使人发狂,因为这些虚拟读者十分刻薄,事实上,我现实收到的批评经常都没有我脑中这些虚拟读者的百分之一恶毒。
薛西斯提到自己脑袋里读者的声音,这是否也是写作者做为自己的第一个读者,在一面写一面读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想法呢?想要进一步追问如何平衡内在的两种声音,因为这样看上去,作者与读者的两个角色似乎经常冲突。而如果这个「读者」指的不是作者分裂出的另一个身分,而是真正想像出的其他读者,十分好奇想请问,薛西斯觉得这会是怎样的一些人(外貌、穿着、神情、身分)?
【薛西斯】:
必须面对市场上的读者,让我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个体和群体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人群虽然由人组成,有很多类似人的性质,但人群的本质并不是人。
我脑中这位就是人群而不是人。所以他是男人也是女人,是太聪明的人也是太愚笨的人,是很前卫的人也是很保守的人,是喜欢我的人也是讨厌我的人。另外,由於我自己也混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你可以说他既是作者自我分裂出的另一个人,同时也是作者想像的其他人。
我其实从没有想要平衡他的意思,他有时候满好用的,会痛骂我但也会瞎捧我,而且,如果我可以这麽简单叫他闭嘴,後面那个600字难题就不存在了嘛。
如果一定要有形象,可能是一团黑暗混沌不可名状之物吧,但此物会发出声音,而且配音员是我自己。
薛西斯不止一次提过小说的虚构性,但我认为好的小说没有足够真实的细节也无法说服读者。而薛西斯的故事总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我相信是真实的,这并非是指《不死鸟》的故事真正出现在世界某个角落,而是读者能够藉由薛西斯的文字,让《不死鸟》在内心真实地发生。对我来说这是小说不可思议的地方,更精确一点来讲,是幻想小说能够创造的魔法。幻想文学曾被称为逃避文学,因为只是纯粹的fantasy。那麽薛西斯又是如何看待小说虚构里的真实呢?
【薛西斯】:
我为写另一本作品《塔纳托斯的梦境》,大量阅读佛洛伊德着作,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乖离:我时时刻刻都觉得他在胡说八道,即使如此,我仍深深为他所说的一切着迷。
这种感受让我忽理解为何许多人指责他是空想文学家而非科学家,这或许正描绘出小说家的一种本质:我们很像政治或宗教领袖,必须时时煽动读者,让他们愿意跟随自己。但和领袖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并不需要读者真的相信我们。
因此我认为,所谓虚构的真实,其实是一种作家与读者间建立的默契,一种秘而不宣的谎言契约——你知道我在胡说八道,但阖上这本书以前你装做什麽也不知道地相信我,由此交换一段时间的快乐。
至於契约如何建立,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事,传统文学或许会更认可写实一些,但必须要够写实才能建立契约,倒没有这样的事。
比如轻小说经常夸张地舍弃写实,但还是能和客群读者建立契约。而推理小说迷也会有限度的容忍不写实(一个惊世犯罪手法,只要在理论上可行且暂时无法证伪,我们就愿意签约啦!)
换句话说,真实和虚构的价值如何看待,我想应该根据的是你想和谁签定契约、并签到什麽程度的问题。
我不太喜欢逃避文学这个词,它听起来很像一种n世代会拿来抱怨n+1世代的用词。有阵子我着迷於一位南斯拉夫作家,觉得与我平时读的作品都不同,他笔下的一切如此充满幻想风情——忽然我察觉,这可能是因为我从未去过南斯拉夫(未来大概也不会去),一个南斯拉夫人都不认识。我依赖他说的每句话来认识他的世界,他的真实对我来说,本质并无异於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虚构。
而这虚构与真实的界线,因科技还在继续高速溶解。我们的真实世界正持续缩小,基本上缩到一个萤幕那麽小。我们根据这小萤幕每日窥看他人一定程度虚构(或称之为再编辑)的人生,并将它解释为真实。
我想,所谓的真实,本质上经常也是仰赖他人所描绘的虚构进行的一种再建构。活在世上,我们参考真实建立虚构,又用虚构再建立真实,所以实与虚,我一向是懒得太用心区分的。

我其实有在默默关注薛西斯的噗浪,我看见你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想放弃写作,我想请问是否现在仍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有的话,你又是如何克服的?做为一个创作者,是什麽支持你不断写下去?
【薛西斯】:
据说人类心智平均每分钟可解析750字,而我们说话速度则平均每分钟150字,也就是说即使此刻正在讲话,我们脑内都还有600字空间的沉默。
我那600字的沉默空间无时无刻都是爆满且大轰炸式的,支持我写下去的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想把这些东西从脑子里腾出来。我从来没有克服过放弃写作的慾望,只是在600字难题存在下,两害相权取其轻。
写作要耗费大量时间、集中力和理性,就像在金字塔顶旋转一颗玻璃球,一点变动就足以摧毁它。因此与其靠个人意志力,我更希望大环境对创作更友善,至少把金字塔变成一个碗,在玻璃球真的不幸落下时,还有机会根据惯性定律来回打转。
剧透注意剧透注意剧透注意剧透注意剧透注意剧透注意
最後一题!这可能是个有点古怪的问题,但由於《不死鸟》深入探讨死亡和长生不老的主题,我想请问薛西斯,假如可以,你会选择如不死鸟加百年身的长生不老、或者仅服下不死鸟,有限但漫长的生命呢?既然无论如何都有超过常人的生命,你会利用这些时光做什麽呢?
【薛西斯】:
艾西莫夫有一段小说情节让我印象深刻:某星球的人寿命很长,於是发展出极度个人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花上几百年去研究一件事,个人就足以精通所有领域。而有寿限的地球人为了快速突破,则常须互相合作、依靠传承。
所以,如果我拥有无穷生命,应该会投身研究一切宇宙真理,既然如此,势必就需要精力、需要有维持在巅峰的生理状态来配合,那就需要百年身啦!
我觉得只是单纯延长生命没什麽意义,就像现在过度发达的医疗带来更多拖延痛苦。不死鸟的设计根本是有缺陷的,但也不能怪它,因为它的设计理念只是要拿来骗天使融资。
不过,也许我两者都不想选吧。极度个人主义同时也代表我们不再需要同伴,我们必将失去群居动物的本能——我认为,群居动物的本能就是爱。
就算我再怎麽讨厌社交,失去爱的能力,这个代价毕竟还是太大了。
▌薛西斯Xerses

台湾作家,创作类型跨推理、武侠、奇科幻,善以人物及谜团为轴心,写出缜密悬疑的作品。故事多从我们生活熟悉的元素入手,挖掘出人性困境後辅以想像力罗织的设定,令人想起阅读虚构文学时最朴实的追求--希望读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邱常婷

生於1990年春,东华大学华文所创作组硕士毕业,目前为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着有:《新神》、《怪物之乡》、《天鹅死去的日子》、《梦之国度碧西儿》、《魔神仔乐园》。
▌延伸阅读
《不可知论侦探》的诞生始末:台湾漫画第一个道士侦探海鳞子 #迷推理
一切的诅咒,都跟这双「筷子」有关——台港日作者与《筷:怪谈竞演奇物语》
▌追踪更多:独步文化@迷诚品
设计师总能在各方的任性中找到出路:科幻小说《最後的太空人》设计幕後
日本漫画珍品重版出来!《波族传奇》:活在时间夹缝中的永生一族
用恐怖对社会提出质疑:日本恐怖小说界的明日之星泽村伊智
在「家」的世界中,黑色是唯一的色彩|插画家安品与《丈夫的骨头》 #书设计
在恐惧之中,我们并不孤独:《疯狂山脉》-田边刚改编H. P. Lovecraft的挑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