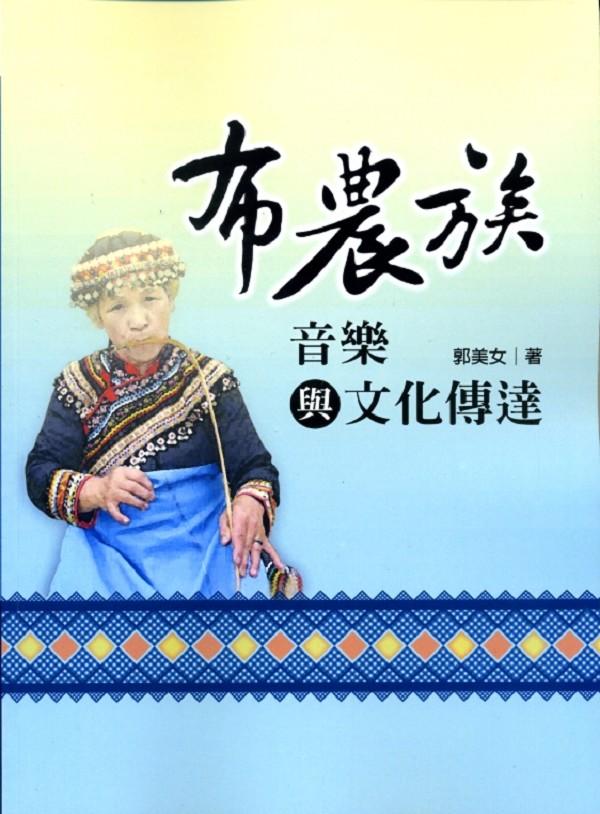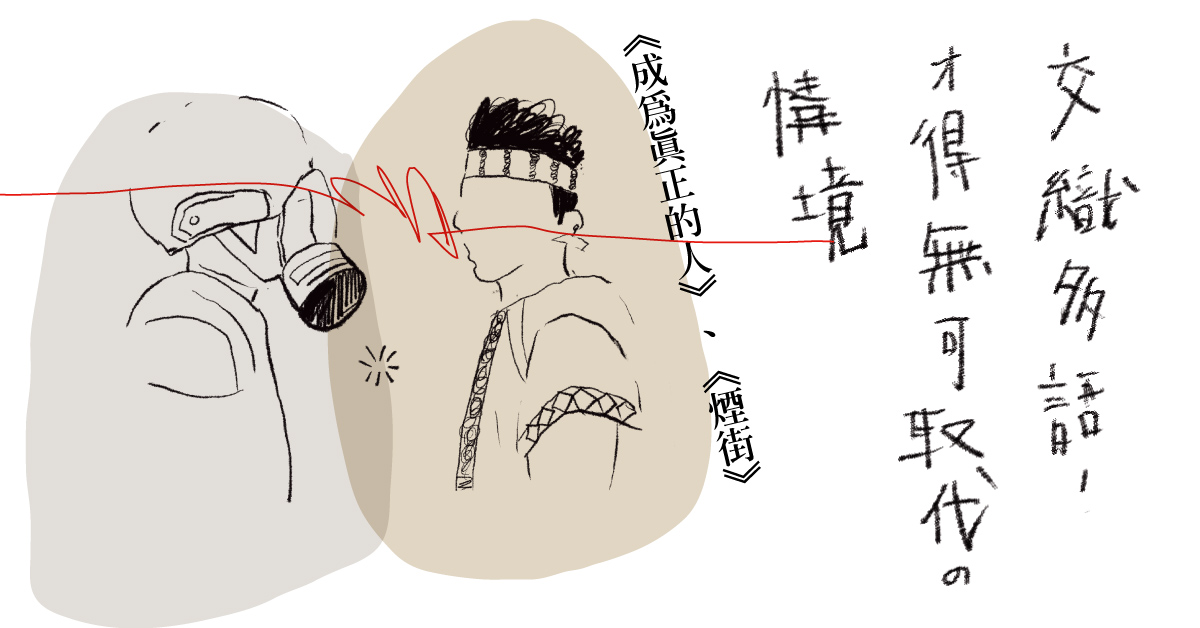
交織多語,才得無可取代の情境——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沐羽《煙街》
撰文 甘耀明、沐羽母語是戀人絮語。
語言奧妙,外人要是不懂,比密碼還難破解,電影《獵風行動》講述美軍在二戰的塞班島戰役,通訊密碼使用美洲少數原住民的納瓦荷語,日軍至終無法破解。小說《成為真正的人》以日本殖民的台灣為背景,描述兩位布農少年前往花蓮市追求棒球夢,在某場棒球賽,出現類似《獵風行動》元素,在緊要關頭,主角哈魯牧特攻占二壘。教練用被敵隊破解的手語下命令,故意露餡,請另一位主角海努南以母語喊出真正指令,大聲喊,因為在場懂布農語的只有這兩人。
母語,只有同族群的人才懂,而且這種語言從文化土壤發芽。比如主角海努南(Hainunan),名字意思是赤楊,這是森林先驅植物,布農耕地中非常重要的樹木。另外在布農傳說,擬人化的樹木會走到家屋成為柴火,直到被婦人辱罵才離開,而哈魯牧特(Halmut)是栓皮櫟,被火燒後,幸有厚重防火衣保護存活,它眷戀與布農的情感,徘徊在家屋附近,這是我用它當作主角名字的寓意。
每種語言太獨特,同語者有一聽就懂的膝跳反射,也因為如此,母語是巴別塔式多語結構中的戀人絮語。《成為真正的人》使用日語、布農語、阿美族語與英語多語情境,少年主角哈魯牧特與海努南,融入淡淡的同志情誼,在花蓮市的都市生活,他倆是種在柏油路的樹木,有時講著與外人格格不入的族語,畢竟這是戀人絮語,母語者權利,那就大方在陽光呼喊也行,這呼喊成了一種小說美好的索引,繚繞久久呢!
撰文|甘耀明
專職小說創作,出版小說《殺鬼》、《邦查女孩》、《冬將軍來的夏天》、《成為真正的人》等。曾獲聯合報文學獎大獎、香港紅樓夢文學獎、臺灣文學長篇小說金典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金鼎獎等。

《成為真正的人(minBunun)》
作者|甘耀明
出版|寶瓶文化
布農族語書名「minBunun」,意即成為布農族人。故事以一九四五年真實發生的「三叉山事件」為背景,講述一位布農族青年哈魯牧特的成長,棒球夢碎,摯友也因美軍空襲罹難的他,回到故鄉,遇上美機墜落意外,加入搜救隊,但過程中不斷陷入痛苦、內心掙扎和自我尋思。
我決定,讓任何一種語言都屬於我
寫《煙街》的時候人在新竹,出版時已經搬到台北了,這兩個地方的粵語使用頻率完全不一樣,又或者說,二〇一九後導致的新一波移民潮,來到台灣的香港人絕大部分都落腳台北。在〈製圖〉裡寫的香港村雖然取樣台北,但實際搬上來後的感受是始料未及的。在書裡,粵語代表著邊緣思考,它與各方各面的中心角力:中國中心、台灣(台北?)中心、歐美中心。然而當我來到台北後,由於身邊七成以上的新朋友都是香港人,有一種顛覆了理論本位思考的感覺。借用駱以軍《西夏旅館》的比喻來說,如果移民潮是滅國時最後一隊出逃的騎兵的話,現在我身處在騎兵陣列的中心——除非登高望遠,實在難以感到自己是位居邊緣。
但在寫這本小說時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時人在新竹,遠離台北;那時人在台灣,遠離香港;那時人在居家隔離,遠離疫情流行。那時母語剝落,而國語怎樣都無法流暢地發出捲舌音——zh、ch、sh、r——那時我知道我已經不屬於任何一種語言了。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決定無賴地,讓任何一種語言都屬於我。只要收集足夠數量的一知半解,我就能製造出我的東西。這也是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雖然我並不喜歡這個詞,但它確實在一個加速的年代裡讓移民者順利安身立命。粵語,又或香港文化,從來都是多重淺根的,它汲取所有可以用的資源,像是七〇年代香港製造業中最蓬勃的技術,以及德勒茲的理論——裝配——找到出路。

撰文|沐羽
來自香港, 落腳台北。著有短篇小說集《煙街》,獲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首獎(小說組)。散文入選《九歌111年散文選》。香港浸大創意寫作學士,台灣清大台灣文學碩士。1841出版社編輯。文章見網站:pagefung.com

《煙街》
作者|沐羽
出版|木馬文化
書名來自沐羽親身經驗,在台灣待久的他,曾把廣東話「應該」說成了「煙街」, 在書最後的〈跋〉中,他寫道:「講了一口不標準的國語,歪掉的廣東話。」另一方面,煙街也帶出反送中運動的香港街頭,要不是抽菸,要不是煙霧彈。書裡有八篇短篇小說,從租房、戀愛、親友死亡等主題中,透出潛藏在生活背面的巨大國家暴力。
關於《提案on the desk》
一本聚合日常閱讀與風格採買的書店誌,紙本刊物每月1日準時於全台誠品書店免費發刊。每期封面故事討論一個讀者關心的生活與消費的議題,推薦給讀者從中外文書籍、雜誌、影音或食品文具等多元商品。
☞線上閱讀《提案on the desk》
☞《誠品書店eslite bookstore》粉絲專頁
Current Issue_多語的美麗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