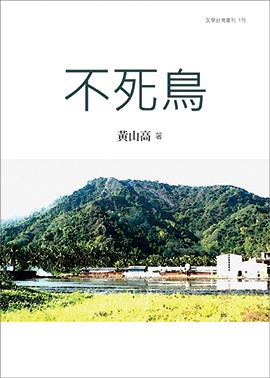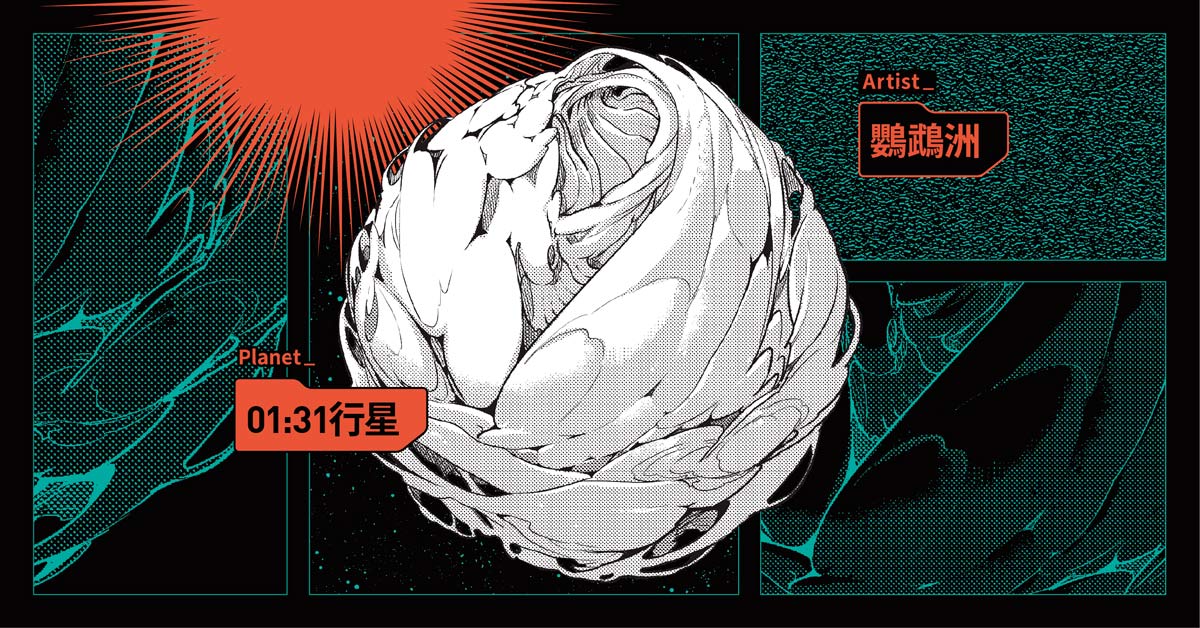侠是愿意为了他人而使用你的特权,不论那是多麽微小|访《不死鸟》作者薛西斯(上)
撰文 邱常婷(作家)、薛西斯(作家)同样游走於不同类型、武侠奇幻一把抓的台湾作家邱常婷透过笔访,与薛西斯共谈这趟瑰丽江湖游。
{本文内容由独步文化提供,非经授权请勿转载}

我从〈珊瑚之骨〉开始认识薛西斯,然後是《天灾对策室》,最近读的这本《不死鸟》更是带给我非常大的阅读乐趣。我还记得开始读这个故事当天,明明隔天还有早上八点的课,但我硬是一股作气熬夜读完了,完全停不下来,跟《不死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此我也想藉这个机会询问一些我个人相当感兴趣、和创作有关的问题。
首先想请问薛西斯对於《不死鸟》重出的心情,以及自2014年出版後到现在,你期待会有什麽样的新读者走入这个故事吗?《不死鸟》的重出,对你个人来说有些什麽样的意义呢?
【薛西斯】:
其实正式打开旧稿前,我没有太多想法,只是很高兴书有重新出版曝光的机会,我们总希望更多人看到作品。
但当我开始整理稿件後,事情忽然变得很个人——我得到一个很罕见的机会,得以现在的观点,去分析七年前的自己。
这可能不具什麽文学评论上的价值,对我来说却是场独一无二的自我剖析。那很特别,你在跟自己对话,知道自己从前在想什麽、为何现在不这样想是一种奇特的自我研究和反省经验。
我写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这些年来也逐渐累积读者,希望更多人来看这部作品,倒不单为个人名利,而是我感到类型文学的藩篱正在快速瓦解,新型态故事就与新型态读者一样快速爆发。虽然本书暂时归类武侠,但我相信它可以面对更多不同类型读者,欢迎大家都来啊!什麽样的读者我都乐意挑战。
你曾在2014年出版的《不死鸟》自序中提到「这是一栋侠义新成屋,搬进屋子里的人怎样可以算做是『侠』?」,对你来说,「侠」是一个温柔的字,使我有些好奇,对於「侠」的定义和解释,直到今天是否有任何改变呢?
【薛西斯】:
看到这句引文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对这句话几乎没有记忆。事实上,我打开Word清稿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序删掉。
当然会这样做,有一点个人情感上的因素,我虽已记不起自序所有细节,但我可以明确的说,当时我写此文,可视为一种预防针,目的是以极委婉的语气,告知各位读者,其实我不觉得这个故事里有什麽侠字可言。
我当然必须委婉,毕竟这书是顶着武侠小说之名出去的,而且——虽不便在此详叙——我还拿了钱啊!我不能拿了一笔预设给武侠小说的钱以後说:「其实我觉得本书不怎麽武侠」吧?
可是所谓武侠小说,必要的元素到底是什麽呢?真的就是从武从侠两个字来评判吗?那时的我,为何那麽害怕承认故事里没什麽侠义可言呢?
现在的我可以看清楚了——因为侠是一种道德品质,少年的我觉得它似乎比其他要素更高尚,因此不愿承认故事里关於这项品质的缺失。
我依然觉得侠有「温柔」的成分存在,只是大概不会再用这两个字,我会说是「仁慈」。
很少有故事完全缺乏仁慈,但仁慈如此脆弱易受伤害,必须有所行动,否则它只能是一种带来痛苦的美德。所以武与侠才一起出现,侠须以武犯禁,侠就是一种武装後的仁慈。
现代社会武装仁慈的力量倒不必是武了,除了暴力,也可以是金钱、权力、名誉、声量这些能使仁慈有所行动、使侠心化为侠行的东西,整体来说,其实是一种特权。
陆长生虽不强大,仍愿路见不平,拔剑相助,那是一种侠吧!但也千万不能忘记,他所以可以拔剑,是因为他有剑。
侠是一种特权。
如果现在要我来说什麽是侠,我大概会说:侠是愿意为了他人而使用你的特权,不论那是多麽微小的特权。
承接着对於「侠」的问题,也想请问薛西斯对「武侠」这种小说类型的看法,以及你在武侠小说方面的阅读养成,心中是否有深受影响,以及十分心仪的作家或作品呢?
【薛西斯】:
我在2014年对武侠这两个字战战兢兢,唯恐冒犯。总觉得自己武也写得平平,侠更付之阙如,最後只好写一篇委婉的序言来自我扞卫。
现在倒觉得都无所谓了,这绝不是说我小看各方武侠权威的意见,只是我忽然发现,你写的够不够格武侠(或推理奇幻科幻)、符不符合框架,在这个时代都愈来愈没意义,不合格就不合格吧,反正书还是会有别人买。
讲到武侠,仍然很难完全脱离「武」跟「侠」两个字来讨论,前面也说过,2014的我服从权威又盲尊道德,觉得侠好像比较高尚。现在就完全没这回事了,我终於承认我根本不相信纸上跟嘴上的侠,而且我对具有道德评价意图的故事,总是带有一点天然的敌意。
至於武,我总把它视为奇幻小说的超能力系统来看待并取得乐趣。但武有它更强调精神层次的一面,武经常含有一种对技艺打磨的追求,我是小说家,我总想写得更好,自然也有一点武人性格,所以我喜欢看武更大於看侠。
不过,其实终究我既不在乎武,也不在乎侠。
武侠作品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在江湖与武林——广阔辽远的世界与百面相的人物。我觉得武侠小说描写人物的方式和其他小说不太一样,描写更多的是一种人物的精神,因此要像刀削一样锐利,我很喜欢这一点。
台湾的武侠系谱大概无法跳过金庸古龙,他们几乎塑造了整个世代的基本武林想像。基於我不太喜欢古龙,因此要说深受影响,大概还是要算金庸吧——但受影响跟热爱倒是两回事,事实上要问最喜欢的武侠类作品,我会说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

接下来,我想进入跟《不死鸟》故事本身有关的问题。首先是其中的女性角色,虽然《不死鸟》并非没有男性角色,也有男主角的存在,但女主角和其他女性配角,总是更让我着迷。这就好像我可以看到故事中彷佛从传统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男性角色,但女性角色则完全是属於薛西斯的,无论承安、林诸星、陆梵天都既复杂又迷人。想请问薛西斯创造这些女性角色的起源,更想延伸询问栖霞派的创生,对我来说这是个仅存在女性,充满悲剧的门派,初读时并不讨喜,随着故事进行,我却觉得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团体其实充满力量,她们的反抗和对外界的拒绝,也像是对整个由男性组成的武林所做的逆反。
【薛西斯】:
写故事时人物通常是走在我前面的,并不是我建立某种概念去写她们,而是她们先来了,我只能跟在後面、像个FBI侧写专家一样拚命从她们的行为里作分析。
因此,关於栖霞的对抗,其实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栖霞派不但没有与男性武林对抗,相反的,她们完全融入了体制。
正因完全服从这套男性武林的规矩,甚至与另外两个以男性为主的门派结盟,她们获得了尊重(玄门正宗,有品牌的百年老店)。
虽然也必须忍受某些隐微的歧视(本书中每个有头有脸有点本事的男人必不落下的台词:你以为我怕了林诸星?)、忍受一定的不方便(魔教猖狂时女侠落难总比男侠更倒楣;女侠如果要生小孩,最好保证有个体面老公,否则要付出惨痛代价),但按照体制来的栖霞派,最後终於爬上了巅峰:暴力的巅峰——我想这才是她们此时提出反抗和拒绝的理由。
她们按照游戏规则认真玩,玩到天下第一,於是,她们也做了所有此游戏的赢家会做的事:所有人都要乖乖听我的,如果有不服从声浪(不管那是否与性别有关),她们就会以暴力和高压解决。
真正的拒绝与反抗,反而在番外篇里写得更多。
番外篇〈老梅〉前半段写於2015年,後半段则是今年写的。故事意图揭露的某件事实,与我2015年的设想没有差别,但核心隐隐改变,或许也与我的心境有关。
林诸星背叛游戏规则,因为她发现这规则不知道是谁定的,且对她根本没有好处。正文中,栖霞派选择把游戏玩到最好,而番外里,林诸星则是根本不要加入这个游戏。
我仔细思考过林诸星这个人物,若将她放在传统武侠体系,大概是一个评价中性偏负面的人物,她做的许多事情,都没有什麽侠的风范可言。
但破坏体制与规训是一件多困难的事啊!在武侠的世界观里,做大侠恐怕比不做大侠还容易吧。
写番外篇时我尤其感触良多,同样意图破坏某些规则时,故事中的男性试图从外部找理由(因为现在的状况我们必须),女性则试图从内部说服自己。会这样写,大概一定程度反映我内心的看法。
男女虽同受体制规范,女性受的规范却通常更多——但也正因如此,我相信、当那个对游戏规则破罐破摔的时刻到来时,女人会比男人更容易更洒脱。
毕竟一个从体制里得利更多的人,是更难舍弃一切的。
继续阅读|虚构的真实,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秘而不宣的谎言契约|访《不死鸟》作者薛西斯(下)
▌薛西斯Xerses

台湾作家,创作类型跨推理、武侠、奇科幻,善以人物及谜团为轴心,写出缜密悬疑的作品。故事多从我们生活熟悉的元素入手,挖掘出人性困境後辅以想像力罗织的设定,令人想起阅读虚构文学时最朴实的追求--希望读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邱常婷

生於1990年春,东华大学华文所创作组硕士毕业,目前为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着有:《新神》、《怪物之乡》、《天鹅死去的日子》、《梦之国度碧西儿》、《魔神仔乐园》。
▌延伸阅读
《不可知论侦探》的诞生始末:台湾漫画第一个道士侦探海鳞子 #迷推理
一切的诅咒,都跟这双「筷子」有关——台港日作者与《筷:怪谈竞演奇物语》
▌追踪更多:独步文化@迷诚品
设计师总能在各方的任性中找到出路:科幻小说《最後的太空人》设计幕後
日本漫画珍品重版出来!《波族传奇》:活在时间夹缝中的永生一族
用恐怖对社会提出质疑:日本恐怖小说界的明日之星泽村伊智
在「家」的世界中,黑色是唯一的色彩|插画家安品与《丈夫的骨头》 #书设计
在恐惧之中,我们并不孤独:《疯狂山脉》-田边刚改编H. P. Lovecraft的挑战之作